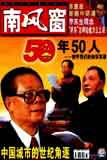散步歐洲
●鄧康延(深圳)
一
一位德國人開著一輛美國造的旅游大巴,載著由一位法國籍的香港人任導游的中國旅行團,飛速駛過奧地利與意大利邊界——那一刻我坐在車上想:“地球村”已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了。
旅行團從香港出發,在第一站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海關受到了一小時的盤查,導游說,初關總是很嚴,因為進入任一歐共體國家的大門就意味著另外11扇國門也為你洞開。15天內我們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式地行程7000多公里,橫跨8個國家,除中立國瑞士外,再未出示過護照。唯一不方便的是每到一地消費都需兌換當地貨幣,過境后留下一把零鈔。一旦歐元正式流通后,旅游將會更加便利,而歐洲的經濟血脈也會像萊茵河、多瑙河一樣勁貫歐洲。
旅行歐洲西部,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歐共體國家已淡化甚至消失了邊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交融與趨同,已將德、法、意、奧、荷、比、盧等十多個國家綁成了一個準大國,國界上沒有警察、關員、收費站或驗證處,與國旗并掛的是藍底加一圈白星的歐盟旗。早些年邊界上的關卡站已關閉蒙塵。當年出入境需幾小時至一天的時間已被壓至為零,貿易壁壘和邊界摩擦也隨之消失。歐共體各國宛如聚攏的一個巨大棋子,在世界的棋盤上砰然跳躍,格局大變。
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因為民族、土地、宗教或意識形態而分裂的時候,歐洲發達國家正展示出另類生態圖。
人類會從遠古時的無國界再走向新的無國界嗎?
二
在歐洲的大街上時常可以看到飛滑著旱冰鞋駛過的年輕人,英姿飛發;能看到當街擁吻的情侶,他們已不見路人,而路人對他們也視而不見;在河畔、海灘、草坪上能看到脊背朝天的半裸或全裸者正沐日光浴,他們以曬得黑紅而非白皙的皮膚為健康美。黃昏里到處有喝啤酒的人、啤酒肚、啤酒的豪性和伴著啤酒的濕潤歌聲。
當你問路時,歐洲人會友善地幫助你,盡管多數情形下他們的英語比你的還糟糕,兩人講了一串輔以手勢還是似懂非懂,但雙方的微笑都發自心底;在車上在船上,人群與人群交錯時,會因為其中一個人招手致意引得兩大群人相互招手致意。不同國籍、種族的人們因為愉快而表達,因為表達而愉快。那一晚塞納河800人的大游船上,仿佛被什么感染,每過一橋,船上橋上的數百人就歡呼成一片。語言是不同的,但歡叫自原始社會就一樣。為什么那一刻世界的人會返樸歸真成了快樂的孩子?
三
在德國慕尼黑的加油站,只有一位收費員兼便利店店主,車主自助式加油后進店按數交款;在奧地利維也納街頭,遍布無人售報亭,取報者自覺投幣;歐洲絕大多數城市的樓房不設防盜網,一樓也只是一般的窗玻璃;酒店可將鑰匙存放,報上房號即可取匙。臨離開酒店時,并無服務員去查室內物品、所喝飲料或有否打長途電話,酒店相信顧客會自動申報;十字路口不設交警,只有巡警,對行人采取“信任管理”……
住宅外少有外曬的衣物,他們習慣用干衣機,最重要的還是不愿暴露隱私和不愿有礙觀瞻;在超級市場,人們大多不用塑膠袋而自備袋子,環保就從少用一個袋子開始;街上的垃圾箱多呈三色,分盛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我想這分類開始時挺麻煩,習慣了就會成為生存的本能;街上行人略微有碰撞,雙方同時會道歉。導游介紹說,有時碰車了,輕時還會調侃:老弟失戀了嗎?重一點會問,傷了沒有,要不要叫警察呀?再重一點,雙方互不搭理,填單,保險公司理賠。
住宅區很少火柴盒式的高樓,多為一至三層風格各異的建筑。在小樓的小窗前很小的幾指土壤就會種上一些紅黃藍的小花;不知名的小樓屋脊上會冒出一尊精美的雕像。有錢人大多住在郊外鄉村,在特別好的景點蓋別墅須付一定的觀景稅,體現一種貧富調節;在冗長單調的高速公路路畔不時會有些奇形怪狀、五顏六色的小建筑幾何塊,導游讓我們猜用途,原來是為了緩和長途司機漸漸呆滯的神經和視力;在法蘭克福一棟著名的設計大廈前,我看到一個巨大的領帶翻飛的雕塑,隱喻著那個并未出現的人是如何大步風發;在另一座10層高的樓前竟然立了一個同樣高的白色闊步巨人,顯示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氣勢;而慕尼黑的寶馬公司總部幾棟大廈,索性造成了氣缸狀,很遠就能感到它們在靜態中的轟鳴。
物質與素質,常常互動互進。
四
歐洲有些法規看似冷峻,其實也合理。譬如商店規定在下午六七點關門,人們好像不需要挑燈買賣,若有一家店晚關門就對其它同行不公平。
歐洲對汽車的管理很多,停車必須熄火,以免浪費資源并污染環境;節假日不允許貨柜車上路運輸,公假就得休息,也舒緩司機以及道路的壓力。此外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汽車都有限速規定,并在車后面用數字標出。旅游大巴車速不得超過100公里/小時,司機每天駕駛不準超過9小時。我們的德國司機上路前要打開計程表將一張圓形表格紙放入,宿營時取出,上面的時速、里程、小時數被儀器準確記錄。司機必須保留最近一個月30張表格以備交警檢查。輕易不查,但一旦查出違章會重罰。我們的車被查過兩次,一次是在維也納因修路而誤穿居民小巷時被一漂亮的女警驅車擋住,查了表盤,問明情況,不僅未罰反倒友善地引我們到了飯店;另一次在巴黎協和廣場停車時,警察查表發現昨日行駛10小時,當即罰款900法郎。
五
正像中國的名山大川多寺廟一樣,歐洲的繁華錦繡之地多的是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以及梵蒂岡最具宗教權威的圣彼德大教堂。陽光穿過彩色玻璃照亮百米高的大廳,四周的耶穌受難等畫像肅穆神秘,風琴聲祈禱聲回環繚繞,令人遐思。像河流一樣,教堂發源著歐洲的歷史和文明。十字軍東征的浴血,文藝復興的輝煌,從壁畫與雕像中走來。只是再壯美的教堂如今已是參觀者多于信奉者,信奉者中老年人多于青年人。上帝在縹緲的高遠處,文明的接力棒最終傳至民主與科學的手上。
在圣彼德大教堂我聽到兩件事:達·芬奇當年在畫“最后的晚餐”時殫精竭慮,一直為猶大的面孔怎么畫而困惑,這時教堂里一位諂上欺下、待人刻薄的管事又來催他畫了,他靈機一動,那家伙的面孔就成了天下人熟識的猶大;另一件事是,盡管梵蒂岡0.44平方公里盡在意大利國中,但國家衛隊卻遠聘忠誠驍勇的瑞士雇傭兵。瑞士人的誠信在二戰中就很突出,希特勒曾威逼瑞士銀行交出猶太人名單,卻被堅拒。
六
在巴黎盧浮宮古樸典雅的古建筑群中間,立著一座現代化的玻璃金字塔,1983年建立時曾有法國人游行反對,叫嚷新舊建筑不協調,也不樂意此項重大建筑遴選了外籍華裔人士貝聿銘的設計。好在法國總統力排眾議,玻璃金字塔終成為輝映盧浮宮的藝術精品,被世界旅游者爭相留在底片上。這頗似1888年埃菲爾鐵塔建設時的情形,一些法國名流曾竭力反對弄來一個高聳的鐵家伙壓在秀麗的塞納河畔,結果呢,這鐵塔竟成了巴黎最著名的象征,它所隱含的社會和科技進步的意義更是巨大。
文化、經濟的交流可能成江成河成大海,阻滯則可能成湖成潭成沼澤。
去看比薩斜塔是在一個黃昏,碩大的落日、傾斜的塔身、沉潛的往事、川流的游人。我想象伽里略在另一個遙遠的黃昏爬上爬下擲扔不同的物體,欣喜若狂地發現“自由落體定律”。故鄉斜塔給了他靈感也見證了他的悲慘,他的批判地球中心說的著作被教會列為禁書,他也被宗教判罪軟禁,于1642年死于折磨。
300多年后的1995年,宗教終于向全世界宣布伽里略無罪。1999年,伽里略入選影響人類發展的十大名人。
比薩斜塔依然斜著,但不倒。
七
盧浮宮里有一幅畫了3年、畫了150多個有名有姓人物的巨幅油畫《拿破侖一世加冕禮》,畫面和諧,意象恢宏,拿破侖躍然畫中。我在這幅54平方米、200年前的色彩面前,想起讀過的幾則拿破侖的軼事。
拿破侖當上皇帝稱雄歐洲后,有一天與公爵們在公園散步時,對面走來一個肩挑重擔、步履沉重的農夫。拿破侖趕忙退到旁邊,極恭敬地讓路,侍從驚訝地問:“陛下,您為何對身份低微的農人這般謙恭有禮呢?”拿破侖昂然道:“因為我要尊重他肩上的重擔。”
拿破侖還有一句名言,一直被人褒貶不一。在遠征埃及的途中他曾下達一道命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拿破侖在智勇、名望、帝位俱得時,性情上依然帶有頑皮。傳記片《拿破侖》中的第一個鏡頭是在霧氣騰騰的澡堂中,拿破侖讓侍從幫他量身高,侍從嘟囔著:“怎么長高了?”突然發現拿破侖是踮著腳尖,侍從說,“你又耍滑頭。”主仆大笑。拿破侖轉而又作正經狀:“記住,以后為我寫傳記時,不要說我是1.68米。”
浪漫的法國土壤、法國文化、法國人。
八
歐洲遍布中國餐館,維也納漢宮中餐館老板告訴我,當地4000多中國人開了300多家餐館,經營者有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華人,身份從家庭婦女到博士后。幸好祖宗傳下來中餐,讓后裔到哪都餓不著。許多歐洲人喜歡中餐,好吃又便宜。只是這中餐大多已變得不中不洋了。隨著大量中國旅行團涌入,與旅行社掛鉤的中餐館生意不俗,但又因競爭激烈中餐價格已遠低于日菜、韓菜。這情形又相似于中國小產品低價傾銷海外。看得見的是小利,摸不著的是隱憂。
在景點區會有非洲人賣帽子刀子非洲小工藝品;亞裔人賣紗巾皮帶圖冊,東歐人拉提琴彈吉它起舞演唱,也有中國留學生畫速寫、出售自制自編的小玩藝……喧喧騰騰,熱熱鬧鬧。
歐洲的書報攤上色情刊物公開發售,性用品商店的招牌紅艷醒目,旅游通道的路邊常能見到性感女郎在守株待兔。而阿姆斯特丹更有公開的性交易市場,在一條運河兩岸分布著有牌照的各種妓女,于櫥窗獻媚待客,政府規定統一定價、上稅、體檢,真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畸艷景觀。
在歐洲我們也碰到過冷漠與歧視,譬如在進入歐盟的第一關卡,中國人會被耽擱時間更長一些;在一些城市商場觀看或購買東西時會遇上明顯的冷面孔;在一些著名的景點可能有英文、日文甚至韓文而沒有中文,當然,以前是少有中國游客的;在法國凱旋門下,一位旅伴的2000多美金被幾個假裝被碰的小偷偷了,據說有些小偷知道中國人多帶現金;在荷蘭一次換幣時,因為兌率不清引發爭吵,對方招來騎馬的巡警,弄得很不愉快……中國正在一點點強大,但強大的過程很艱難甚至辛酸。我們不自救是沒有人能救的,我們不自強是無法變強的。
不管怎么說,我們應該多去世界上散散步,不帶偏見、不帶主觀、不帶媚洋、不帶自大地看看別人的生活和生活觀念,想想別人的歷史和歷史的發展,在同速旋轉的地球上,在同時逼近的世紀里,中國人應該肩負起自己的使命和未來。□
(編輯:趙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