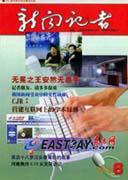給記者加個(gè)“冕”
俞松年
前不久,筆者在《新聞戰(zhàn)線》發(fā)表了一則“記者感言”,題目為《無冕而不王》。說的是人們把記者稱之為“無冕之王”,作為干新聞?dòng)浾咝挟?dāng)?shù)模筒荒芤虼硕h飄然,忘乎所以。記者不是王、不稱王、不為王。記者應(yīng)當(dāng)“不計(jì)名利,敬業(yè)愛崗,廉潔從業(yè),無私奉獻(xiàn)。”文中引用了一首記者理應(yīng)讀懂的歌:
城里走,鄉(xiāng)里走,山里走;握纖手,握綿手,握繭手;風(fēng)也受,雨也受,氣也受。有道是:名不求,利不求,官不求;伐惡效獅吼,逄善魂相就。
圖一個(gè),天無垢,地?zé)o垢,心無垢。
同行評(píng)說:“這才是真正的新聞?dòng)浾摺!蓖瑫r(shí)又指出“感言在理,意猶未盡”,希望有“有冕亦不王”的續(xù)篇。于是,就有了此篇“感言”。
記者不是王,無所謂有冕無冕;記者不是官,素來與官無緣。新聞職業(yè)是一個(gè)戰(zhàn)斗的崗位,新聞?dòng)浾呤菫檎胬矶鴧群暗氖勘.?dāng)年身居要職的萬里同志十分羨慕新聞?dòng)浾撸f新聞?dòng)浾吣堋俺痢钡降讓樱苈牭皆S多真實(shí)的故事,能感受到老百姓的喜怒哀樂,能寫大報(bào)道,又能以小“內(nèi)參”直接向中央領(lǐng)導(dǎo)報(bào)告。正如萬里同志所言,在新聞?dòng)浾哧?duì)伍中,不乏那種“熱愛人民,忠于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韜奮語);不乏那種“不怕麻煩的研究,不怕艱苦的搜索,不避艱險(xiǎn)的奔波,不畏辛勞的采掘”的作風(fēng)(范長江語);不乏那種具有“廣博的知識(shí),豐富的思想,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廣闊的活動(dòng)舞臺(tái)”的素質(zhì)(鄧拓語);不乏那種“有事業(yè)興趣,而無個(gè)人野心”的人品和人格力量(朱穆之語)。由此,新聞?dòng)浾呤艿饺嗣袢罕姷淖鹬亍?/p>
要說給記者加“冕”,上述句句嘉語,無一不是戴在新聞?dòng)浾哳^上的頂頂桂冠。新聞界前輩黃遠(yuǎn)生曾立下四言,并以此律己:“能調(diào)查研究,有種種素養(yǎng);能交游肆應(yīng),以時(shí)訪接;能聞一知十,由顯達(dá)隱;能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態(tài)度。”無疑是對新聞?dòng)浾哌@個(gè)職業(yè)的高度贊美。
記者無冕,亦不是王。“無冕之王”的雅號(hào),實(shí)際是從事記者職業(yè)的辛酸記錄。
在古羅馬,有一種人,專門傳鈔(抄)元老院錄事,然后把錄事的內(nèi)容,報(bào)告給地方長官。開始由識(shí)字的奴隸擔(dān)任,后才由自由人從事這項(xiàng)職業(yè)。因?yàn)橐M(jìn)元老院抄錄,當(dāng)政者就發(fā)給一張“門證”,類似現(xiàn)今的記者證。中世紀(jì),各地的貴族和僧侶聯(lián)系頻繁,他們通信的內(nèi)容,就是報(bào)告各自知道的信息,稱之為“新聞紙”(我們現(xiàn)今稱報(bào)紙為新聞紙,蓋源于此)。一些抄錄元老院錄事的自由人,就辦起了“新聞紙”,傳播各種信息。這就具有了現(xiàn)代報(bào)紙的雛形,也是記者的濫觴。從事這種職業(yè)的人,因社會(huì)地位低下,常受人欺凌,每每觸犯當(dāng)政者,“新聞紙”就被取締。有個(gè)叫彌爾敦的人,上書抗議當(dāng)政者動(dòng)輒取締“新聞紙”的做法。協(xié)力抗?fàn)幷弑姡?dāng)政者不得已,贈(zèng)于他一個(gè)空洞的“爵士”尊號(hào),社會(huì)卻認(rèn)可。同伙們戲稱這就是“王冠”,彌爾敦就是他們的王。“無冕之王”由此而來。
可見,“無冕之王”這個(gè)為社會(huì)所授予的稱號(hào),是記者職責(zé)之所在,而非新聞?dòng)浾哂刑厥獠拍堋?/p>
“無冕之王”似為大,那是因?yàn)樾侣剤?bào)道影響大,人們稱記者為“無冕之王”,似是褒,褒中有貶,內(nèi)中不免含有戲稱、逗趣的成份。當(dāng)記者的以知趣、自重為要。切不可利用社會(huì)對記者的信任、尊重,去圖“有償”,去謀私利,去鋪墊自己升官發(fā)財(cái)之階石。如果說新聞?dòng)浾哒嬉用幔悄┻@頂桂冠就是:——
“人類靈魂工程師”,“社會(huì)主義精神文明宣傳者和實(shí)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