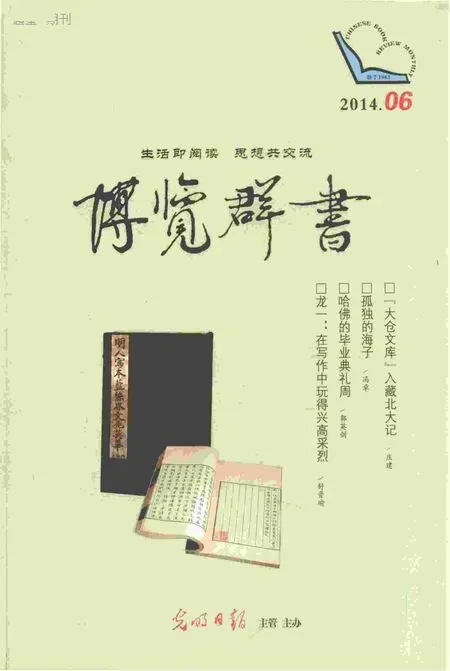佛本生經(jīng)傳
真如
最近,斯里蘭卡一位佛教界朋友送給我一套《佛本生經(jīng)傳》,令我大喜過望,愛不釋手。因為這部經(jīng)典巨著雖誕生了2000多年,在佛學(xu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至今未有完整的中文譯本,要想全文閱讀這部經(jīng)典,領(lǐng)略其中的精華,真是非常困難。
《佛本生經(jīng)傳》又稱《佛本生故事》,由于佛教僧人講經(jīng)時經(jīng)常引用,以警示人們行善去惡,流傳十分廣泛。它成書于公元前一世紀第四次佛教結(jié)集之時,開始以文字形式傳布于世,并傳播到所有信奉佛教的國家,以本生故事為題材的文學(xué)、繪畫、音樂等作品大量涌現(xiàn),極大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文化發(fā)展。如果說,這些國家的傳統(tǒng)文化是以佛教文化為本的話,那么本生經(jīng)傳就是這一佛教文化的基礎(chǔ)。
《佛本生經(jīng)傳》由547個本生故事組成,全部譯為漢語足有200萬言。本文僅就佛本生的學(xué)術(shù)價值發(fā)表一些淺薄的看法,有不足之處,歡迎指正。
一、佛本生的佛學(xué)價值
本生是三藏經(jīng)典中的通俗讀物,是普通信眾的“佛經(jīng)”。它不像律藏那樣不厭其煩地陳述那些繁縟的戒條和清規(guī),也不像其它經(jīng)、論那樣論述深奧的佛學(xué)哲理和教義(如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等);它僅以幾百個生動有趣的故事,反復(fù)說明輪回和業(yè)報的“規(guī)律”,以勸導(dǎo)人們止惡揚善,廣積福德。正是這一簡明、樸實的佛教思想,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人緇素信善,佛教和佛教文化正是在這樣的“群眾”基礎(chǔ)上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
此外,“本生”和其它巴利經(jīng)典不同。在其它巴利經(jīng)典中,只談佛、辟支佛、羅漢、比丘和比丘尼,沒有“菩薩”的位置。而本生的547個故事講的都是菩薩,塑造的都是“光輝的菩薩形象”,把“菩薩”抬舉到甚高的地位。在“大孔雀本生”(mahamora Jataka)中,連辟支佛都要向菩薩行禮致敬,這樣的記載在巴利三藏其它經(jīng)典中是十分少見的。在宣揚“菩薩濟世”這一點上,南傳佛本生與北傳的大乘佛教取得了共識,表現(xiàn)了大體上的一致。所不同的是,南傳本生中的菩薩都是些品德和智能較高的“普通人”,而大乘中的許多菩薩已經(jīng)神化。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我們也可以認為上座部佛典中的本生類是集成較晚的一個部類,因為它明顯地受到了大乘“菩薩道”的影響。斯里蘭卡佛教學(xué)者西里西沃里(Sirisivali)長老在他所著的“佛教世界”(Bhodhalokaya)一書中曾經(jīng)說過:“如果某一個國家或民族喜愛本生故事,那么這個國家或民族必然閃耀著大乘思想的光輝。”公元3世紀以后斯里蘭卡盛行菩薩道,只有行菩薩道的王子,才具有繼承王位的資格。傳說桑加坡國王(Sirisamgabo,247—249)為避免王室內(nèi)亂,生靈涂炭,曾把自己的頭顱割下來獻給政敵。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多處提到“大乘上座部”的問題,季羨林先生據(jù)此著文論述上座部佛教接受大乘思想的情況,巴利系佛典中的“佛本生”或許就是上座部接受大乘影響的一項實際例證。
二、佛本生的文學(xué)價值:
研究東方文學(xué)和研究佛教文學(xué)的學(xué)者,一向把佛本生視為一部古典文學(xué)作品,把它籠統(tǒng)地歸入到“民間故事”一類文學(xué)作品中。例如李斯·戴維斯(Rhys.Davids,1843—1922)就曾說過:“在現(xiàn)有的民間故事集中,最重要的最古老的民間故事集是《佛本生故事集》”。這部故事集在世界文學(xu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佛音于公元5世紀將僧伽羅語本生譯為巴利語這一佛國通用語后,它很快便傳布到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文學(xué),往往蒙其影響。
“佛本生”畢竟是一部佛教文學(xué)作品,所以受它影響最深最廣的,首先還是在佛教國家和地區(qū)。斯里蘭卡的古代文學(xué)和中世紀文學(xué),除西格利亞詩和禽使詩之外,其它一切文學(xué)作品幾乎都受到了“本生”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長達2000年的斯里蘭卡古代和中世紀文學(xué)就是“本生文學(xué)”。這種影響一直延及到近、現(xiàn)代。蘭卡學(xué)者認為,蘭卡的“小說”這一文體不是從西方移植來的,而是在“本生故事”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被譽為“小說之王”的蘭卡小說家W.A.席爾瓦(W.A.Silva,1890—1957)的代表作“月光”(Handapara),簡直像“古薩本生”(Kusa Jataka)的翻版。緬甸阿瓦時期“比釉詩”興盛一時,這些“比釉詩”也大都取材于“本生”。信摩訶拉塔于1523年根據(jù)“象護本生”(Hatthipala jataka)創(chuàng)作了一部324節(jié)的長篇敘事詩——“九章”,這部緬甸文學(xué)史上的名篇一直被推崇為詩歌的典范。在我國傣族地區(qū),“須大拿本生”(Vessantara Jataka)經(jīng)鋪張擴展,寫成了一部32冊的宏篇巨著。這篇“須大拿”本生在泰國也受到格外的喜愛,在全國傳誦甚廣,孺婦皆知。西藏的佛教徒依據(jù)從印度傳入的本生編寫了本民族的本生“甘珠爾”,其中許多故事與本生就十分相似,只不過人物、情節(jié)略有更動。例如“大隧道本生”中的維德赫國王的名字改成了嘉納卡(Janaka),他昏庸愚鈍,常常遭人譏諷。天神告訴他說:農(nóng)夫溥瑪?shù)膬鹤訉⒌靡蛔樱麊尽办`藥”,將來若封此村童為相,國運可昌。后來果應(yīng)其驗。靈藥之妻阿瑪拉的名字改成了維薩凱(Visaka),她聰敏美麗,盡管國王和大臣絞盡腦汁,百般勾引,最后她還是以自己的智慧挫敗了這幫無賴。在西藏的故事中,她似乎已成為主角。
印度在10世紀以后雖已不是一個佛國,但本生對印度梵語文學(xué)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五卷書”(Panchattantra,比較流行的本子編訂于12世紀)、“故事海”(Kathasaritsagara,成書于11世紀)、“嘉言集”(Hitopadesa,成書于10世紀)等,無不受到“本生”的影響。
“佛本生”從印度傳到波斯,從波斯傳到敘利亞,又從敘利亞傳到希臘。阿拉伯地區(qū)的《一千零一夜》,希臘的《伊索寓言》,也都受到本生的影響。
公元8世紀,希臘的圣·約翰根據(jù)佛本生創(chuàng)作了一部傳奇文學(xué)作品——“巴拉姆和約瑟夫”。到11、12世紀以后,這部作品被譯為拉丁文和其它歐洲文字,不少作家還據(jù)此寫出了詩歌和劇本。巴利語的“本生經(jīng)傳”于1880年譯成了英語,共6冊。這套英譯本大大地擴展了“佛本生”的傳布范圍。
三、佛本生的“文化”價值
如果我們要想全面地認識、研究“佛本生”,就不能像佛教徒那樣僅把它看作一部佛教圣典;也不能像文學(xué)家那樣僅把它看作一部影響甚大的古代文學(xué)作品;至少,我們還必須研究它在文化的其它領(lǐng)域和在社會學(xué)領(lǐng)域中的地位和影響。
“文化”的含義頗廣,上文所談的本生的佛學(xué)和文學(xué)價值也都可以歸入“文化”之內(nèi)。本文不可能闡述本生的全部文化價值,這里僅談及它在繪畫、戲劇、民俗學(xué)和心理學(xué)幾個方面的影響和作用。
自“佛本生”誕生之后,藝術(shù)家們便看中了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寶庫”。在佛教國家,雕塑、繪畫、戲劇、舞蹈等藝術(shù)領(lǐng)域中“佛本生”的影響幾乎隨處可見。早在公元前2、3世紀,印度山奇一帶佛塔的浮雕中,已有不少本生故事。我國東晉高僧法顯在5世紀初在斯里蘭卡修學(xué)期間,曾目睹五百本生的“大型畫展”。在緬甸蒲甘王朝(公元1044—1287)所建的眾多佛塔上,也都能見到本生壁畫。直到今天,在佛教國家里的幾乎每所寺廟里都能見到本生壁畫。
在“佛本生”中,許多故事生動有趣,富有戲劇性,歷代都有戲劇家將本生改為劇本,搬上舞臺。緬甸語的“戲劇”一詞源于“本生”(Jataka),說明古代的緬劇與“本生”同指一物,密不可分。斯里蘭卡最著名的戲劇家薩拉特江德拉(Edirivtra Saratcandra,1914—1956)年創(chuàng)作了一部優(yōu)秀劇本——“瑪納梅”,此劇在蘭卡戲劇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劇本的題材就是在本生經(jīng)傳中的第374個本生故事“小弓術(shù)師本生”(culladhanuggaha Jataka)。
“本生”還具有很高的民俗學(xué)價值。斯里蘭卡學(xué)者庫瑪拉冬格(Kumaratunga)曾指出:“本生故事中含有大量生動的關(guān)于社會學(xué)和民俗學(xué)的內(nèi)容,如果有人發(fā)愿殫畢生之精力對本生進行研究,必可撰出學(xué)術(shù)價值甚高的論著呈獻給人類。”(見“大隧道本生”前言)
“本生”中記有一些著名的民間傳說,這些傳說流布于東西方各國,見諸于各大宗教的經(jīng)籍文獻,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chǎn)。現(xiàn)舉例如下:
第1則是“二母爭子”的故事傳說,此則故事載于“大隧道本生”的開篇。故事說:一母夜叉搶得一男孩,強辯說是自己的兒子,與孩子的母親爭吵起來。菩薩為斷明此案,在地上劃出一條線,將孩子置于線上,命雙方拉拽孩子,規(guī)定誰能把孩子拉向自己的一方,孩子便歸屬于誰。孩子在拉拽下大哭起來。生母心疼,松開了手,于是菩薩斷定“心痛孩子者必為其母親,而只顧拉拽,無動于衷者必為假冒”。類似這樣的故事,有劇本“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德國的布萊希特又將此劇改編為:“高加索灰闌記”,成為西方劇壇佳品。
第2則是本生中的第316則——“兔本生”(SasaJataka)。講的是一只兔子。它行為無尚布施,躍入火中,要把自己的肉烤熟給人吃,帝釋天感其志誠信篤,把它的形象畫在月亮上,以使光照人間。“月中有兔”的傳說也流傳在世界各地,已成為全人類的“信仰”。
第3則是第322則本生——“巨響本生”(DaddabhaJataka)。說的是林中一顆果實掉落下來砸到一片棕櫚葉上,發(fā)出一聲巨響。臥在那里的一只兔子以為是天塌地陷,倉皇逃命;其它諸獸也跟隨奔跑。此故事亦流傳甚廣,記得在上小學(xué)時,語文課本中就有這則故事。我們西藏地區(qū)所傳的“咕咚來了”的故事,也與此故事大同小異。
這些故事和傳說是否最早見于“本生”,尚待考證。但無論如何,世界各地民間傳說中這些相通之處,對民俗學(xué)來說具有甚高的研究價值。
本生對民俗學(xué)的價值比較顯而易見,其例證俯拾皆是。而本生在心理學(xué)中的價值則往往被人忽視。魏克拉瑪辛訶(WikramaSinha,1891—1976)在《佛教文學(xué)》一書中指出:“人們都應(yīng)該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使那些好人,在他們心靈深處也會有貪欲、忌妒、傲慢等不健康的成分。這些隱蔽的(或說是隱藏的)念頭,在某種情況下會促使好人干出壞事,甚至會把好人變成罪人。在本生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證。……有些本生被世人譏為‘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中,發(fā)現(xiàn)了行動的心理學(xué)材料的例證,從而解決了他們許多‘心理學(xué)難題”。魏氏沒有具體闡述哪些本生具有怎樣的心理學(xué)價值,但他充分肯定了本生的心理學(xué)價值。所以,心理學(xué)家如對“佛本生”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必然也會有所發(fā)現(xiàn),大有所為。
四、佛本生的社會價值:
1狽鴇舊對社會道德的作用:
佛本生是佛家借助于各類故事闡述、弘揚人間善法的經(jīng)典。在南方佛國,本生的精神影響了人們的思想,陶冶了人們的感情,鑄造了人們的性格。本生中的各類菩薩,已成為人們效法的光輝榜樣。他們鄙棄慳吝,樂善好施,廣積福德;他們品行端正,反對淫欲,孝敬父母,敬仰賢德。在那些全民信佛的國家里,大多數(shù)人的這種思想品德很自然地決定了全社會的道德,這種人間善法對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現(xiàn)在一些佛教國家仍用佛本生作為進行道德教育的教材,在中小學(xué)課本里,都編入了不同篇幅的本生故事。我國傣族地區(qū)一向社會風氣純樸,有些地方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大概與“佛本生”也不無關(guān)系。當然,在佛本生所宣揚的道德觀念中,也有些消極落后的東西,如濫行施舍,忍辱不爭等,這些是應(yīng)該有所揚棄的。
2狽鴇舊對啟迪智慧的作用:
巴利語稱為“般若(panna)的智慧”,向為佛家所特別重視。佛本生來之于民間,凝聚著人民群眾的智慧,本生中所闡述的人生經(jīng)驗,是廣大人民千百年來社會實踐的總結(jié),經(jīng)本生作者(都是些有智慧的高僧)加工潤色之后,更放出智慧的光輝。這里應(yīng)該特別指出的是,佛本生中以諸多菩薩為代表的智者,大都是些勞動群眾和普通生靈。佛本生的這一特點也顯出他的進步意義。
3狽鴇舊所反映的古代印度社會:
不甚發(fā)達的奴隸社會:許多本生都說明佛陀時代處于奴隸社會。如“卡地朗迦本生”(kadirangara Jataka)中有一奴隸說:“老爺揪著我的頭發(fā)要把我賣掉,我有什么辦法呢?”說明那時存在奴隸和奴隸買賣。但奴隸主與奴隸常以兄弟相稱,保持著表面上的平等。那時,多數(shù)人的主要職業(yè)是務(wù)農(nóng)和經(jīng)商,主要交通運輸工具是推拉的車輛和畜運的幫隊,這說明當時商品交換已相當發(fā)達。有些商人還從事海上貿(mào)易,如“海商本生”(Samuddavanija Jataka)等本生,都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印度古代的王朝:有些本生比較明顯地反映出印度古代某一王朝或某個王國的情況。如“大隧道本生”的時代背景就是孔雀王朝前后的時代。
婦女的解放: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允許女性出家修道,在古代印度引發(fā)了一場“革命”。從一些本生中,也可以看出這種情況。如“滕本生”(Ucchanga Jataka)中講到這樣一件事情:國王把一個婦女的丈夫、弟弟和兒子押入死牢,其后又決定釋放她的一個親人,問她放誰為好。她說:“只要我能活下去,我還可以結(jié)婚、生子,但我父母已亡,我不可能再有弟弟。所以我請求釋放我的胞弟。”這就說明當時的婦女已有再嫁的自由。
自公元3世紀以來,隨著佛教向漢地傳布,一些佛本生也通過各種途徑和語言媒介譯為漢語。“佛本生”的評介,對漢地菩薩乘的形成與發(fā)展,對大藏經(jīng)和大乘佛教文化的完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生的漢譯本大都譯自于梵語。梵語佛典較巴利語稍晚,其本生的數(shù)量也比巴利語少,更無專門的部類,而且本生又往往和本事(ltivuttaka)、“譬喻”(Avadana或Apakana)融雜在一起,梵語本生譯為漢語時,自然也只能是“遇殘出殘,遇全出全。”于是,梵語本生的晚、殘、雜的特點也便帶入了漢譯,使?jié)h文大藏經(jīng)中的本生類也具有了這些特點。
巴利語系的本生是否從未有過漢譯呢?當然不應(yīng)說得這樣絕對。早在齊武帝時(483—493)外國沙門大乘就曾在廣州譯出“五百本生經(jīng)”(見《出三藏記集》卷二)。恐怕這就算是巴利語系本生譯為漢語的第一次嘗試吧。
時隔1500年左右,夏∽鶇影屠三藏日譯本轉(zhuǎn)譯巴利本生150則,分二冊出版,收入到普慧大藏經(jīng)中。其后,郭良ⅰ⒒票ι二同志直接從巴利本生中譯出154則(其中有7則為季羨林先生所譯),集為《佛本生故事選》,于1985年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很好的譯本,只是數(shù)量尚嫌不足。正如譯者在“后記”中所說:“在故事數(shù)目上不足全書的三分之一,而在篇幅上,估計不足全書的六分之一。”巴利語系的佛本生到目前為止尚無全譯本,許多精彩的故事,大部分中國讀者尚無法得知,應(yīng)該承認這是一大缺憾。對這部本生的研究,自然更是剛剛起步了。
從上文所述此類佛本生的學(xué)術(shù)價值,便可知研究它的重要意義。可惜的是,這樣一部有兩千多年歷史,對東方各國人民的思想、社會、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這樣一部經(jīng)典著作至今未能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如果能早日把它全文譯成漢語,必將對我國的佛學(xué)研究產(chǎn)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