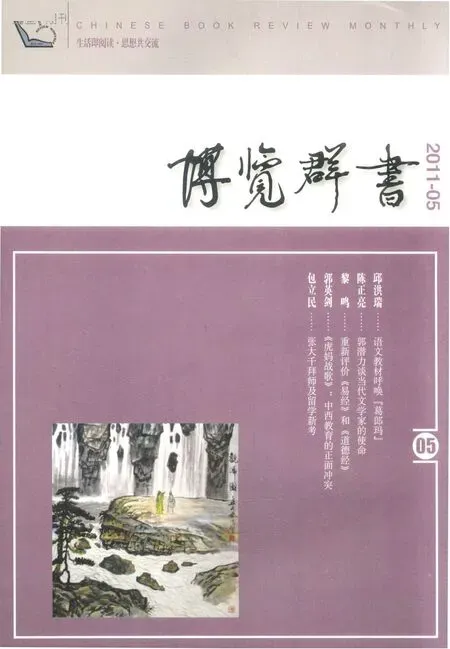“天才”的“盲點”
李力研
近日在某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專講“余杰的學(xué)風(fēng)”。文章大意是,余杰想做內(nèi)地的李敖,但在學(xué)風(fēng)上卻做不到李敖那樣。在昆德拉和哈維爾問題上不僅出現(xiàn)了引文不準(zhǔn)的問題,而且還有判斷與操作方面的問題。文章說:“要當(dāng)大陸李敖,在學(xué)風(fēng)上也得改進(jìn)。比如說,李敖要是引了誰的文章,總不忘了做注釋。不管是文中注,還是腳注都很仔細(xì)。余杰引了十處哈維爾的話,不但沒有一處注明出處,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處引文之中,出錯的就有四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準(zhǔn),才而敏,卻不能像錢鐘書那樣,直接閱讀原文,還得引用別人的“譯文”。更可怕的是,“引文”之后沒有“出處”,還有“錯誤”。這當(dāng)然是不能原諒的“學(xué)風(fēng)”問題。這確比李敖的學(xué)風(fēng)遜色一些。李敖有其浪蕩一面,但為文則很嚴(yán)謹(jǐn),甚至嚴(yán)謹(jǐn)?shù)揭驀顸h祖宗之墓,竟對“三民主義”如何抄襲美國賢哲語錄大做考證。真功夫就是真功夫,學(xué)問來不得半點含糊。看了這篇“評點”文章,將余杰的書《說還是不說》找來翻檢,里面還有一句話讓我驚訝,即“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昆德拉熱一直長盛不衰。相反,我們對哈維爾卻采取了不應(yīng)有的疏離和冷淡”,又說“對昆德拉趨之若鶩,而對哈維爾卻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國當(dāng)代知識分子人格層面里存在的某些盲點”。(余杰書,128頁,129頁)這可能是事實,但據(jù)那篇討論余杰“學(xué)風(fēng)”的文章所示,余杰之“吶喊”與“豪放”,竟然是引用國內(nèi)同好之“譯文”之后才大略了解并剖析起哈維爾及其思想的。就是說,昆德拉和哈維爾之“熱”有個先后問題,否則無法說明別人翻譯哈維爾又屬于什么。難道那也是“有意地回避”?余杰照著別人的“翻譯”說話,然而再說別人“冰冷”,從而斷定“中國當(dāng)代知識分子人格層面”存在著“某些盲點”。這類矛盾或問題是否代表著內(nèi)地李敖與臺灣李敖之差異?中國當(dāng)代知識分子(人格?)中肯定存在著“某些盲點”,但“盲點”應(yīng)該判給誰,則需重新估量。
“老子”問題應(yīng)謹(jǐn)慎
我因那篇短文而認(rèn)真了起來,這里也來添舌,談一談余杰之“學(xué)風(fēng)”或“立論”問題。他有一篇涉及“智慧”的文章,那就是《反智論:〈老子〉的精髓》。
必須承認(rèn),只要涉及到這個問題,就有可能陷入“地雷陣”中,稍有不慎,就會露出問題。因為“老子”和《老子》不同,中間有極復(fù)雜之“變遷”。往昔,大作家柯云路最愛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分不清“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兩者混同,胡攪蠻纏。讓我吃驚的是,余杰在這個“智慧”問題上,竟然也存在著“某些盲點”,大概也分不清“老子”和《老子》。余杰這樣說道:“老子認(rèn)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躉虺蛇不螫,猛獸不據(jù),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和(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接著,余杰又對這段“老子”式的言論做了解釋和發(fā)揮:“嬰兒時代是人生中最強大的時代,因為赤子處于一種天真渾樸、無知無覺的狀態(tài),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能從天地間汲取無窮無盡的能量”。
應(yīng)該強調(diào),短短50來字的引文,已有兩處甚至三處“引誤”。首先是“蜂躉虺蛇不螫”,這本是王弼本中的“注文誤入”,今人早將之改正。任繼愈早余杰20年(1978年)就將這句話改成了“毒蟲不螫”,并有改動之詳細(xì)說明:“‘毒蟲,王弼本做‘蜂躉虺蛇不螫。按下文,‘猛獸、‘攫鳥,都是一般名詞,和‘蜂躉虺蛇這些類名不一致。這是把‘毒蟲這一詞的注文誤入正文的。現(xiàn)在根據(jù)河上公本改為‘毒蟲。王弼注中正是說‘故毒蟲之物無犯……。據(jù)成玄英《疏》,蜂、蝎,毒蛇之類”。(見任著《老子新譯》1982年修訂本178頁)余杰為北大中文高材生,似應(yīng)對《老子》這樣的古典文獻(xiàn)更細(xì)究竟。然而不然,令人遺憾。余杰不知從哪里看了別人的引文就又抄到了自己的書中。這樣的舉動,寫給抽屜固然可以,但還是稍顯草率,即使不愿使用今人的“新譯”,也應(yīng)有個堅決引用王弼本的交代。毫無疑問,這應(yīng)屬于又一“盲點”。第二處“引文”問題是長沙馬王堆《老子》本做“未知牝牡之合(而非“和”)而駿作(“作”又為“怒”)”(“駿”,左邊應(yīng)為一個血,右邊應(yīng)為一個沒有單立人的俊,但電腦中沒有此字,無法寫出,只好以此字代出),而王弼本則是“全作”。任繼愈對此也有改正交代:“今據(jù)河上公本及唐碑本改。因為這一句分明講的是‘牝牡之合。”
顯而易見,改與不改不只是一個文字問題,而涉及其中的“意思”和我們的“理解”。
余杰把前面的一堆“古文”說成是“老子”說,而不是《老子》中說,這已經(jīng)有失水準(zhǔn)。將古文再做這樣的“翻譯”、“闡釋”甚至“發(fā)揮”則越發(fā)有些離譜,不像“學(xué)人”作品,更像是氣功界的“大師”言論。余杰好像只看懂了“比于赤子”一句,然后就將“引文”大而概之地翻轉(zhuǎn)成了“嬰兒時代是人生中最強大的時代”,再后就翻轉(zhuǎn)為“赤子處于一種天真渾樸、無知無覺的狀態(tài)”,從而“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這些都還馬馬虎虎,半對半不對地說得過去,但最后一句話則離譜得厲害,以致讓人懷疑余杰是否看懂了《老子》言論:“能從天地間汲取無窮無盡的能量”。老子一派固然“反智”,因為這一派人馬認(rèn)為“智慧”,會污染心靈,分散精力,從而使人“患得患失”,不能精誠團(tuán)結(jié),難以堅固城池。《老子》中幾乎處處都以“自然”事例喻示人間道理。這里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仍舊是比喻。這些話的意思是什么呢?老先生們的翻譯大概還是比較準(zhǔn)確。比如任繼愈的翻譯就可參考:
“包含的‘德的深厚的程度,應(yīng)該比得上無知無欲的嬰兒。毒蟲對他不刺,猛獸對他不撲,惡鳥對他不抓。(他)骨弱、筋柔,而握持得牢固。他還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交合,而他的小生殖器常常勃起,因為他有充沛的精氣。他一天到晚嚎啼,而不顯得力竭聲嘶,因為他平和無欲。”(《老子新譯》178—179頁)
應(yīng)該說這樣的“字面”翻譯是可以說得通的,只是在“嬰兒”與“毒蟲”的關(guān)系方面,似乎給嬰兒再加一個“不怕”才對。只有這樣才能突出“無知無欲”狀態(tài)下的嬰兒何以有“德”。《老子》這段話講的依舊是“以小勝大”。《老子》用一個“嬰兒”的“自然事例”,解釋了“以弱制強”的“規(guī)律”。《老子》中的“德”可訓(xùn)為“得”,而其“得”主要又是抽象意義上的“道理”或“大道”、“太一”之類的東西。
應(yīng)該說明的是,老子當(dāng)時并不寫書,就像孔子也不寫書一樣,老子本人并沒有《道德經(jīng)》或《老子》這樣的書,因此,“老子”其人與《老子》其書不是一回事,時間相差好幾百年。《老子》是經(jīng)過后人特別是“稷下學(xué)宮”一派人馬上百年之努力逐步“修繕”而成的,它屬于探索“自然規(guī)律”的道理總系。
《老子》豈在“反智”!
“老子”和《老子》并不“反智”,而是崇尚另一種真正的智慧。這種智慧就是“自然的智慧”,是故強調(diào)“道法自然”。上面“比于赤子”的話還是“道法自然”的具體說明。比如小樹,本敵不過刀槍,但因為它沒有對刀槍的認(rèn)識,從而面對刀槍之戕伐也就無所謂恐懼,反而成了刀槍之障礙,甚至眾多小樹小草會把刀槍折損。這其實才是一種高級智慧。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經(jīng)常使用《老子》中的智慧。比如,抗日戰(zhàn)爭末期,美國人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世界輿論為之紛紛,驚訝這種炸彈之無比威力,但毛澤東馬上制止了中共方面對這一神奇炸彈的宣傳,他的理由就是“老子”式的:八路軍的人數(shù)本來就少,得勝之本貴在英勇,中共部隊聽了原子彈威力的宣傳,肯定不利于打仗,會更多地迷信武器。(可參考《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有關(guān)章節(jié))又比如,中共從蘇聯(lián)遠(yuǎn)征軍手里接收東北之后,得了大量日本精良裝備,強大了自我,但毛澤東也不讓宣傳這些武器,而是有意宣傳“小米加步槍”的威力。如此作法,其“智慧”之高明,那就是鼓舞和凸現(xiàn)戰(zhàn)士們的“斗志”。(參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有關(guān)章節(jié))這樣的宣傳果然頂用,毛澤東最后打敗了蔣介石。至于毛澤東以后犯什么錯誤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得益于《老子》式的智慧則沒有疑問。《老子》的智慧非常重要,也是事實。
余杰似于此不察,斷然把“老子”和《老子》都說成是“反智”,實在有些武斷。時下,王朔有本暢銷書,名字叫《無知者無畏》。這樣的話,套在余杰對待“老子”和《老子》問題上似也合適。
余杰硬把“老子”說成是“靈魂被壓扁了的政客”。這句話無論如何講得不對,老子與孔子比較而言,老子真還不像政客,孔子倒更像些。余杰可能是過于年少,看得多,想得也不少,但觀察和體會得不多,從而得出了這類書生結(jié)論。
正因為余杰有些書生氣味,又對“老子”做了另番解讀:“老子人生哲學(xué)宣講的對象是被統(tǒng)治者,‘曲則全,枉為直,洼為盈,蔽(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在人類的現(xiàn)實世界里,生存的前提成了愚昧。”(《說還是不說》289頁)這些話何以是專給“被統(tǒng)治者”所“宣講”?面對復(fù)雜世界,明火執(zhí)仗、硬碰硬,常常解決不了問題,相反,某些“策略”式的“智謀”恰恰可以有效解決,而“自然”又為我們提供了示范。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沒有洼地,何以屯得住東西(水)?如果沒有某種彎曲,又何來全面(后更演變成了“委屈求全”)?余杰可能是看到“多則惑”就想到了“愚昧”。其實“多則惑”講的是人關(guān)注的事物太多反而會生迷惑。這些話不是講給“被統(tǒng)治者”的,而是講給“統(tǒng)治者”的。退一步講,這樣的道理,即使是講給“被統(tǒng)治者”,那也不是壞事,會讓大家聰明起來,更好地生存和發(fā)展!
其實余杰自己常有些“老子”或《老子》式的“智慧”。比如他在《火與冰》一書第45頁第“十三”個問題上,就說得很好:“石頭。再堅硬的石頭也會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沒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這與《老子》中的“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有何差別?水和流水是再柔弱不過的東西,但架不住它有勢能與耐力,滴水穿石就是典型的“以柔克剛”。《老子》之四十三章開篇就有一句話:“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余杰之“流水現(xiàn)象”就是由“天下之至柔”而變成了“天下之至堅”。在《老子》五十二章中又講“守柔曰強”,皆為同意。顧準(zhǔn)、陳寅恪等人骨頭再硬,即使是日記這樣的秘密“武器”,亦復(fù)如此。余杰等兄弟們骨頭雖硬,但好些話也只是提示甚或曲筆一把,也沒有大膽到在“紙的王國”里直言快語。斗爭常需曲折,硬碰硬未必效果最好。老子講的就是這層意思。余杰可以明白“石頭”和“流水”這樣的“辯證法”,而在解讀《老子》時又成了十足之“反智論”,出現(xiàn)了不小的“盲點”,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智慧”,真是不該。
老子尤其《老子》的智慧在于“無情”和“殘酷”,是“兵家”理論的濫觴。韓非、司馬談、朱熹、顧炎武都看出了《老子》中的“兵家”特征,毛澤東在“文革”中干脆講《老子》就是兵書。從邏輯上講,沒有《老子》理論便無《孫子兵法》。它的中心思想還是前人總結(jié)的“辯證法”以及今人總結(jié)的“不動聲色”,“守雌”、“貴柔”進(jìn)而“克剛”、“制強”等等。如果余杰對這些說法多做了解,不至于只是看了兩眼余英時的某些說法就在“抽屜”里“望文生義”。作為錢穆之弟子,余英時的文章常有不及他老師之處。作為“天才”和“怪才”的余杰,不能因為痛斥了“王府花園”中的郭沫若就忽略郭在史學(xué)上的考證,尤其不能忽略馮友蘭和郭沫若在“老子”和《老子》問題上的重要考證。
并非“東方專制主義的最高秘密”
看見《老子》中的“虛其心,實其腹”就認(rèn)為看出了“東方”問題之所在:“這六字真言道出了東方專制主義的最高機密:給人民一碗飯吃,而不給人民以知識。”這話聽起來很“現(xiàn)代”,進(jìn)而很“自由”、“放達(dá)”,但與這派思想很不吻合。作為“道術(shù)為天下裂”之春秋戰(zhàn)國,包括“老子”和《老子》在內(nèi)的“思想家”們考慮的重大問題當(dāng)然是“救國”、“圖強”。如何救國圖強?自然不是一個君主和一個圣人可以解決,其中“使民”才是重要“出路”。讓百姓吃好,家庭富足,少一些想入非非,眾志才能成城,這才是“救國”之唯一出路。假如“國”中之人個個都是思想家,著書立說,發(fā)表講演,離德離心,都去追求“自由主義”,肯定無法“救國”。好些事確實不是老百姓所能管的。這類問題古今一樣。就像當(dāng)今日本,人人都像傻子,百姓并沒有中國人那么多的“思想”,依舊是“江戶時期”的“勇信”精神彌漫于心,上級讓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新加坡好友多次跟我講,那里的百姓都像是技術(shù)員,只會一種本事,其余不會,尤其不會“侃大山”。這真還屬于《老子》中所講之“虛其心,實其腹”。這些國家都還富庶,人民康樂。中國則情況不同,讀點書的人個個有毛病,紛紛成“侃家”,都有講演癖、權(quán)力癖、思想癖和寫書癖,都有一套又一套之治國安邦、濟世救民的巧妙說法,結(jié)果是人人不團(tuán)結(jié),個個像滑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知余杰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當(dāng)代“東方”之中國,各級政府機構(gòu)也在大力推廣“公務(wù)員”制度。這一制度誕生于“自由主義”之西方。我覺得這種制度也屬于“虛其心,實其腹”的一套,上級指令,公務(wù)員只說模范地執(zhí)行就是,其余別管,也根本用不著你來操心和多管閑事。如果中國社會中到處都是余杰這樣的雄辯之才,社會組織不亂才怪。假如余杰做了“哲學(xué)王”,目睹“理想國”中的個個公民,都是講演家,都是辯論家,都是著作家,都有另一套“理論”和“主張”,更有每個人對付上級的“對策”,不知“哲學(xué)王”的日子又該怎過!因此我們說,“虛其心,實其腹”并非“東方專制主義的高級秘密”,也屬于“西方自由主義”的“高級秘密”。余杰兄弟不能因為聽了某位發(fā)表的老子屬“深陷苦難的文人”的高論,就以為讀懂了“老子”和《老子》。那“五千言”的解讀還未必那么容易。其中糟粕雖多,但主體思想依舊深刻,至今不失為優(yōu)秀“智慧”,正如余杰引用錢大昕話說:“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如果真是“反智論”,豈有“救世”之理!
不應(yīng)錯解“焚書”與“坑儒”
余杰由于痛恨“老子”之“反智”,進(jìn)而火冒三丈地痛恨上了韓非,由于痛恨韓非,更是痛恨上了秦始皇之“焚書”與“坑儒”。點出這兩大“事件”之后,余杰自然又是一番偉論:“這兩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論在政治實踐上的最后歸宿。”這樣的判決盡管“鏗鏘有力”和“擲地有聲”,卻依舊是些情緒性的語言。北大才子也把秦始皇及其“焚書”和“坑儒”讀成了“暴政”的“符號”,而未能讀出大體準(zhǔn)確的史實,實在遺憾。有關(guān)“焚書”問題,倒是余英時的老師錢穆更為“實在”一些。他在《國史大綱》上冊141頁中這樣寫道:“秦代焚書,最主要者為六國史記(即當(dāng)代官書),其次為詩、書古文(即古代官書之流傳民間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間書)非其所重。漢興,學(xué)統(tǒng)未嘗中斷。”可見,“焚書”之事并非那么簡單,涉及統(tǒng)一六國后的“思想去向”問題。至于為何要發(fā)動這場“運動”,錢穆結(jié)合《史記》等多種史料也曾做了細(xì)致分析:“焚書本起于議政沖突,博士淳于越稱說詩、書,引據(jù)古典,主復(fù)封建,李斯極斥之,遂牽連而請焚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jì)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而又附禁令數(shù)項:一、敢偶語詩、書棄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可見當(dāng)時重禁議政,輕禁挾書也。”錢穆還說:“秦雖焚書,史官、博士官仍未廢,著述亦未中輟。下迄漢惠。除挾書律,前后只二十三年。漢廷群臣,亦多涉學(xué)問,名人臣德,雜出其間”。錢穆之說概有所本。劉勰這樣憤恨秦始皇,《文心雕龍》也還能公允而言:“煙燎之毒,不及諸子”。“焚書”事件,并沒有關(guān)上中國學(xué)術(shù)研究之大門。如果秦始皇真把書給燒光了,尤其把“諸子”都燒了,大概余杰連談“先秦諸子”的可能都沒有了。錢穆在政見上與中共相左,既不相信共產(chǎn)主義,又不迷信資本主義,惟相信孔孟之道,最后到了香港和臺灣,甚至是蔣介石的座上客,但在治學(xué)問題上,則沒有含糊,遵守史德,結(jié)論與毛澤東倒有很大相似,應(yīng)該說這是他的“客觀”表現(xiàn)。我這里反復(fù)引用錢穆出場,一是錢穆有些史學(xué)功夫,二是余杰曾有一文將這老夫子剝過“皮”。
郭沫若在毛澤東秦始皇觀念的“指引”下,最后也修改了自己的“焚書”觀。他在《讀隨園詩話札記》一文中說:“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tǒng)一文字,在當(dāng)時實有必要。”也許余杰會說郭沫若是在“諂媚”,不屬于真正的史學(xué)研究,但未必如此,郭論的依據(jù)恰是清代“文學(xué)巨子”袁枚之《隨園詩話》。在大興文字獄的清代,并不得志的袁枚未因憤恨而把秦始皇解讀成“暴政”之符號,而尚能就事論事,公議“焚書”:“秦焚書,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內(nèi)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自蕭何不取,項羽燒阿房。而書亡矣。”顯然,中國之書真正燒毀的不在秦代,而在流氓項羽。余杰之行文立論,顯然沒有考慮甚至未能參考到這些“前人”之“史見”甚或“成見”。
再談“坑儒”。這也不是一個“符號”化的問題,不完全是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據(jù)大牌史學(xué)家顧頡剛先生考證,那是因為當(dāng)時的儒生們參與了欺騙活動,才惹得皇上大怒,將那467個“方士化了的儒生”坑在了咸陽。儒生何以騙人?這與秦始皇的迷信以及追求長生確有關(guān)系。戰(zhàn)國末期,方士吃香,秦始皇也很相信這些人,于是徐福、侯生、盧生還有韓終等人都在他的身邊喋喋不休,描述長生不老的前景和藥物。秦始皇聽后信以為真,遂派這些人去尋寶。結(jié)果,仙藥找不來,人卻逃之夭夭,還在外面說怪話,這下子惹惱了皇上。秦始皇下令進(jìn)行追查。追查的結(jié)果讓人吃驚,原來政府中的不少儒生因方士們的吃香喝辣而早已變節(jié),裝模作樣干起了方士們的勾當(dāng)。顧頡剛所謂“方士化的儒生”指的就是這些人。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兒,確讓秦始皇大為惱怒,便發(fā)生了“坑儒”事件。顧頡剛說:侯生、盧生等方士出事以后,“他(秦始皇)把養(yǎng)著的儒生方士都發(fā)去審問,結(jié)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陽。當(dāng)時儒生和方士是同等待遇,這件事又是方士闖下的禍,連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這件事與‘焚書作一例看,實在錯誤”(《秦漢的方士與儒生》10頁)。聯(lián)系起來看,到了漢代,漢文帝也殺過不少這樣的人,但因為歷史上對之不追究,就好像沒有發(fā)生過“坑儒”一樣。其實“坑儒”是一種“反偽”舉動。當(dāng)時皇帝對方士言論非常相信,因為那里面有不少稷下學(xué)宮似的“哲學(xué)”語文,大家對“理”不死從而“人”也可不死的說法,將信將疑,心存僥幸,愿意一試。秦始皇、漢文帝乃至漢武帝都有過這種“向往”。今天看來這是他們的悲劇,但也有他們的認(rèn)真,那就是如果發(fā)現(xiàn)有人背后搗鬼,特別是像儒生這樣口口聲聲仁義道德者,凈干方士們的勾當(dāng),妖言騙人,自然是格殺勿論。離秦始皇很近的漢代王充對“坑儒”事件則有這樣的看法:“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如果儒生不生是非,不胡言亂語,不對秦始皇進(jìn)行詐騙,斷乎不會“坑儒”。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說:“則知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坑之。”這也說明了“秦時”不曾“盡坑”儒生。秦始皇坑掉467個儒生之后,政府機構(gòu)里依舊大量保存和使用著儒生。否則,漢初就不會有諸如賈誼、晁錯、王臧等眾多大儒生。誠如錢穆所說:“先秦諸子注意教育問題者莫如儒”,“儒家在漢初,仍以友教青年貴族為第一任務(wù)。”(《國史大綱》144頁)。可見,秦始皇再“坑儒”,也沒有破壞“先秦”到“漢代”的“儒教”傳統(tǒng)。
余杰在書中不也舉例說某個大“儒”在“大躍進(jìn)”年代里“科學(xué)”預(yù)報“畝產(chǎn)”問題嗎?這類人不也極像“方士化的儒生”嗎?當(dāng)今,迷信書、妖妄書,虛假騙術(shù)和那些鬼七馬八之徒不也早該被“焚”或被“坑”!問題就在于“焚書”、“坑儒”一旦解讀成“暴政”之“符號”,就有了比暴政一點也不差的問題,就成了余杰這樣的解讀歷史。我以為,文章尤其抽屜里的文章盡可以張狂,但再張狂也不能偏離歷史。
“焚書”與“坑儒”,只是余杰在“老子”問題上所涉及到的兩個歷史事件,立論之義憤可以同情,但偏離史實則讓人費解。
余杰文論中的問題大概不止這些。冷靜想想,我不免要問,余杰為何會有這樣一種寫作激情?觀其“自由的言說”,則可讀其“語碼”。他這樣說道:“在紙上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他也有交代:“我從事寫作是因為:缺乏自信的我需要尋找自信,缺乏溫暖的我需要尋求溫暖,缺乏愛的我需要尋求愛。”原來不寫文章,余杰老弟仿佛棄兒,而寫了文章,“自信”、“溫暖”和“愛”也就可以滿足“需要”。這與需要“過癮”與“幻化”者要抽“大麻”沒有多大的區(qū)別,與弗洛伊德、李漁等人的“白日夢”理論也極相近。
余杰對其筆下文章也自有價值估量:“在我看來,文章絕不是‘經(jīng)國之偉業(yè),不朽之盛事。我知道自己拯救不了什么,改變不了什么,我所做的正如赫塞所說:‘面對充滿暴力與謊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靈魂發(fā)出我作為詩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為例,描寫我自己的存在與痛苦,從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視。”必須承認(rèn),在我們的生活中,確有某些暴力,尤有太多的謊言。有余杰輩挺身而出,應(yīng)該說不只是北大的光榮,也算是中國人的驕傲。在此問題上,我愿忝列其間為余杰鼓掌。余杰的文章總是那么激忿,激忿得讓人喜愛,但也讓人擔(dān)憂。他的行文“立論”就是我之薄憂。
余杰與他同類的朋友都有一個特征,那就是對“自由”的無比向往。
然而,余杰為這“自由”確實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他不說,僅就書中若干“判斷”錯誤就讓人覺得余杰的文章有些“太自由”了。“太自由”必然會成為“自由”的代價和死敵。一些立論過于“頑強”,“頑強”得讓歷史和邏輯都發(fā)生了誤會。余杰曾引郁達(dá)夫話說:“生怕多情累美人”。結(jié)果眾多“美人”還是被余杰之“自由”和多情給“累”著了。正是有感于此,我才為余杰擔(dān)憂,愿意高喊一句,為了“自由”,謹(jǐn)慎、謹(jǐn)慎再謹(jǐn)慎。
我與余杰素昧平生,不曾過節(jié),年齡有別,學(xué)養(yǎng)有異,但渴望“自由”的心則完全一樣。為了愛護(hù)“天才”,尊重“天才”,為讓“天才”更有“天才”之舉動,不得不就其“頑強”的聲音及其某些“盲點”如實說來。誰讓余杰是天才呢!以上意見,大體上不會傷害余杰之“天才”本體,惟愿余杰及其“自由”戰(zhàn)士們行文謹(jǐn)慎,不要“太自由”,免得給自己更給北大帶來“天才”之外的其他說法。忠言逆耳,如余杰不棄,我愿為“天才”們舉杯,觥籌相對,結(jié)為朋友。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