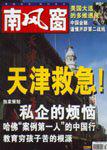彈性管理何時變“硬”?
■策劃:本刊編輯部執行:張哲誠鄭作時

哲人說:存在就是合理的。一個深圳的朋友說:目前的生存環境對于私營企業來講,是建國50年來最好的。在本刊記者走訪了廣東、北京及浙江的許多私營企業之后,的確也得出相同的結論。然而,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解決現實的不合理性,從眾多私營企業家和個體經營者無奈的嗟嘆當中,我們發現在規則的制定和執行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彈性空間,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
在這里,我們暫且不去理會那些政策層面的硬性規定,而把關注點放在各個政府主管部門“原則上要執行的規定”上,以及那些無章可循的“決策”。事實是,這其實是一個游離于法律監督之外的巨大的“軟性”空間,它其中的“規定”,可執行也可不執行,可“嚴格”執行,也可“變通”彈性執行,可即刻執行也可慢慢執行。它直接導致了法規政策環境的不明確、不清晰、不透明,也就不可預見,使得企業經營者在與這些掌握實權的政府“服務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金錢成本,最后可能還使生意泡湯。
這個“軟性空間”的存在,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讓經營者感到,私營經濟的發展始終在一種令人不安的、難以預測的生存環境之中“謀求生路”。這直接來源于一種根深蒂固的對私營經濟的歧視和辦事的低效。
“名正言順”的低效率
前文提到的制冷企業新菱集團,它的設備已被香港圖書館和展覽館引進,對這種大型的設備來講,當然需要工程技術人員提供維護和及時的檢測服務,所以公司急需為兩名工程師辦理多次往返香港的出境證。在所有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仍然被“有關部門”拖了整整7個月才辦下來,結果因為服務不到位,使公司形象大受影響,讓人哭笑不得。
“如果都按這種效率來工作的話,在這種服務競爭的時代,多數情況下,恐怕什么生意都不可能做了!”譚總無奈之下,也十分“理解”個中緣由:假如問科長,他可以說處長沒批;問處長,他也可以說額度滿了,需要排隊等待。總之“解釋權”在辦事機構手上,你對此毫無作為。
番禺有家花園家具廠,他們所生產的花園用家具,全部是外銷的。每年都大約有十幾萬的出口退稅,在去年,只需3天就退稅給企業了,而今年卻拖了半年多,理由很充分——“財務大檢查”,僅憑這句話,就讓本身屬于企業的資金長時間地滯壓,而這時正是企業需要周轉資金的時候。至于是否因為財務檢查,就可以長時間占有企業的資金,并沒有人告訴他們。企業也只有企盼著稅務部門盡快地將屬于企業的財產“恩惠”給企業,而絲毫不敢奢望所遭受的損失得到賠償。
該廠的生產原料也是從國外進口,海關以前要求企業拿出瀕危物種證明,開始只要檢查復印件,后來要檢查原件。而企業突然發現新的規定是:從今年元旦起,國家已經取消了這項檢查。于是急忙告訴海關,而海關卻表示并不知道,當把新規定擺在海關面前時,回答讓人啞然失笑:“執行也需要一段時間吧?”
成都一名小有名氣的私營企業家也深有感觸:“我辦企業13年來,遇到很多事情,本來1個小時或者5分鐘能解決的,可拖了3年、5年甚至8年都不能解決。國家應該制定一部公務員和執法人員的標準化管理法規,誰拖延辦事或者亂辦,造成當事人直接經濟損失的,他要負上法律責任和經濟責任。”
難怪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對現行的政策“沒有一天不關心,也沒有一天不擔心”。
骨子里的歧視
在廣東省汕尾市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館,來了一個派出所的“公安人員”,表示要收取“治安費”,不多,每月200元“而已”。而店主認為此屬亂收費一類,因此據理力爭,堅持不交!扯皮到最后,“治安費”突然被改為“勞工管理費”,仍然要交,然而店主堅持不交。幾天后,主管此事的“公安人員”又來了,對店主說:“我現在鄭重警告你,你店不服我所管理,店里員工的4證(身份證、暫住證、計劃生育證、勞工證)要辦齊喔!”接下來就開始查證件,中午11點(剛好午市開市),店里所有4證缺一者均被帶走了!好家伙,40人的餐館頃刻只剩下十幾個人,只好關門大吉!
全國人大代表、被稱為深圳“土著”居民的私營企業家鄭卓輝,現掌舵一家企業集團,該集團是一家生產銷售發電機、工程機械部件的私營企業,在國內有50家連鎖店。在過去,他最大的愿望是一家大小能吃飽飯,5個弟弟妹妹有書讀。雖然現已不再貧困,但在很長時間里,私營從業者仍被人瞧不起,用鄭卓輝的話說,就是低人九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義平說:“現在民營企業還被歧視。這種歧視是根深蒂固的歧視,是骨子里的歧視。”
今年,某地政府就一幢標志性大樓的自動控制系統進行招標,廣州一家私營企業也參加了競標,本來整個招標過程是非常規范的,技術水平過關之后就看價格。其他的競標者都是國企,如果完全遵循游戲規則,沒有投中是無話可說的,可是偏偏在投標的過程中,因為某領導的一句話:“他們是私營企業,可不可靠?是不是要照顧國有企業?”于是這家私營企業就自然出局了。
這個官員的話只是一種疑問和顧慮,還是對一種原則的判斷,我們無法評估,但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在于,這種歧視是任何現行法規都控制不到的。這種觀念,至今仍然彌散在每一個角落。
執法的困惑
人們總是習慣了從法規的出臺來評判一種“公平交易”和“商業精神”的確立以及進步,而只有經營者自己,才能以切膚之痛去真切地把握自己生存的環境,哪些是能為我所用的資源,哪些是只能望之興嘆的,并且要隨時準備面對不可預見的打擊。
記者所走訪的眾多私營企業主,他們雖然對目前的政策環境和輿論環境都有不滿,但顯然都沒有想要回避,而是在正視自己的生存環境和命運,其中不乏睿智的思想和建設性的意見。他們共有的心聲是:政府應盡快轉變角色,由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到仲裁者和服務者,以便切實營造一個創業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下,信息是通暢的、對等的,所有資源的獲取和享用是公平的;所有法律、法規以及執法本身是透明的,哪些是硬性的,哪些是軟性的,它的彈性有多大;違反規則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是明確和清晰的。
的確,這比整天在口頭上支持私營企業發展要好得多,也更具現實意義。
而當下我們的法制環境以及執法情形又如何呢?新希望的李曉東先生打了一個精辟的比方:十字路口安裝了紅綠燈,然后人們被告知說紅燈停,綠燈行,但是由于人們長期看不到有交警在值勤,于是就有人開始違章,大多數人開始還在觀望,但發現違章的人并沒有被處罰,于是越來越多的人就不再顧慮紅綠燈,慢慢地,它也就形同虛設了。然后有一天來了一個交警,把他所看到的第一個違章者抓住,并且處罰了他。那么其他的人會怎樣認為這個被罰者呢?會認為他違章是咎由自取嗎?絕對不會,而只會認為他倒霉,不走運,正好被值勤的交警看見。
推究下去,如此的執法者只會產生兩種影響,一種是對守法者,他們會感到無所適從,權益也得不到保護,而在心里淡化法規的嚴肅性和公正性;而對于那些一味鉆法規空子的人,則會養成一種心理惡習。社會上不是流傳著一個說法:當打擊盜竊的時候,你就去造假;打擊造假的時候,你就去盜竊。當法律在執行的非公正性和巨大彈性之下備受蹂躪的時候,“執法機關為經濟保駕護航”又從何說起(這里指的“執法機關”包括所有司法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
可笑的是,人們一方面極力呼喚游戲規則確立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養成另一種截然相反的心態:“規矩就是拿來破的。”當執法環境還不能充分透明,執行程序不能公正、公開,違規的代價和成本不能清晰可辨時,我們也只有沉浸在千百年來“擊鼓鳴冤”的舊夢當中去“維權”了。□(圖:新華社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