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在陣痛中摸索新路
翁寶
打破堅冰搟韓國
亞洲以往的經濟奇跡更多是建立在一種國家主導的社會組織結構基礎上,加上亞洲人勤勞吃苦的精神,這是亞洲經濟奇跡的兩個輪子。現在,這兩個輪子都受到外界以及國家內部的質疑。一種講求更具自主性,更代表底層意見的組織結構開始在亞洲試驗,同時,建立創新機制,鼓勵創新的努力,在亞洲國家中更是方興未艾。在新經濟時代,亞洲人的智慧會否促成新的一輪經濟奇跡?這是留給后人的一個懸念,也是此次亞洲企業年會的主題。韓國財政和經濟部長李憲宰在第一天的會議中,就韓國的經濟形勢作了一個綜合性的說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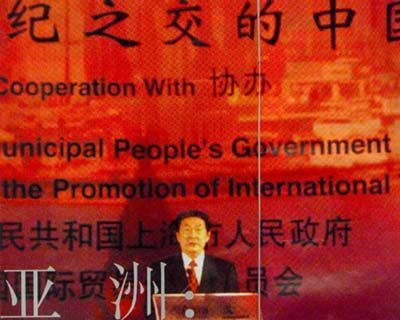
他說:“在解決危機的基礎上,韓國人把這視為是重新起飛的一個機會,韓國現在正著力引進以將來為導向的體制標準。”在談到韓國改革的目標時,李部長強調,社會發展和社會公正之間必須平衡,之后才能再發展。韓國在1999年第4季度取得了經濟比前年同期增長13%的好成績。
韓國1999年全年的增長率為10.7%,是1987年以來最快的一年,今年將會繼續增長,用李部長的話是,“不會低于6%”。由于金大中總統兩年來的一系列游說活動,韓國人開始改變了許多來自民間的偏見,這使得韓國的金融部門更加開放。此舉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達到244億美元,比以前20年的直接投資總額還多。同時,金融部門的發展對推動韓國企業的調整作用顯著,使得中小企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資源,從而促進了高科技公司和與因特網有關系的新公司的發展。韓國正在從“財團王國”變成“風險資本王國”。去年韓國的風險創業企業達到3萬多個,今年將達到4萬多個,發展速度還在加快。韓國風險企業的興起不僅得益于人才的流動,在1997年的經濟危機中,很多的優秀人才脫離了財團,轉身加入了世界性的網絡創業浪潮之中。
同僅僅憑一個網站就自稱是網絡企業的香港風險企業相比,韓國許多的企業在開發技術方面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危機前的韓國,財團一統天下的經濟體制似乎是不可動搖的。韓國社會普遍彌漫著大樹底下好乘涼的風氣,但是,大宇家族最終還是破產了,而原先提倡日本式終身雇傭的三星公司也不得不大幅裁員。三星經濟研究所所長崔玉錫說:現在大家都認識到唯有依靠自己。很多老邁的韓國人不無感慨地說:勇往直前的挑戰精神又回來了。這同朝鮮戰爭之后僅剩下一堆瓦礫的時代氣息非常相似。
創業浪潮無疑對縮小收入差距有利。同時,韓國政府在建立社會平衡的方法上,也是竭盡全力他們出臺了一個“生產性的福利計劃”,即通過工作來獲得社會福利,而非原先單純的福利定義。李說:“對待危機的前提是公開承認面臨的問題,只有坦誠,才能有未來。”李部長在總結經濟危機的教訓時,歸之為道德和原則性的問題,而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與此相類,隨后發言的印尼外長阿爾維·謝哈布的一個比喻得到會場上的一片掌聲,他在講到政治改革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說:沒有政治改革就沒有經濟改革。
就像是用一個很臟的碗盛飯,你是先盛上飯就吃呢,還是先把碗洗干凈?
內容為王的立國之本
人類在音樂方面的發展早期是注意樂器的制造,后來是注意作曲以充分表現樂器的音樂,而到了近代則把競爭集中于指揮與演奏,看誰能利用樂器的表現力最好地詮釋樂曲。信息技術的競爭也與此類似,逐步地從軟硬件性能的競爭向搭載內容的競爭轉化,發展“內容”成了發展信息技術的“生命線”。在信息時代,內容為王倒也是一條確實可行的陽光大道。
一直以來,在立國策略上高人一籌的新加坡人正在這方面從容規劃他們的未來。估計隨著今后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進展,小國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的機會也將急劇增加。新加坡雖然不能獨立生產重要的信息產品,但是,新加坡和美國在運用信息技術、控制資金流向新的經濟增長方面要比其他國家的效率要高。
在此次亞洲企業年會上,新加坡國家科技局主席張銘堅介紹,去年新加坡總共投資100億新元,模仿硅谷模式,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科技孵化機構。正如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此前所說:“我們必須有一種像美國一樣對人才的吸引力。
我們要建立一個人才的硅谷,如果在人才之爭中失敗的話,就如同把一種強大的武器送給了敵人。”
伴著技術的力量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傳播,新加坡政府正在全面推動效率低的企業的不斷進步。在具體的政策上,對傳統的家族企業進行改造,同時對高新技術企業開始減免稅收,張銘堅主席在會上還公開表示,新加坡保證將會出臺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
新加坡的教育一直是引以為豪的話題,以前人們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如果要躋身新加坡政壇高層的話,不僅需要具有東方教育背景,同時又必須擁有西方大學的文憑才行。但是,現在,情況已經在慢慢變化,根據張銘堅介紹,現在新加坡的學校里,強調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是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現在,美國的一些大學直接在新加坡設立分校,為當地培養人才。文化上的嫁接,一直以來是新加坡的立國大計,此舉在一向強調傳統文化的新加坡,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新經濟時代的新嘗試。
在復雜的周邊環境中,新加坡的前領導人曾經提出了“做一條有毒的小魚”的立國方略,并成功在惡劣的周邊環境中長期生存。新加坡的領導人也成為世界政壇上少有的“小舞臺上的大人物”。在信息時代,新加坡人智慧的轉變,我們也能感受得到。
新企業家精神能否扎根亞洲?
研究顯示,在美國等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突出表現在“結構改革的速度”、“支持企業創造的支持體系”、“市場開發的自由度”上領先于其他國家。綜合這三個條件,對于正在進行結構改革的亞洲企業來講,如何“支持企業的創造支持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對亞洲的企業家的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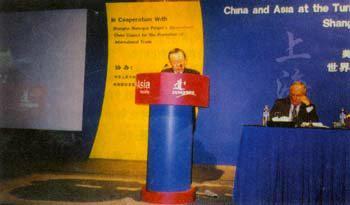
在舊經濟模式中,規模以及市場的早入是一個企業成功的關鍵,但是,新經濟則不同。由此也注定了新舊企業家氣質上、能力取向上的不同。亞洲原先的企業家隊伍中,一般都同原先的社會組織管理結構關系密切。除了因為企業發展過程中,必須充分借助于各方資源包括國家資源之外,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選擇,也決定了管理方式上認同于集權式管理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新的企業家精神必須加上創造力的背景,以及不同從前的管理思路。可以想像,信息時代的競爭和發展模式往往是:企業家必須首先能夠制定一個進取性的目標,這是關鍵性的一步。
然后他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工作,在這過程中耐心并不可取。最后是在新興企業中建立新的團隊精神與合作方式。來自印度十大私營企業之一Mahindra&MahindaLtd.;的AnandG.Mahindra說:“如果還是沿襲舊的聯系方式的話,那么企業的效率就會非常低,比如把許多人招來一個大的辦公室工作的話,并不見得有效率,而且,并不一定是同每一個人實際的接觸才能保持工作的效率。”我們看到許多的老式公司也在發生新的變化,比如韓國一些企業,通過廢除終生職位的風氣使本國經濟的官僚習氣減輕,并且,企業開始全面受到利潤的驅動,而不再盲目于追求數量上的擴大,或者是一味強調趕超。
如果說第一個亞洲奇跡是成千上億的亞洲人辛勤汗水的結晶,那么,下一個奇跡亞洲需要更多的是靈感而不是汗水———以及一種更高級的勞動。前一種勞動模式符合亞洲人口眾多勞力低廉的狀況,那么,更高級的勞動是否能夠同勤勞又有創新能力的人們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地區性大合唱的歷史局面?這對亞洲的企業家隊伍提出了新的課題,即是如何激發人們更多的靈感,而非讓他們流下更多的汗水。亞洲當前的問題不是最終要走向何方,而是如何更有效地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這是一個全球經濟的年代。亞洲人在思考自己未來的位置的時候,應該著眼于“亞洲在世界創新中要發揮怎樣的作用,在技術方面,組織方面能作什么貢獻”這一宏觀主題。
信息時代亞洲的社會問題
信息時代的財富集結方式,企業管理思路,必然引發原來社會結構的松動。在教育背景參差不齊,人口眾多,傳統的農業經濟依然占據社會經濟主流的大背景之下。亞洲同未來的擁抱難免有許多的不協調。在亞洲不少國家,經濟基礎建設以及社會基礎建設還沒有完善,加上社會各階層的關系短期之內難以理順的大背景,新經濟會否在亞洲掀起一場社會性革命,這也是此次與會代表們思考的問題。
幾乎可以想像,在新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貧富分化將會是最大的社會隱患。這點,高盛公司董事經理亨利·康奈爾直言不諱:在韓國,優秀的年輕人積極投身于這場歷史性的機會之中,但是,我們也不能避諱,許多企業的老員工面臨著辭退的風險。而這些人群是現實的社會中的主流力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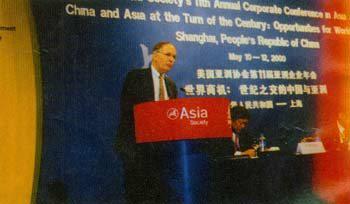
“未來已經到了,只是未來的成果還沒有很公平地分配”,一名小說家如此寫道。在原來的世界格局中,富人們住在北半球的城市里,而窮人們住在南半球的農村里。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在亞洲的許多地區,窮人和富人成了鄰居,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新興網絡企業家同一貧如洗的農民住在一起。社會分配的結果越來越不平衡,而實質的暴力革命就越有可能發生。
幾乎在亞洲每一國的經濟中,都有大批的人沒有能力滿足或者應付這種迅速變化的時代,他們將陷入底層,形成結構上的問題。除非政府提供培訓和再培訓的條件,讓他們重新走上崗位,或者在產業設置上,更多顧及到廉價勞力的長期存在的現實,這對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除了貧富分化之外,在全球化浪潮之下,超國界的非政府組織在地區經濟發展中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樣導致的結果將是現有許多特權階層(原先在地區經濟發展中擁有特權,在社會結構上享有高人一等權利的階層)權力的淡化。這也將會對地區的局勢發生微妙的變化。一方面,亞洲各國政府對新技術的培育應該有新的作用。一方面,又必須直面自己的變革。在新的世界中,政府必須改變他的面貌,必須承擔他的新的責任。擴而大之,全球政府職能的轉變也是不可避免的。電子商務領域的發展可能導致“中介的消失”,同樣,在政治上,充當部分“中介”職能的政府某些部門會否被隔絕出來,變得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