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采山女
● 龐劍凌/文● 宋志濤/圖
1
1942年秋初,我一個人去跑山,去長白山采挖人參。在山腳下的小酒館里邂逅認識了三個人,一個是老把頭徐黑子,五十多歲;一個是三十多歲的長著一雙蛇眼的于松,徐黑子和于松自稱是一起的;另一個是個頭不高,說話不多但很沙啞的黑臉半大小子……不,十六七歲的樣子。
因為都是跑山的,徐把頭歲數又大,他提議,大家不妨結伴而行,彼此之間好有個照應,我們都說好,于是結伴而行。
“跑山”不容易,山道崎嶇布滿荊棘,根本沒路可走,徐老把頭是老跑山的,行動快速,腳步很大,抬腳干凈利落。那于松也不算慢,能跟在徐老把頭的后邊。我緊跟在于松的后面,那個黑半大小子則跟在我后面。
老跑山的很看重山規。在山中行走有喊山的規矩,沖大山喊,沖野嶺叫,故意驚動山蟲野獸,讓它們知道人來了,它們好躲一邊去,喊山也是為了防止迷山,好知道自己和同伴的位置。我、徐老把頭、于松喊的很起勁。唯獨那個黑半大小子不喊也不應,也許他說話太費勁或有什么口齒病吧,我想。
黑半大小子的不喊不應再加上行動不快惹得徐老把頭不時停住腳大罵:“媽了個疤子,你這小癟犢子也叫‘跑山的,這是逛山牎彼婧蠓薹薜叵蚯翱熳卟換贗貳K母鋈訟∠±拉地在山中行走,山高樹密,很快誰也見不到誰了。
前面不時傳來徐老把頭的喊山聲,我在后邊應和著,同時,不住回頭瞅瞅那個黑臉半大小子,有時我也說他幾句:“兄弟,你能不能走得快一點牎焙詘氪笮∽恿呼哧帶喘,始終是一個腳程,他只是看看我,不吭聲,繼續走他的路。
我們趕上徐老把頭的時候,太陽已經快落山了,徐老把頭和于松在一棵大樹下正吃著東西,我坐在離他倆不遠的山坡上也吃起東西來,而那個黑小子坐得較遠,坐在伐木剩下的樹墩子上。
“媽的,小王八犢子犇闥媽的一點山規不懂,這佛爺的位子你也敢坐牬顆淌欽宜饋牎斃燉習淹分缸藕諦∽勇睢U經跑山的人都懂得山規:山上的樹墩子是坐不得的,是留給過往的神靈和佛爺坐的。另外,跑山的除了喊山之外不能亂說話。要說話也得按照山規說,比如在山里遇見耗子,你得稱它為“媳婦”;遇見蛇,你得稱它為“錢串子”等等。
黑小子聽見徐老把頭罵他,趕緊從樹墩子上下來坐到地上。我看見徐老把頭和于松都用一種怪模怪樣的目光瞅那黑小子,尤其是于松的目光更有些古怪,那眼光像能把黑小子穿透似的,黑小子趕忙向別的地方看。
晚上,我們四人和衣躺在傍天黑時搭的窩棚里,四周點燃了篝火。徐老把頭說,點燃篝火能嚇跑野獸,好睡個安穩覺。
這一晚,我、徐老把頭、于松挨得很緊,而那個黑小子在離我有一尺遠的草鋪上躺著,抱成一團,誰也不搭理。
2
山里的早晨挺涼,我們醒得很早,東方已泛出魚肚白,山腰流蕩著濕冷的霧,徐老把頭去山溪邊洗臉,大聲地喊山,喊聲在山林中回蕩,我和于松應和著,而黑小子仍不言不語。
一會兒,徐老把頭回來了,對我們仨說:“我們要進深山了,越走越難走,我有話要說,”徐老把頭大聲道,“大家都聽著,我們跑山的其中有一條最重要的山規,就是女人不能跑山,不能讓女人跟著,誰是女人自動回去,還來得及,也怪我昨天進山心切,直到天黑時才發現我們之中有個女人,真是沒想到的事,請這個女人趕緊回去吧牎
說罷,徐老把頭與于松帶著一種怪樣的表情互相望了一眼,直奔前面的山頭而去。
黑小子沒有動,我這次才仔細打量著他,見他長得小巧玲瓏,臉雖黑些,但很秀氣,問道:“你是女人,裝得真像男人,徐老把頭不挑明,我還真看不出來,怪不得昨晚你不和我們靠在一起呢。”
黑小子沖我罵道:“放你姥姥的屁犑橋人又怎么樣,我跑山誰也管不著,老王八犢子,狗眼怪好使的,我女扮男裝還是給認出來了,真是狐貍的眼睛。”她說話不再是沙啞的聲音,而是尖細的聲音。
我想,這小女子從哪來犖什么要跑山,要做男人做的事情,這年頭兵荒馬亂的,日本人到處抓人,抓女人、抓抗聯的余黨,跑山的人也要多留神,也得多個心眼兒時刻提防著點兒。沒想到今天在跑山的人中竟出了個女的。我跑山的時間不長,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不知怎么辦好,一時僵在一旁。不過,我心里隱隱地感到這個小女子有些神秘莫測。
我聽著徐老把頭在前面的遠遠喊山聲,和解地對黑丫頭說:“小妹子你到底去不去了煵蝗ゾ突丶野,你要是害怕我就送你回家。”我的心是真誠的,沒有半點虛假。我叫她“小妹子”是因為她長得比我小。
“你走你的,咱們互不牽扯,我發現你老是纏著我。”黑丫頭淡淡地說。
我苦笑了一下,尷尬地搖搖頭,我想幫助她,可她半點情都不領。
我覺得面前的黑丫頭不是一般妞兒。
“喂,你等等,你替我背著干糧袋子好嗎煛焙諮就吠蝗凰怠3齪蹺業囊飭稀
我聽了,轉過身來接過她的干糧袋,袋子挺沉。我發現她還有一個小包兒背在身上,用一只手緊緊護著。
就這樣我和那不愛說話的黑丫頭繼續向前走,彼此之間不說話,無論我怎么提話茬,她就是一聲不響。
眼前的霧漸漸地散去,朝陽照著山間,野花絢麗多彩,散發著一股股沁人的濃香。可那黑丫頭好似什么都沒看到似的,只是默默地前行,我覺得眼前的女子真是個“小怪人”。
前面一條小溪攔住去路,黑丫頭蹲下身子手捧溪水大口地喝著,并不時地抬頭看著周圍的山巒。徐老把頭喊山的聲音早已聽不見。但是從倒下的草叢及溪水邊留下的痕跡來看,我斷定我和黑丫頭的路走錯了,但那黑丫頭不聽我解釋,繼續沿著溪岸的草叢,深一腳淺一腳地只管走。
我疾步追過去,攔住她的路說:“我們走錯了。”她閉上眼睛,不看我好像在養精神。突然她睜開眼睛,從我身邊繞過去,繼續趕她的路。我沒招兒了,只得提著跑山的家什——參竿跟著她走。她腳步輕松敏捷,不快也不慢,顯見是個常跑山的。
我們正走著,猛然間我聽見旁邊的草叢中有觸動草葉的聲響,我嚇得尖叫起來。
“你站著別動,我去去就來。”黑丫頭轉過身面無表情,從腰上抽下一把鞭子,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包著鋼條的鞭子。迎著那聲音,她“叭叭”地抽著鞭子走進我旁邊的草叢,我心里雖然擔心,但也很佩服她的膽量。
一會兒,她回來了,右手里掐著條蛇,蛇還在蠕動,并吐著信子。但這條蛇牢牢地被黑丫頭控制在手里。我一看是被本地人稱為野雞脖子的毒蛇,頓時嚇得頭皮發麻,心里打顫。我哆嗦道:“小……小妹子,怎敢拿蛇玩兒?這蛇毒性大得邪乎,趕快打死它牎彼卻笑了:“不犗衷諢共荒苷死這條蛇,我抓它的目的就是因為它的毒性大,這才對我有利……”她還想說下去,但看到我專心聽的樣子,又不說了。轉過身繼續向前面
的山頭走去。這次黑丫頭走得比較緩慢,因為她手中有一條毒蛇。我越來越感到黑丫頭無比神秘了,她決不是一般的跑山的,一般跑山的絕不能隨便抓蛇“玩兒”。我感到她神秘莫測的背后,隱含著殺機。
不知不覺中,紅日西沉了。我們走到一個眾山相會的山坳。黑丫頭停住了,我也停住了。她指著一座山對我說:“從這座山翻過去,這山的半山腰有三間草房,要是點兒正的話,你能碰上徐老把頭。”我問她怎么知道,她白了我一眼,有些不耐煩,玩著蛇說:“信不信由你,我們到此分手吧,不過得還我干糧袋了。”她接過干糧袋子,說走就走,往另一方向的山頭奔去了。我看得出,黑丫頭對這一帶的山道地形相當熟悉,我感到這黑丫頭越來越神秘了。
3
我按照黑丫頭的指點,直奔那座山而去。這時,天幕上閃爍著星星的白光,在這莽莽蒼蒼的大山里只我一個人,使我感到幾分恐懼。說起來,我也算是個老“跑山”的,盡管年齡不大,但走起山道來,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這一次,尤其是遇到黑丫頭之后,我感到有一種不祥之感。難怪徐老把頭說,女人不能跑山,女人跑山是進山大忌。可后來的事實說明,這所謂的“山規”,純盤是他媽的屁話。各位,別忙,我繼續說。
轉眼間,我來到這座山的山崗上,往下瞅看見了有三間茅草房,茅草房的西間和中間都亮著燈光。我聽到西間有喝酒劃拳的吵鬧聲,但分不清是誰。我想起了黑丫頭的話,在這或許能碰上徐老把頭。再說現在天也晚了,管他這個那個的,先找個地方吃飽肚子再說。我疾步朝那草房門口走去。
或許是我的腳步太急了,弄出了聲響。門口忽然竄出一條狗兇猛地沖我而來,我急忙閃到一棵樹后,隨著一陣鐵鏈聲響,那狗滑向了一邊。我好后怕,嚇出了冷汗。虧了狗用鏈子鎖著,要不非把我掏了不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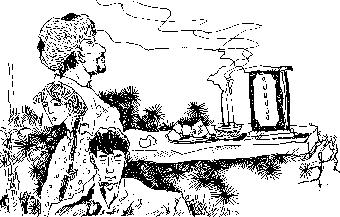
隨著狗的叫聲,中間門開了,透出一股強烈的光,一盞馬燈吊在中間屋地的柱子上,柱旁邊的鍋里散發出一股狍子肉的香味,門口上面冒著熱氣。一條漢子從熱氣中出來,四處望了望沒吭聲,又回屋了,并隨手關了門,可能是我躲在暗處的原因吧,這人竟沒發現我。
我雖然挺餓,但我改變主意了。不能冒冒失失地進屋,要是土匪窩那可就倒了血霉了。我從旁邊繞到了草房后面,沒有驚動狗叫,巧的是西間屋后面有一小窗戶,已糊上了窗戶紙,以免蚊子進屋。窗戶紙不隔音,我聽到里面有兩個人的說話聲音,我聽出是徐老把頭和于松在對話。我剛要敲窗戶紙準備進屋,但卻被他倆的談話驚呆了,只聽徐老把頭說:“于隊長,那兩個雛兒不知上哪去了,能不能跟著來熚易芫醯醚燮だ鮮翹,今個兒準要出什么事兒。”忽聽得于松一陣怪笑:“虧你還是個老跑山的,真是老眼昏花,我看那男的雛兒是個正經跑山的,只是那黑丫頭叫人琢磨不透,我看那丫頭不像跑山的,再說我們也沒見過哪個女的跑山。我看八成像抗聯的余黨在完成個什么任務,我有這個感覺。不過,她再要出現,格殺勿論。”下面是徐老把頭恭維的聲音:“真不愧為植田將軍手下的偵緝隊長,有著蛇一般的眼睛,看事情這么準,于隊長真是高人。”
我聽著他們二人的談話,脊背都發涼,替那個黑丫頭,不,小抗聯擔心,擔心她誤入魔鬼的圈子。在我們這一帶地方,大家最怕的就是縣偵緝大隊長于隊長熤劣謨謁燒飧雒只不過是隨便叫的,他長著一雙蛇樣的眼睛,心像毒蛇一樣陰狠。幾年來,他殺的“抗聯”及其“余黨”無數,光人頭得用車裝,他很受本地駐日軍司令植田的看重。但這于隊長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人們只聞其名,不識其人。只要一提于隊長人們就不寒而栗,當時情況就這樣。
就在我靠窗戶驚恐萬狀之際,聽到里面于隊長冷冷的聲音:“徐老把頭,你剛才不是說眼皮跳要出事嗎犇慊拐嫠刀粵恕!彼婧笫親擁上膛的聲音。情急之中,我忘了害怕,用手蘸著唾沫快速地在窗戶紙上弄了個小眼兒,聲音不大,沒有驚動屋里的兩個人。
透過窗戶紙上的小眼兒,我看見于松熡詼映ぃ犇米乓恢Ф糖乖詒譜判燉習淹,徐老把頭嚇得直后退,邊退邊說:“于隊長,有話好……好說,別殺……殺我牎薄昂謾犖胰媚闥欄雒靼住P旌謐印犇闥,你上山的任務是什么?不光是跑山吧,你的主要任務是給植田將軍送大煙膏。可你每次送煙膏都要到縣城的‘雪蓮藥店去,我查明,這‘雪蓮藥店是抗聯的一個地下交通站,你送的‘貨他們給抗聯的傷員用。只可惜這次送‘貨不會有人接了,他們都升天了。哈牴牴犖冶ǜ媼酥蔡锝軍,植田將軍讓我跟你來取‘貨,因我不熟道路,所以沒有下手殺你。現在你該明白了,對皇軍不忠誠的一律格殺勿論。徐黑子,你死得不冤,抗聯要是知道你為日本人送‘貨,也會處死你的。”說罷,一聲槍響,徐老把頭倒在地上。隨即引起幾聲犬吠。
我仍站在墻邊煷盎е酵獗叩那劍犚歡不敢動,生怕弄出聲響驚動惡魔。
我聽見另一個聲音和于隊長說話了,是這草房的主人熓歉詹拍欽蠖開門沒吱聲就進外屋的人牎V惶他說:“于隊長,何必這么絕情呢熢勖嵌際且惶跎上的螞蚱,都給植田將軍做事……”“放屁犇闥媽的說我絕情,這話有別人說的,可沒你說的。當初,你要不絕情,怎么能把楊靖宇的行動計劃告訴我們熞知道,楊靖宇對你這個警衛旅的參謀可格外器重啊牪還話又說回來,要不是你,恐怕楊靖宇到現在還不能鏟除呢,哈牴牴牴牎庇詼映ひ徽蠊中Α
兩年前的冬天,我在家“貓”冬時聽說抗聯的頭頭楊靖宇讓日本人在縣城邊的樹林子里給打死了,抗聯也給抓住斃了不少,弄得人人驚慌。人們都說是楊靖宇的手下人向日本人告的密,據說是一個什么長,反正官兒不小。
我雖然害怕,但懷著好奇心再一次透過窗戶上的眼兒向里看,看一看出賣楊靖宇的人什么模樣:這是一個高個子瘦削的男人,兩只眼睛賊亮,只是臉焦黃,在不算亮的馬燈下也能看得出此人是個“煙簍子”,歲數在三十五六歲左右。
待于隊長笑完后,黃臉漢問道:“于隊長,我若沒猜錯的話,你來這兒不光是取煙膏吧煛彼蛋,很自信地瞧著于隊長。
于隊長突然用槍指住了黃臉漢的胸口,黃臉漢臉不變色似有準備。于隊長罵了句:“媽的牪灰動牎
“我根本就沒動,不過,于隊長你能不能讓兄弟死個明白。”說罷瞥了一眼旁邊的徐老把頭的尸首。于隊長沒有往旁邊瞅,他大聲說:“好犇閭著,植田將軍長期吸大煙,得了頑癥,現要回日本治療,但是不能說抽大煙得的病,一旦軍部知道,那要犯死罪。植田將軍怕你泄露出去影響他的前程,特派我來銷毀你已經整好的煙膏,還有把你送上西天。不過嘛,你是死定了,這煙膏兄弟不能銷毀,我拿下山可以發一筆大財寬綽寬綽。情況就是這樣,怎么樣,我的‘參謀老兄,這下該瞑目了吧牎彼蛋沼詼映ふ兆嘔屏澈旱斃匾磺,黃臉漢臉朝下應聲倒地。
于隊長見狀,哈哈大笑,笑聲傳得很遠,特別扎耳。門外,狗又叫起來了。于隊長踢開外屋門,沖正在狂叫的狗就是幾槍;狗跟著沒動靜了。就在于隊長哈腰查看西屋地上的大煙膏時,背后一把鋒利的匕首頂在了他的后心上。“怎么熌忝凰饋煛薄骯哈犖以趺椿崴濫亍熡詼映,你知道我為什么沒死嗎熚疑仙澩┳歐賴衣,是當年執行任務時,楊總指揮送給我的,沒想到,今日派上了用場,不過這事我跟誰也沒說過。”
于隊長服軟了:“老兄,看咱們都在一個槽子里吃食的面子上,放小弟一馬吧,小弟終生相報牎
“你小子少他媽的跟老子玩輪子,植田將軍的脾氣我不是沒領教過。兄弟,你死了以后,我拿著大煙膏去發財,到時候給你郵點陰大洋花花。”一陣大笑之后是一聲慘叫,于隊長的尸首像鋸倒的木頭一樣橫在了地上。
我在窗戶外面看到里面的血腥場面,直要吐,腿肚子打轉,還沒等我回過神來,一個我熟悉的聲音飄進了屋:“你這可恥的叛徒,抗聯敗類,我找你兩年多了,今兒個總算老天有眼,讓我來拿你的命來了。”隨后閃進一個人,這人正是那黑丫頭,不,得叫小抗聯,她右手里提著白天抓的那條蛇,蛇信子還在抽動,蛇的眼里放著陰鷙的光,叫人不寒而栗。
小抗聯和黃臉漢在西屋地對峙著,他們之間是兩具尸首,黃臉漢手拿帶血的匕首,惡狠狠地說:“都怪我當初沒瞧得起你這個臭丫頭蛋子,讓你今天成氣候,不過,今天你來了,你是死定了,我打發你找你的總指揮干爹去吧牎輩壞然屏澈合蚯敖身,小抗聯手中的蛇已飛到了黃臉漢的肩上,黃臉漢用刀割斷了蛇身,但蛇頭緊緊咬住了他的左手,黃臉漢持刀沖向小抗聯,小抗聯早有防備,躲閃一邊。
蛇毒擴散,黃臉漢漸漸地手腳動作慢了下來,臉色變為青色,渾身抽搐著,口吐白沫子,最后倒在地上,吃力地說出最后一句話:“這是報應啊牎敝后再沒動靜。
我從窗戶后面跑到屋里,拉住了黑丫頭的手說:“小妹妹,你真了不起,比我們男人都強牎彼看了看我,沒有吱聲,仿佛我的出現是她意料之中似的。
我眼看她用匕首把黃臉漢子的頭割下,把人頭放到屋內的小桌子上。她在旁邊跪下,先從肩上解下干糧袋子,又解下那個緊貼身的小布包,把包打開,里面是幾支香和一個牌位,上寫:先父總指揮楊將軍靖宇之靈位。
小抗聯點燃了香,放聲大哭:“總指揮牳傻犈兒已經給你報了仇,我用叛徒的人頭來祭你老人家的英靈,你老人家閉上眼睛吧,你老人家死得太慘了,死后還被他們給挑開肚子,這些沒人性的畜生,女兒早晚要把他們殺光,求你在天之靈保佑女兒吧牎
聽著小抗聯的哭訴,我也忍不住掉淚了,也跟著跪了下來拜祭英靈。
選自《上海故事》199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