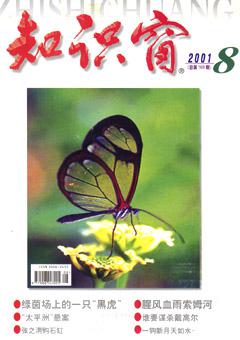“太平洲”懸案
浦泳修
很多人都聽說過“大西國”的故事。可你知道嗎?在太平洋也有個“太平洲”懸案。它們并非像大西國那樣出自某位先哲之口,而是歐洲人在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探索過程中,陸續發現的種種難解之謎,似乎都與另一塊已不存在的大陸有關。太平洲問題的提出,得從一個不起眼的、但隱藏著無窮秘密的小島說起。
復活節島的石像和文字
1722年荷蘭人羅杰文在南太平洋的東南部發現了復活節島。它遠離美洲大陸和其他島嶼,島民們稱之為“基普塔阿基一黑努阿”,意即“大地的肚臍”或“世界中心”。小島只有117平方公里,奇怪的是在島的周圍布立著數百尊高大的石像,一個個背海而立。石像中高的有10數米,面有胡須,頭上都戴著圓筒狀的紅帽,臉型全不像島民,一付威嚴高貴的氣度。石像雕刻精細,栩栩如生。全島大約布立著500座這樣的石像,采石場里還有約150尊沒有完工。而在羅杰文發現它時,島民還處在石器時代,既無巨木又無粗繩,如此高大的石像、石帽又如何拉運?當時尚處在這樣落后階段的土著,他們的祖先又能先進到哪里?假定上古時代的先民比現在的先進,或者假定,那時在島上居住的是“史前文明的民族”,可小島的自然環境也容納不了許多人啊,哪有人力物力來開展如此浩大的工程?再說,這些石像都代表誰呢?奇怪的是島民們對石像的歷史竟一無所知。種種疑問吸引了世人的好奇,許多人紛紛來到島上想探個究竟。
既然小島本身無法承受如此浩大的工程,人們自然會想到,必有顯赫的用戶需要這些石像,這個島只是工場而已。可復活節島距周圍的大陸和大島都十分遙遠,在古代,誰有這個能力把數十噸重的石像一個個地搬到船上外運?于是有人懷疑,莫非復活節島原本與一塊大陸相接?在這塊陸地上居住著眾多的人口,有很強的中央集權。唯有這樣,才可能由當權者調撥眾多的工匠、物資來支持工程。1838年,有人在島上發現了一種誰也搞不懂的象形文字,那時島上只有幾個人還多少懂得這些字符的含意。就小島居民本身,沒有必要書信往來,而島上居然發現了文字,這不就間接地隱喻了,他們的祖先曾經生活在一個地域廣闊、相當發達的國度里嗎?
神奇的太平洋諸島
早在復活節島發現以前,一些研究太平洋的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就感到奇怪,在這些星羅棋布的海島上,生物種群和居民種族中怎么會有那么多的難解之謎?
那么海島上最初的物種是從那兒來的呢?
最直接也是最簡單的通途是隨海流漂來的,但這對陸地動物是比較困難的。只有個別的“游泳高手”才能作遠距離遷徙。如在印度洋的可可群島上,就發現過900公里以外的巽他群島才有的鱷魚。這種鱷魚可算作遠渡冠軍了。河馬、水牛、北極熊、馴鹿等大型動物也能橫渡數十公里的海峽。可淡水魚及兩棲動物是決不敢橫穿海峽到他鄉“定居”的。它們都是怎么“擺渡”的呢?達爾文作出了解釋,他發現,這些動物可以攀附在樹桿、草束等漂浮物上,“移居”他鄉。植物則借助候鳥把種子撒落到遙遠的地方。當然人類在轉移生物的棲息地上更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有時甚至徹底地改變了當地原有的物種結構,這種事例已不勝枚舉。
可是也有一些物種的轉移,用上述“航渡”、“空運”、“人為”等途徑是難以說通的。例如,在太平洋中部的斐濟群島,那兒竟生活著東半球才有的飛龍蜥和美洲才有的鬣蜥,還有一種蟒蛇和三種青蛙,也是在周圍的島上都沒有的。誰能相信,美洲的鬣蜥竟能橫渡上萬公里的水程,游到斐濟列島,更不用說,生活于淡水的青蛙怎么可能人海游泳?而在斐濟東側的薩摩亞和湯加列島上,還生活著巨蟒和巨蜥,這些物種根本不可能自己過洋涉水地來到這里,只有船載或陸路才能把它們帶到島上。可哪會有船肯把如此可怕、又無經濟價值的動物運到島上去呢?這么說來,這些島嶼難道原本有條“陸橋”與其他大陸相連?還有一些植物的分布也讓人產生這種猜測。像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島,距周圍的陸地都在數百上千公里,那兒竟集中了各大洲的植物種群,堪稱“植物王國”,這也是用“偶然因素”難以說通的。于是有人推斷,或許夏威夷群島原本與其他大陸或島嶼至少有“陸橋”相連。
布朗的論據
在20世紀20年代倫敦出版了《太平洋之謎》一書,作者是當時研究大洋洲的權威布朗。此書以復活節島上無法理解的文明為線索推斷說,復活節島或許就是太平洋國王和貴族們的陵墓,島上的石像就是這些統治者的雕像,所以個個神態威嚴,氣度非凡,目空一切。除此之外,還在島上發現了象形字符和許多獨特的雕像,這些都體現了原來太平洲的高度文化。
如果認定復活節島是太平洲顯貴們的寢陵,布朗進而推測太平洲的首都應當是此島西側有幾千公里之遙的波納佩島。波納佩島是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中的一個島,面積僅18平方公里,由數十個小島人為地連成。19世紀就在島上發現了龐大的古建筑遺址。殘留的城墻全由厚厚的玄武巖堆砌而成,大的石板重達25噸,不知用什么方法提升到了20米的高度。像這樣的工程如果沒有數以萬計的工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若以該島為中心,在半徑2000公里的范圍內,也找不出2千個石匠,他們都散居在各島,相互的間距有上百成千公里。怎么能想象,為了建筑這座古城,竟把他們從各方召來,且乘用的竟是那么簡陋的獨木舟,那可能嗎?所以布朗認為,此島曾是一塊陸地的一部分,那兒曾生活著眾多的居民。
為了證實自己的推測,1913年,布朗來到了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沃萊艾環礁,在這個居民不足600人的珊瑚島上,竟有5人能使用一種從不曾見過的獨特象形字符。就是說,在太平洋東邊的復活節島和西邊的沃萊艾島上都有這種神秘的文字。布朗再次肯定,這是一種曾在大洋洲范圍內廣泛使用的文字。而文字都是在國家形式初具規模之后才會產生的呀!于是他堅信,這兒曾有過一個強大的國家。
冷靜的分析家認為,雖然布朗對“太平洲”的推斷令人懷疑,但他所發現的奇特現象和提出的種種疑點應予重視。
科學尚難定論
在布朗發表《太平洋之謎》時,人類對大洋海底的了解還不如對月亮表面的清楚。只有當回聲測深儀在航海上得到普遍應用之后,才使我們對海底的地貌了解得越來越細,可那已是二次大戰以后的事了。這才有了20世紀地質學上最大的一項發現:原來在世界大洋的洋底,有一條貫穿五大洋、總長約6萬公里的海底山脈。太平洋東部洋底的隆起就是這條山脈的組成部分。這個東部隆起的規模極大,高度1~3千米、寬度常超過2千公里,全長竟達到1.5萬公里。由復活節島至赤道是它的中段,而離復活節島不遠的東面,還有一片水下高地。這些地質學上的發現,使太平洲的探尋者們大受鼓舞。或許,這里不僅有復活節島,可能還有其他的陸地或島嶼。如果事實確是如此,那么這兒曾經有過太平洲的假設不就有科學依據了么?
聲學儀器不僅使深度測量成為易事,還為了解海底的地貌和地質結構提供了可能。有了這個儀器,海洋地質學家們驚訝地發現,原來洋底與大陸的地殼構造有很大的區別。
先不說別的,就地殼厚度來講,大陸地殼的平均厚度有33公里,最厚處可達60~80公里,可大洋地殼平均只有5公里,最厚處也不超過10公里,洋殼要比陸殼薄得多!再有,在層次的結構上也不相同。大陸地殼除表面沉積層外下面有二層結構一一花崗巖層和玄武層;而在大洋下面,在很薄的沉積層下只有一層玄武層。
1969年著名的美國“格洛瑪·挑戰者”號大洋鉆探船來到赤道太平洋西部做了鉆探。有些區域的地質結構出乎專家的意料,那里取上的巖心樣品競不是玄武巖,而是大陸地殼獨有的花崗巖(更深的玄武巖還沒有觸及到)。這就證明,這塊接近澳大利亞的洋底原本是一塊陸地,換句話說,太平洲的存在雖然疑點重重,但從地質角度來看,還真不能排除這個推測。
人們原本寄希望于海洋地質科學能對太平洲的存在作出明斷,可結果仍是云里霧里,太平洲的懸案依然是個未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