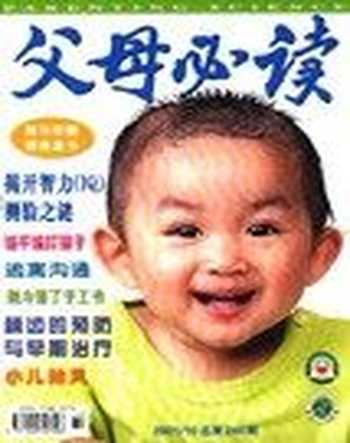派遣
●李子勛
不少研究教育的學者認為,“望子成龍”是當今社會對孩子無休止施壓的心理根源,呼吁家長們應該對自己孩子的能力有一個恰當的認識,并給予合理的期待,不然的話,欲速則不達,反而幫了倒忙。人有不一樣,花有千樣紅。
家長恰如其分地引導自己的孩子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在我看來,“望子成龍”其實是一個跨文化現象,東方如此,西方亦如此,區別只在各自期待的內容有所不同。西方人比較重視孩子的獨立,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東方人重視孩子的孝順,能被社會認同——學習好。在中國的文化原形中,教育的意味本就大于慈愛的意味,許多代代相傳的故事都在強調“嚴教方能出孝子,黃荊棍下出好人”。
望子成龍甚至可以引申到自然界,許多生物(動物)種群會強迫孩子學習求生的本領,鼓勵它們超越父母,父母甚至甘愿做犧牲品。現代學把這種現象稱為一種“基因意識”,即每種基因群都有一種要求自己被無窮復制、放大、延續的自私。望子成龍何嘗不是父母親期待從孩子的生存發展中得到一種自我 生命價值被延續的內心滿足,這顯然就是一種人類固有的心理特性。當然,我們會覺得二十年前中國的望子成龍現象并沒有像現在那樣的被夸大與濫用,如我們的漫畫里,對孩子能力的期待已經到了一種極端情景。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源于我們社會的家庭構成。在多子女的家庭里,父母對孩子的期待會被自然地分類,對能力強的孩子期待會大一些,對能力弱的孩子可能會遷就一些。
精神分析學家艾爾弗德·阿德勒認為,子女在家庭中的排行不同決定個人的心理位置不同,父母對他的心理期待也不同。一般地說,老大是一個特殊位置,被關注和承擔責任較多,從小發展也比較好。老二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常常期待超越老大贏得父母的關注,所以,如果老大很優秀,老二的心理壓力就會很大。老三與以后的中間的子女,會有被擠出局的感覺,如果他們不是出奇的優越或出奇的搗蛋,父母給予他們的關注與期待會少一些。老幺卻是家庭的寵兒,被父母關注縱容很多,內心幼稚,行為卻往往最易離經背道。獨生子女的心理特征既像老大又像老幺,父母會把對后輩所有期待和嬌寵都壓在他的身上,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欣喜感和挫敗感都會很強。
心理學認為,這里存在一種家庭內部的心理補償,父母無私地為孩子辛勞付出,孩子必須努力發展,為家庭爭回一定的優越感來回報父母,這仿佛是天經地義的事。就眼下來說,孩子們對學習以外的多種興趣或愛好都可能被社會和父母冠以不務正業,要么就非得讓孩子在某個業余愛好中出類拔萃,把一種簡單的娛樂放松、陶冶情操的樂趣轉變為一種求生的壓力。兒童心理學家斯迪爾林提出了一種親子關系中的派遣理論,認為父母把自己成長中的未竟事業和期望過度投射給孩子,造成一種派遣過度,使孩子成長中心理負荷太重,不容易體驗到成長中的自我滿足,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反過來,父母過多地關心自己,不愿意被卷入孩子的教養中,又會形成派遣缺失,使孩子缺少階段性目標,阻礙了孩子的成長期望。讓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是斯迪爾林在家庭治療中的主導方向。
在一個家庭里,無論孩子有多少煩惱或行為方面的問題,只要學習過得去,家庭一般不會帶著孩子去找醫生。一旦孩子的學習不好,家庭很容易從孩子身上找到“原因”。在我的門診里,我會問:“如果你的孩子的心理問題治好了,父母怎樣看出來?”父母的回答常常是:“孩子能夠愛學習和學習好。”有一個家庭,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經濟不錯,孩子的學習環境和條件都很好。父母事業有成,對孩子的期待也高,打小就讓她學外語,畫畫,鋼琴考級,游泳比賽,可謂全面發展。可偏偏到了十四歲(初二),女孩得了“社交恐懼癥”,見人就臉紅心慌,嚴重的時候不能堅持上課。父母雖然好強,看到如此痛苦的孩子不得不軟下心來,給孩子充分減壓。
孩子的上學成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本是班上的尖子生,不久就成了學習的“困難戶”。家長處在兩難情境,內心焦慮日漸明顯。面對這樣的家庭,心理醫生不會鼓勵家庭繼續替孩子減壓,而是要父母看清家庭內部的互動是如何把孩子的“問題”放大的,父母需要維持一種家庭的內在規則,比如,承認社交恐懼會影響孩子的人際感覺、情緒,或者也會影響她學習的效率,但不會影響她的生活和學習的行為與規則。我們常常會對家長說,真正的問題不是“社交焦慮”,這種焦慮人人都會有,人人都要過這關。真正的問題是焦慮引發的“逃避行為”,不鼓勵逃避,甚至父母有意減少對孩子焦慮的關注,會使孩子的麻煩自然減輕。心理醫生在幫助孩子學會自我放松的同時,會著手為孩子重建一種行為規則,去完成一個學生應該完成的學習任務。
看起來,像是心理醫生在替代父母來給孩子施加壓力。心理醫生這樣做是看到“問題”給孩子帶來的獲利,社交焦慮使她可以不遵守社會規 則,隨心所欲,還能逃避父母的責難,這樣的獲利使問題有被慢性化的可能。如果心理醫生過多地關注孩子的癥狀,也可能會強化了孩子的病態心理,使她被固著在對疾病的恐懼中。所以我們會故意忽視一些癥狀,把關注放在孩子表現正常的那些生活情景里,給她一個她自己滿不錯的暗示。我們不把“病”看成是一種被外部強加的東西,而把它看成是孩子內部愿望的一種“婉轉”的表達,把它解讀為一種與父母互動中的需要。這樣,問題的受害人就演變為問題的行為人,由此鼓勵孩子做新的選擇。我們甚至會裝著很驚訝地問孩子:“你怎么做到讓‘焦慮來控制你?怎么做到自由自在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我們會裝著欣賞她,說她很特別,有特別的辦法來應對別人應付不了的事情。我們不去責難父母,或批評望子成龍的社會意識,相反,我們要建議孩子接受現實,主動與社會主流意識保持一致。我們會和孩子討論行為的階段性目標,這個目標不是治病,不是學習,而是孩子的身心發展。
同時,我們會鼓勵家長去關注孩子的進步,給予及時的正面鼓勵,強化她的好行為。如果心理醫生只關心孩子的癥狀,傾力訓練孩子應付焦慮、恐懼的技術,或為她設計行為脫敏治療或暴露療法程序,以為孩子掙脫了社交恐懼一切都會萬事大吉,這樣的心理醫生只能算半個心理醫生。只有在幫助孩子處理焦慮的同時,又要孩子學習與焦慮做朋友,把焦慮看成是人生的一種情緒常態,看成是一種可利用的發展動力的醫生,才具有心理醫生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