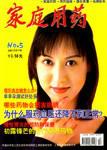消除誤導,走出誤區,控制好您的血壓
趙光勝

我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在對高血壓病的認識和防治的問題上,存在著許多誤區,務必進行糾正。
一、對血壓正常標準的“下調”不必心存疑慮什么血壓算“高”,事關高血壓診斷和防治的根本。但直到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血壓協會和美國對此才取得共識:小于140/90毫米汞柱為“正常”,血壓的正常標準下調了。需知,血壓水平和心腦血管病發生率間呈連續的相關關系,即血壓越高,并發癥發生的危險越大,并不存在能截然區分有或無危險的分界點,這需要長期、大量和前瞻性觀察才能大致判定對心腦血管病基本無負面影響的血壓“理想水平”,即近年來國際準則所建議的小于120/80毫米汞柱。據統計,經治療后的病人,即使血壓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其血壓水平仍高出正常人一大截,無怪乎前者并發心腦血管病的機率仍高數倍呀!所以,在允許的情況下,不能滿足于小于140/90毫米汞柱的目標,應盡量使其更低些。
二、厚“高舒張壓”、薄“高收縮壓”的錯誤觀念必須更新知道“高收縮壓”的危害甚至大于“高舒張壓”已30年了,現已將其與舒張壓一樣作為分級(期)的依據,例如收縮壓在140~159毫米汞柱便是Ⅰ級(期)。然而迄今在諸如掌握開始用藥時機,降壓目標、分級、入選對象標準、評估預后和療效等上,依舊厚“高舒張壓”、薄“高收縮壓”。以往的舊規定也未觸動,例如,保險公司“收縮壓=100+年齡”的公式顯然是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高收縮壓可以增高,其實這種認為是不科學的。1978年我們在鄭州全國會議制訂、現仍廣泛沿用的“療效標準”,規定收縮壓需降30毫米汞柱或以上才作“有效”(舒張壓只需降10毫米汞柱)、且不設“顯效”,也該修正!老年時收縮壓遞升而舒張壓反低的“單純性收縮期高血壓”多,只按舒張壓、不依收縮壓評估預后更是貽害大矣(老年舒張壓愈低愈不好)!
三、防治高血壓的目標不單純在于降壓,而應著眼于心腦血管病罹患與死亡的減少高血壓固然是心腦血管病發生和發展的重要“危險因子”,但尚有其他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凝等多種代謝異常因子對其施加負面影響,應該一并檢出和防治。上述諸危險因子還存在累加效應,合并包括高血壓在內的多種危險因子者系“高危個體”,應是一級預防的重點對象。不認為危險因子的某水平系“正常界限”;而是強調其遞增效應,以最佳區間為“理想水平”(如血壓)。從血壓水平、其他危險因子合并數目和強度、罹患心腦血管病及其他疾患等作綜合性危險評估,從而對應否藥物治療和力度做出個體化判定,是近幾年來心腦血管病預防領域最重要的戰略轉移和進展。據此,對血壓輕度升高、卻合并多種其他危險因子的,也需積極治療。合并糖尿病的高血壓病人,降壓更要小于130/85毫米汞柱;有腎病且尿蛋白排出每日大于1克的高血壓病人,要降至120/75毫米汞柱以下等等。
四、達到降壓目標后決不可就停藥和某些急性感染疾病不同,高血壓病是由遺傳與環境內外因結合生成,乃機體對升降壓平衡機能的失調結果,目前的治療尚難對其根治,需要長期規律性治療。采用小劑量一般不會因長期應用而產生耐藥性和大的副作用,所以大可不必顧慮。據報道,病人經治后血壓正常已一年后停藥,僅約15%血壓維持“基本正常”,一般應遞減劑量至“維持量”,當血壓復升時又需恢復。
五、“復降片”治療不但沒有過時,而且要大力倡導我們在1965年提出小劑量復方降壓治療的配伍原則和處方,數十年來“復降片”廣為流傳應用,深受廣大病員和醫生的歡迎。現在,國際準則已予倡導,但復降片“過時”,甚至“有害”之說卻沸沸揚揚。其實,老藥既有缺點,也有經驗多、了解深等長處,新藥也不一定完美無缺;藥物副反應一般與劑量大小成正比,今日的極小劑量怎能和數十年前大劑量時同日而語?即使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也高度重視藥物的效/價比值,摒棄價廉、有效、副作用小的“復降片”,國家、集體和個人如何長期承受得起?據不少大型臨床試驗報道,約2/3血壓已控制的病人需要2種或以上的降壓藥,既然如此,為何不在早期就用復合治療?
據我國1991年統計,經治療后血壓控制率在城市僅4.1%,在農村更低,僅0.9%。如能消除上述誤導和誤區,則將大大有利于高血壓控制率的提高,從而十分有益于心腦血管病的防治,其作用比單純掌握某些降壓藥的方法不知要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