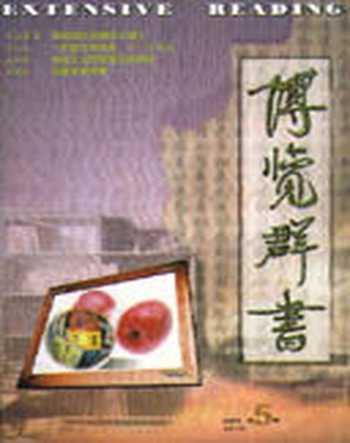“心橋”跨越“代溝”
李城外
這算得上是一篇“命題作文”。前不久,我晉京拜訪75歲的翻譯家文潔若先生時,她送給我一本蕭乾和兒子蕭桐的通信集《父子角》(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牐囑我寫篇書評。我馬上答應下來。一則因為蕭老生前曾幾次接受我的采訪,他老人家辭世快三年了,我卻尚未寫點紀念文字,現在正好聊表懷念之情;二則“父子角”之名,就出自原文化部咸寧“五七”干校,而我正在從事向陽湖文化研究,這本書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也有必要向更多熱心關注“文革”史的讀者推介。
我們先看蕭乾眼中的向陽湖。據《父子角》“代序”介紹,1971年冬季,蕭乾舉家下放鄂南向陽湖已有兩年,他生怕蕭桐沉湎于捉蛇喂鷹而耽誤前程,便有計劃地輔導兒子學習英語。父子倆經常去一個叫王六咀的小村角落,在那里一呆就是大半天,蕭乾戲稱之“父子角”。由于這段人生經歷彌足珍貴,以至從1977年到1999年間,百余封往來信函中還時常提起。如蕭乾在信中深情地向兒子表白:“每當憶起‘父子角,我心里就無限溫暖。”(993年9月8日)時隔五年,老人又敘述道:“昨天晚上還想起咱們父子倆半夜去看什么井,又有一回想起同去452高地回來的路上。那陣子(干校)是我的苦日子,你的存在減去了一大半苦!如今追憶起來,還是很親切。”煟保梗梗改輳對攏玻慈眨牎—不難看出,晚年的蕭乾已將兒子視為除夫人之外最親密的談心對象,遠離父母的蕭桐也成為父親最難得的忘年知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座“心橋”是架在向陽湖上的。熟悉咸寧干校歷史的讀者也許還記得,蕭乾生前曾為鄂南留下兩幅題詞:“深深地懷念咸寧和向陽湖”;“向陽湖是文革時期我們的避難所”。竊以為,《父子角》的文字是對它們最好的詮釋。
下面再看蕭桐筆下的父親:“回想干校那三年,我眼前總浮現出在泥濘烈日里頭戴草帽、肩扛一鐵锨的知識分子隊伍,其中就有憂愁滿面的爸爸在深一腳淺一腳地趕路……”干校的磨礪使尚未成年的蕭桐“早熟”,他學會關心長輩,體貼雙親。更難得的是,他開始接觸社會,思考人生。可以說,蕭桐之所以日后成為一名活躍于美國畫壇的年輕畫家,向陽湖水一直是他隨身攜帶的“健力寶”如在干校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等等。難怪蕭乾有次還表揚兒子:“這次去新疆,你沒有失掉當年干校插隊的吃苦精神,使我十分欣慰。”1991年9月7日對照蕭桐,我不由得聯想到現在的中學生們。時下一方面強調素質教育,一方面又是應試教育的體制,沉重的書包壓得學生們喘不過氣來為了獲取高分,他們不得不死背一些也許考試后對今后的人生再無一點用處的“知識”,而令人擔憂的是,他們中不少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林彪、“四人幫”何許人也我不禁要發問,他們僅僅吃穿住行無憂無愁,就一定比在“父子角”中成長起來的“向陽花們”快樂嗎?我們做父母的視為無限幸福的獨生子女們,他們自己真正感到幸福嗎?他們不知道什么叫“戰天斗地”,什么叫“忍辱負重”,如果遭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如何?他們將來就一定會比蕭桐們有出息嗎?誠然,“文革”應徹底否定,“干校”是錯誤路線的產物,但向陽湖文化人子女的成長史和蕭乾的教子之道,對培養下一代健康的體魄和健全的人格,仍是不可或缺的輔助教材。
捧讀《父子角》,我體會出這里的父愛,絲毫不遜色于偉大的母愛。全書既洋溢著父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又有尊重兒子作出有悖于父親意愿選擇的理解;既有父親對兒子的厚望,又有兒子給父親的慰藉。通篇是“舔犢之情”,卻沒有干巴巴的說教;滿紙是“寸草之心”,而沒有軟綿綿的撒嬌。蕭氏家書讓人感嘆,世間的幸福莫過于父子成了朋友犓又促使人思考: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讀畢《父子角》,我由衷地相信,兩代人之間只要平等相處,以理解架起“心橋”,是可以跨越任何“代溝”的。蕭桐曾致信父親:“您是我最崇敬的人之一,您一生中的浮沉悲歡,我了解不少。許多感情我都是能自覺親身體驗的。冒昧地說,我很像您。”煟保梗福材輳吃攏保踩眨犖掖酉敉┥砩峽梢鑰闖魷羥的身影,也祝愿天下善良人們的兒子都不僅形象上酷似乃父,更要力求達到和父親心靈相通、品格承傳的境界,這才是真正做到了生命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