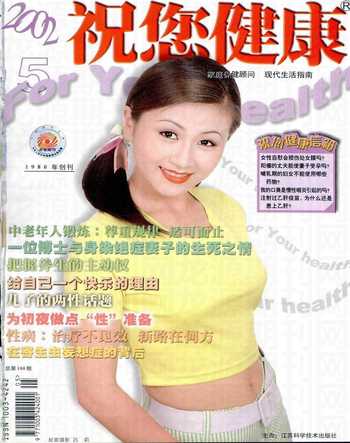一位博士與身染絕癥妻子的生死之情
河 川
100年前,美國作家歐·亨利在《麥琪的禮物》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圣誕前夜,一對囊空如洗的年輕夫婦都想送給愛人一件貴重的禮物。為此,妻子賣掉了自己的秀發,給丈夫買了一條白金表鏈;丈夫卻賣掉了金表,給妻子買了純玳瑁的發梳……
100年后,一對中國夫妻用生命演繹了更為凄美的故事:為幫助丈夫完成學業,在大學任教的妻子東渡扶桑去打工;為照料身染絕癥的妻子,身為博士的丈夫辭去了系主任職務,放棄了發展的機會……
這是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
1986年,哈爾濱的日語教師王信赴日本進修了。這對一個學日語的人來說,真是件大喜事兒。王信在日本的上越教育大學研修了一年。第二年,轉入筑波大學。王信渴望能在日本多學幾年,能拿到碩士學位。第三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日本崎玉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作為自費留學生,經濟的拮據、生活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他不僅要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攻讀學位,而且還要外出打工,靠打工賺的錢來讀書和生活。隨著學習逐漸深入,王信漸漸感到難以應付這雙重的壓力了。
1988年3月,32歲的徐曉微毅然飛往日本。她——一位大學教師,舍棄了即將到手的講師職稱,赴日本打工,以幫助丈夫完成學業。
在日本,曉微的最大痛苦不是打工的難堪與苦和累,經過幾年北大荒鍛煉的她,干活踏實、潑辣,使挑剔的日本人也十分滿意。她最大的痛苦是,王信等中國留學生在攻讀碩士、博士,而她卻在角落里努力打工,空耗生命。
王信是位情感細膩、善解人意的丈夫,他知道曉微內心深處的痛苦,他經常安慰曉微說,他學成后,一定要為她打工,讓她去美國或加拿大留學。曉微期盼著那一天……
1990年,王信考取了日本東海大學日本語言與文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隨后,他們把家搬到了川崎的麻生區,又托人將分別數載的6歲女兒帶到了日本。他們一家三口終于在日本團圓了。
日子在夫妻的奔波勞累中一天天過去。王信的博士研究生將要畢業了,他已聯系好了國內接收單位——北京某學院,并且談妥一家三口人都進北京,王信當日語教師,徐曉微做英語教師。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要來臨了……可就在這時,曉微卻莫名其妙地時常頭痛,王信便勸她去醫院檢查檢查。因為日本醫療費很高,曉微舍不得花那些靠辛辛苦苦打工掙來的錢,王信催緊了,她才去了醫院。
那天中午,曉微從醫院打來了電話:“醫生說,左腦可能有問題,片子上有一個白點。”王信聽罷憂心如焚,立刻騎上摩托,趕往醫院……醫生告訴他,徐曉微必須住院治療。醫生說的醫學術語王信聽不大懂,但是他從醫生的表情和口吻中得知她病情很重。
曉微住進了醫院,她為自己的病而感到恐慌,為自己不能打工還要支付高昂的醫療費而內疚和不安。她發現同病房的那些腦瘤術后的患者,不是昏迷不醒的就是癱瘓在床不能動彈,她更加惶恐不安了。遙夜沉沉,難以人眠,她望著窗外的星斗,一邊想著自己的病,一邊思念父母和家鄉那條奔流不息的松花江……
她對王信說:“王信,我要回家,我要回哈爾濱!”
王信忍著內心的痛楚,耐心勸慰著她:“這里的醫療條件比較好。我們等手術做完之后就回國,回去看望我們的親人……”
1992年11月27日,曉微做了開顱手術。王信提心吊膽地守候在門外,他默然祈禱著:千萬別是惡性腫瘤啊!結婚10年來,她還沒有享過福。為了我。她拋家舍業、遠渡重洋來日本打工,我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9個半小時過去了。這9個半小時對王信來說,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斜陽下的影子,長長的,暗暗的。手術做完了,醫生把王信叫過去,語調深沉地說:“她得的是惡性腫瘤。病灶沒有徹底切除。如徹底切除的話,人也就徹底廢了。手術后,她可能有一段最佳狀態,你們就趕快回國吧。”
王信猶如一頭跌進了無底深淵,他感到骨軟筋麻,汗水伴隨淚水潸然而下……
1993年9月,王信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攜妻子、女兒回國了。他望著舷窗外的日本海悔不堪言:為了一紙文憑,妻子染上了絕癥。他多么想用那張渴望已久的文憑換回妻子的健康啊?可是這到哪兒去換呢?
王信回國后,想放棄生活和工作比較優裕的北京某學院,重返哈爾濱。他想讓曉微在父母和親人的身邊愉快地度過最后歲月。對此,曉微的父母也表示同意。可是,曉微堅決不同意,在日本“洋插隊”吃的那些苦,不就是為了王信回國后能干一番事業嗎?在曉微的堅持下,王信在北京某學院報到上班,曉微和孩子暫居哈爾濱,她一邊養病,一邊等待北京的住房分下后再過去。
1994年1月,病情稍穩定的曉微在王信的陪同下又來到了日本,他們在京都游玩了6天,要去依豆半島,曉微的頭突然痛了起來,脖子也變得僵硬了,不得不中止旅游,去川崎復查病情。日本的醫生認為,還需要手術一次。于是,曉微在日本做了第二次手術。
王信工作不到一年,就擢升為日語系副主任,主持系里的工作。他要管理8個本科班和一個研究生班,還要備課授課,系里的教師少,他得超課時講課;他要做家務,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學的女兒,晚上十一二時前很少睡覺,只要曉微不睡,他就得陪著;另外,他還要四處為曉微尋醫問藥。
二次手術后一年,曉微右腦又長出了腫瘤。國內的一位腦科權威說:“如果將她的腫瘤徹底切除,那么100%會變成癡呆;不徹底切除的話,那么就像割韭菜一樣,過不多久還會長出來。另外,如果手術做不好,她將會變成癱瘓;即使手術成功了,情感也會喪失,性格和思維也將改變。這種手術做與不做意義并不很大……”
但王信認為:“還是應該手術,手術是一個積極的措施,哪怕她癱了,我也要養著她……”一位富有責任心的丈夫怎能放棄妻子的生命?
曉微又做了第三次手術。
手術成功了,徐曉微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96年夏,曉微又出現了腦積水,顱內壓力升高,不能說話,右腿失去知覺,又住進了醫院。經過搶救,她終于能說話了,可是從那以后她像變了一個人,思維紊亂,情感淡漠,一個十分文靜而內向的她變得很粗魯,有時還罵王信;手術后,她每天必須服藥,服藥后她就尿床,王信每天夜里要給她換好多次尿墊子,那尿味又特別的大。最后,為了照顧曉微,王信不得不辭掉了系主任職務,
1999年初,正值學期末王信最忙時,曉微做了第五次手術。為了護理曉微,王信從家鄉黑龍江請來一位小保姆。白天,他守在病榻旁,有課時他匆匆跑回學校上課,下課再急忙跑回來,一邊批改作業,一邊照看妻子;晚上,把妻子交給小保姆陪護,他回家去照顧女兒,
一天,王信正在喂曉微吃飯時,有電話找他。原來,小保姆騎自行車回家時,被一輛桑塔納撞傷。卑鄙的司機將她拉到一家醫院后就逃掉了。小保姆昏迷不醒,瞳孔已經擴散。醫生從小保姆的身上找到了醫院的看護證,便將電話打了過來。王信放下電話,像陀螺似的跑去看小保姆,代家屬在手術單上簽字,把她推進手術室,然后急忙回家籌錢,跑到教室給學生布置作業,又跑回醫院來照料妻子和小保姆……
一年過去了,曉微的病情有所好轉,她能在別人陪伴下到外面散步了。可是她沒有了情感,她不知道親一親自己的女兒,思維混亂,語無倫次。
1996年以后,曉微便失去了情感,夫妻生活也終止了,她已無法再充任妻子的角色了。情感豐富的王信工作和照料病妻之余,只好把精力全然投入到授課與做學問之中,幾年來,他在日語系授課的課時最多,成果也最多,有近20項科研成果問世,并且在日本發表了3篇學術論文,還出版了一部25萬字的《精修日本文法》。
有人為王信感到悲哀,他是一個健全的、感情豐富的、擁有七情六欲的男人,他是一個擁有高學歷的、很有發展前途的男人,為一個已不可能康復的、失去了正常思維和情感的妻子而付出這些是否值得?也有人認為,王信應該將曉微送進療養所,然后去尋找自己的生活和愛情,去攀登事業的高峰,他不該為此而斷送自己的幸福和前程。
但王信說,一位真正有道德的人,是無力背叛自己的良知的,否則他將會受到自己良心的折磨。
(編輯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