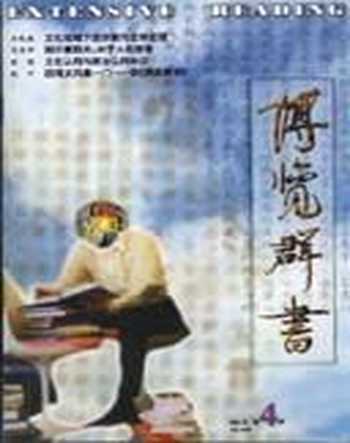文化視域下的宗教與全球倫理
王曉朝
尋求“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普遍倫理”)這一當(dāng)代全球性思想運(yùn)動(dòng)若以德國(guó)神學(xué)家孔漢思于1990年率先提出全球倫理的口號(hào)為起點(diǎn),迄今為止已逾十年。在此期間,中國(guó)學(xué)者也積極參與了討論,并發(fā)表了一些論文與專著。這些作者在論著中所表現(xiàn)的跨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視野、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強(qiáng)烈關(guān)注、執(zhí)著的理性訴求,對(duì)于推進(jìn)全球倫理運(yùn)動(dòng)起到了重要作用。
筆者認(rèn)為,孔漢思先生建立全球倫理的倡導(dǎo)從學(xué)理角度可以視為在一般文化系統(tǒng)中探討宗教與一般倫理相結(jié)合的可能性,希冀由此摸索一條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道路,而對(duì)中國(guó)的倫理學(xué)者來說,除了對(duì)這一倡導(dǎo)的積極響應(yīng)外,更加注重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趨勢(shì)下中國(guó)文化自身轉(zhuǎn)型與更新的具體進(jìn)路。這些工作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shí)意義,然而若不置于文化視域下進(jìn)行考察,對(duì)孔漢思先生本意的誤解也在所難免。
一、一般文化研究與宗教文化研究的關(guān)聯(lián)
西方社會(huì)有著深厚的宗教背景,談文化必談宗教,而談宗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早在二十世紀(jì)初,西方學(xué)者就已經(jīng)開始不分國(guó)度地把西方世界作為一個(gè)文化整體加以反省,思考整個(gè)西方文化的前途問題,這種理性的反思貫穿于整個(gè)二十世紀(jì)。德國(guó)歷史學(xué)家施賓格勒在上世紀(jì)初首開先河,打破了十九世紀(jì)風(fēng)行的進(jìn)步觀念,認(rèn)為西方文化已經(jīng)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正在走向沒落。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道森反對(duì)這種歷史宿命論,認(rèn)為只有重新發(fā)現(xiàn)曾為西方文明提供了最初精神動(dòng)力的基督教,西方文明才有希望得到復(fù)興,宗教并不是一種與社會(huì)客觀現(xiàn)實(shí)無關(guān)的個(gè)人感情,而是社會(huì)生活的核心和現(xiàn)代各種文化的根源。德國(guó)哲學(xué)家卡西爾的文化哲學(xué)以整個(gè)人類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想要從人性的根源上去解決文化危機(jī)。
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以后,隨著西方社會(huì)種種社會(huì)危機(jī)和文化危機(jī)的出現(xiàn),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們帶來的心靈震撼和精神創(chuàng)傷,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的文明形態(tài)理論以全面回答西方文化的前途問題為宗旨,認(rèn)為每一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都是宗教,西方文化的希望就在于基督精神的再生。美國(guó)神學(xué)家蒂利希的文化神學(xué)也是在文化傳統(tǒng)瓦解、主體意識(shí)衰退、永恒真理隱遁的緊要關(guān)頭,想要為消解西方文化危機(jī)提供一種神學(xué)答案。
由此可見,西方學(xué)術(shù)界的宗教文化研究實(shí)際上是二十世紀(jì)西方宏觀文化研究的組成部分,而宗教學(xué)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又促使西方學(xué)術(shù)界擁有了一種多元共存和面向未來的文化理念。
西方的宗教學(xué)自創(chuàng)立以來,其研究方法一直受到比較語言學(xué)的影響,不少西方學(xué)者廣泛收集世界各地的宗教資料,試圖通過比較研究闡明宗教現(xiàn)象的起源與發(fā)展。他們“對(duì)世界上各種宗教的起源、結(jié)構(gòu)和特征進(jìn)行比較,同時(shí)考察確定各種宗教真正的一致之處和歧異之處,它們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范圍,以及將其視為不同類型時(shí),它們相對(duì)的高低優(yōu)劣。”①可以說,宗教學(xué)在其初級(jí)階段基本上是在近代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論,特別是在生物進(jìn)化論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其比較研究也還沒有脫離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學(xué)術(shù)氛圍。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文化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已日趨式微,而作為其文化之魂的基督教價(jià)值體系亦遇到世俗化、多元化、后啟蒙或后現(xiàn)代化的強(qiáng)烈挑戰(zhàn)。值此機(jī)遇,西方宗教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進(jìn)入了新時(shí)期。一方面,大多數(shù)學(xué)者開始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近代宗教研究,日益傾向以“宗教史學(xué)”(HistoryofReligion)來取代“宗教學(xué)”或“比較宗教學(xué)”,以標(biāo)明新時(shí)期宗教研究的主要特點(diǎn)。即使那些繼續(xù)沿用“宗教學(xué)”或“比較宗教學(xué)”概念的學(xué)者也有許多在比較研究觀念上跨入了新時(shí)期,他們盡力彌補(bǔ)傳統(tǒng)橫向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的缺陷,注重對(duì)各種宗教形態(tài)進(jìn)行經(jīng)驗(yàn)性的描述和歷史性的比較。與此同時(shí),一些交叉學(xué)科,比如宗教心理學(xué)、宗教社會(huì)學(xué)、宗教現(xiàn)象學(xué)、宗教語言學(xué)、宗教民俗學(xué)、宗教考古學(xué)等等,相繼出現(xiàn)。這些研究與西方整個(gè)宏觀文化的研究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了整個(gè)西方文化研究的熱潮。
正因?yàn)樽诮涛幕芯颗c一般文化研究的上述關(guān)聯(lián)性,所以二十世紀(jì)宗教文化研究的意義決不限于宗教學(xué),也不限于某一種民族文化,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或世界性的特征。擺脫了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桎梏,西方學(xué)術(shù)界終于形成了一種面向未來的新的文化理念,其具體表現(xiàn)就是觀察問題的跨文化視野、闡述問題的文化系統(tǒng)框架和分析問題的跨學(xué)科方法。筆者稱之為“文化視域”,并視之為上世紀(jì)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成就。
與“視域”這個(gè)詞對(duì)應(yīng)的英文是perspective。這個(gè)英文詞的中文釋義還有很多,有透視、遠(yuǎn)景、展望、觀點(diǎn)、看法、眼力、事物相互關(guān)系的外觀、正確觀察事物相互關(guān)系的能力,等等。②本人把“culturalperspective”這個(gè)英文短語譯為“文化視域”,用來指稱經(jīng)由二十世紀(jì)多學(xué)科文化理論的綜合研究之后學(xué)術(shù)界形成的思想境界。文化視域的形成有以下三個(gè)標(biāo)志:
第一、觀察問題的視野有無覆蓋多個(gè)學(xué)科,乃至所有學(xué)科的研究對(duì)象。二十世紀(jì)文化研究的對(duì)象無所不包,然而囿于人類理性思維的習(xí)慣,學(xué)者們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定義之雜多,也是人所周知的。學(xué)者們?cè)谧匪莓?dāng)代文化研究的淵源時(shí)大都追溯到泰勒的文化定義。這位學(xué)者寫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xué)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shí)、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xí)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huì)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xí)慣在內(nèi)的復(fù)雜整體。”③這里,他將文化與文明等量其觀,在二者之間未作任何區(qū)別,實(shí)際上開了消融文化與文明界限之先河。界限的消融帶來了研究對(duì)象的擴(kuò)展,在此意義上,二十世紀(jì)多學(xué)科共同研究文化問題的局面自泰勒始。
第二、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解釋有無突顯其文化或人文意義。文化的一般界定在于把文化視為人類創(chuàng)造活動(dòng)與創(chuàng)造成果的總和,而進(jìn)一步的界定則是人類所擁有的觀念和精神,或物質(zhì)、制度、行為中所包含的文化或人文意義。文化是一個(gè)高度綜合的統(tǒng)一體,文化精神滲透于民族、社會(huì)的各個(gè)部門和領(lǐng)域。所以文化研究應(yīng)當(dāng)將文化的各個(gè)部門、各種起作用的因素作為一個(gè)有機(jī)的綜合體聯(lián)系起來進(jìn)行考察。這種聯(lián)系文化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并對(duì)其所含人文精神的綜合考察就是一般的文化研究,目前最接近這種一般文化研究的是文化哲學(xué)的研究或以宗教與文化關(guān)系為核心問題的抽象理論研究。
第三、能否突破傳統(tǒng)歷史學(xué)的機(jī)械因果論,提出新的理論框架。自從德國(guó)學(xué)者斯賓格勒提出文化是有機(jī)體的觀點(diǎn)以后,他的文化宿命論的結(jié)論沒有被普遍接受,但是他反對(duì)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方法,即那種簡(jiǎn)單地套用自然科學(xué)術(shù)語及機(jī)械因果論的方法,得到了學(xué)術(shù)界的認(rèn)可。學(xué)者們公認(rèn)文化是歷時(shí)性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是一種活體,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軌跡。在新世紀(jì)的文化研究中,我們有必要綜合現(xiàn)有多學(xué)科的理論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chǔ)上求得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
文化危機(jī)意識(shí)引發(fā)了學(xué)術(shù)界的宗教文化研究熱潮。在這樣的學(xué)術(shù)氛圍中,宗教與文化的關(guān)系問題突顯,成為宗教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西方學(xué)者一般認(rèn)為,宗教與文化的關(guān)系,較之其他文化形式與“文化整體”的關(guān)系,有著更深刻的意義。宗教不只是依賴于各自的文化,而是可以從中抽象出來的,有著自身獨(dú)立性。只要有人,就一定會(huì)有宗教的觀念、宗教的情感和宗教性的追求;不論這些觀念、情感和追求是公開的還是隱蔽的,都是客觀存在。所以他們強(qiáng)調(diào),宗教乃是普世的,體現(xiàn)在人性、人的社會(huì)性和人的文化性之中。
文化人類學(xué)的開山祖馬林諾夫斯基曾把文化人類學(xué)界定為“研究文化的特殊科學(xué)”。他的文化概念是傳統(tǒng)的廣義文化,即把文化看作人類社會(huì)生活中的物質(zhì)現(xiàn)象和精神現(xiàn)象的總和,但他對(duì)宗教的認(rèn)識(shí)卻完全屬于現(xiàn)代。他指出,宗教決非超越整個(gè)文化結(jié)構(gòu)的抽象觀念,而是一種相伴于“生命過程”、有其特定功能的人類基本需要。這種基本需要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個(gè)體的又是社會(huì)的,歸根到底是文化的。韋伯把宗教視為一種基本的文化特性,注重揭示宗教信念在西方近代文化起源過程中對(duì)社會(huì)文化心理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十分謹(jǐn)慎地反復(fù)驗(yàn)證宗教經(jīng)濟(jì)倫理與世俗經(jīng)濟(jì)倫理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湯因比更進(jìn)一步,他把人類歷史的載體規(guī)定為文明,視宗教信仰則為文明社會(huì)的本質(zhì)體現(xiàn)、文明過程的生機(jī)源泉。這樣一來,文化與宗教的關(guān)系問題被納入文明通史,在全盤涉及文明的起源、生長(zhǎng)、衰落和解體的系統(tǒng)研究中獲得了前后關(guān)系。美國(guó)神學(xué)家蒂利希接受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化觀念,進(jìn)而認(rèn)為廣義的宗教不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種特殊機(jī)能,而是整個(gè)人類精神生活的“底層”,是貫穿于全部人類精神活動(dòng)的一種“終極關(guān)切”。人類文化的統(tǒng)一性就在于宗教,人類文化成果所體現(xiàn)的一切,就其內(nèi)涵來說都是宗教的。因此他說:“正如文化在實(shí)質(zhì)上是宗教,宗教在表現(xiàn)形式上則為文化。”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文化熱和宗教熱也是熔為一體的。在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時(shí)期,中國(guó)學(xué)者了解了西方學(xué)術(shù)界的研究態(tài)勢(shì),并相對(duì)獨(dú)立地展開了自己的研究。現(xiàn)階段中國(guó)學(xué)者對(duì)宗教與文化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可以高度概括為一句話:宗教是文化(文明)的核心。這一命題的具體含義主要有:(1)宗教作為文化的一種形式滲透或包容一般文化的各個(gè)層面和各種形式,不僅滲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識(shí)層,而且滲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為層,不僅包容文學(xué)和藝術(shù)等文化形式,而且包容其他一切文化形式;(2)人類各大文化系統(tǒng)均以某種宗教為代表,現(xiàn)存世界各大文化體系均有宗教的背景,均以某種宗教信仰為支柱,西方文化以基督宗教為代表,東方文化以儒教為代表,⑤阿拉伯文化以伊斯蘭教為代表,等等;(3)宗教為人類社會(huì)提供了基本的信仰體系、價(jià)值規(guī)范、行為準(zhǔn)則、組織體制。
經(jīng)過上個(gè)世紀(jì)的文化研究,宗教是文化的核心這個(gè)觀點(diǎn)已經(jīng)被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大多數(shù)學(xué)者接受。人們?cè)絹碓缴羁痰卣J(rèn)識(shí)到,宗教受整個(gè)文化體系的制約,它本身也是文化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和文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人類文明史的絕大部分,在各個(gè)時(shí)代和各個(gè)國(guó)家,宗教是文化統(tǒng)一的核心力量。它是傳統(tǒng)的保護(hù)者,道德法則的維護(hù)者,智慧的傳播者,人們生活的教育者,可以把社會(huì)控制在一個(gè)確定的文化范型之中。不了解處于文化核心的宗教信仰就不能理解這種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撇開宗教就不可能對(duì)文化作出完整的解釋。從世界和全人類的范圍來看,宗教作為一種漫長(zhǎng)的歷史現(xiàn)象仍將繼續(xù)存在,并將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發(fā)展中起重要作用。
二、同一文化視域下的不同思想進(jìn)路
在有關(guān)全球倫理這一主題的諸多文獻(xiàn)中,萬俊人教授的《尋求普世倫理》⑥是筆者所見最詳盡的一部由中國(guó)學(xué)者完成的作品,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參與尋求全球倫理這一思想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作。因此我們可以用它來作為一個(gè)范例,分析中外學(xué)者的不同思想進(jìn)路。
由于學(xué)者的知識(shí)背景和關(guān)注點(diǎn)不一樣,文化視域可以是同一個(gè),但聚焦點(diǎn)可以不同。比較一下孔漢思教授與萬俊人教授的文化視域,不難看出:在前者的文化視域中,宗教始終占據(jù)文化系統(tǒng)的核心地位;而在后者的文化視域中⑦,道德無疑是一個(gè)聚焦點(diǎn)。孔漢思教授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承認(rèn)教義差別(也包括各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差異)的前提下,存異求同,尋求人類對(duì)全球倫理的認(rèn)同;而萬俊人教授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超越各種意識(shí)形態(tài)(也包括以宗教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差異,存異求同,尋求人類對(duì)普世倫理的認(rèn)同。問題是同一個(gè),但要求回答的側(cè)重點(diǎn)不同。
相比較而言,孔漢思先生需要回答的問題要容易些。這是因?yàn)榭诐h思先生對(duì)宗教與文化二者關(guān)系的理解是“宗教核心論”的,亦即認(rèn)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孔漢思從宗教這一關(guān)鍵要素出發(fā)解釋全球文化系統(tǒng)的運(yùn)作,打通宗教與道德的關(guān)系,不會(huì)遇到太多的麻煩;而在萬俊人教授的文化視域中,宗教的重要作用雖然得到了高度強(qiáng)調(diào),但他的聚焦點(diǎn)是倫理,因此最后的結(jié)果是一定程度的倫理泛化,宗教則被淹沒在世俗倫理的汪洋大海之中。
從萬著對(duì)“普世倫理”的界定以及對(duì)其基本理論維度的分析來看,這一傾向十分明顯:“普世倫理是一種以人類公共理性和共享的價(jià)值秩序?yàn)榛A(chǔ),以人類基本道德生活、特別是有關(guān)人類基本生存和發(fā)展的淑世道德問題為基本主題的整合性倫理理念。”⑧“依據(jù)以上有關(guān)倫理層次結(jié)構(gòu)及其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了解,我們可以這樣來確定普世倫理的基本理論維度:在信仰倫理或道德形上學(xué)、社會(huì)規(guī)范倫理和個(gè)人心性美德倫理三個(gè)層次之間,普世倫理將以社會(huì)規(guī)范倫理為其基本理論維度,同時(shí)保持對(duì)信仰倫理與美德倫理的開放性探討。這種理論定位是由普世倫理本身的特質(zhì)所決定的,具體地說,是由其‘最起碼的最大普遍化理論立場(chǎng)所決定的。”⑨相對(duì)于中國(guó)社會(huì)的特點(diǎn)(信仰宗教的人數(shù)不占總?cè)丝诘亩鄶?shù))來說,這樣的界定和理論維度設(shè)置有著十分正當(dāng)?shù)睦碛桑蝗欢褪澜绶秶裕ㄈ澜缧沤倘藬?shù)約占總?cè)丝诘模福埃ィ@種“普世倫理”能否做到“最起碼的最大普遍化”,筆者表示一種謹(jǐn)慎的疑慮。
萬俊人先生問得好:“當(dāng)代宗教界為什么要提出全球倫理問題?為什么提出全球倫理問題的是宗教界而不是倫理學(xué)界?進(jìn)而,當(dāng)代宗教界所提出的全球倫理問題究竟是宗教神學(xué)的某種世俗關(guān)切和現(xiàn)實(shí)介入的需要?還是我們這個(gè)世界的道德現(xiàn)實(shí)反應(yīng)?”紒紛矠對(duì)這些設(shè)問,萬俊人教授已有基本正確的解釋。紒紜矠造成這一事實(shí)的原因確實(shí)不僅是一個(gè)思想敏感度的問題,而且是一個(gè)全球文化現(xiàn)狀的問題。如果聯(lián)系全球宗教信仰現(xiàn)狀來看這個(gè)問題,那么尋求全球倫理的思想運(yùn)動(dòng)由宗教界而不是由倫理學(xué)界來倡導(dǎo)實(shí)在是再自然不過了。
撇開全球宗教信仰現(xiàn)狀不談,僅從思想進(jìn)路著眼,孔漢思教授在一個(gè)以宗教為聚焦點(diǎn)的文化視域下,由宗教進(jìn)入倫理,是比較自然的事;而萬俊人教授在一個(gè)以道德為聚焦點(diǎn)的文化視域下倡導(dǎo)“普世倫理”,由倫理進(jìn)入宗教,這種做法固然沒有什么不可以,針對(duì)中國(guó)文化特點(diǎn)也有其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我們看到,在這一進(jìn)路中越是強(qiáng)調(diào)宗教所具有的某種重要作用,也就越加大了建構(gòu)“普世倫理”的難度。基于對(duì)宗教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重要作用的肯定,萬俊人教授以一種承認(rèn)“宗教為一種重要的道德資源”的方式由倫理進(jìn)入宗教,但他馬上指出:“然而站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倫理學(xué)立場(chǎng)上,我們并不認(rèn)為宗教倫理的方式是一種(更不用說惟一)現(xiàn)實(shí)可行的普世倫理的建構(gòu)方式。”紒紝矠兩相對(duì)照,筆者只能說心理學(xué)上的“鴨子變兔子”(或世界觀的轉(zhuǎn)變)在學(xué)者的思維活動(dòng)中也得到了印證,在一個(gè)以宗教為聚焦點(diǎn)的文化視域下非常現(xiàn)實(shí)的東西,到了一個(gè)以倫理為聚焦點(diǎn)的文化視域下成了不現(xiàn)實(shí)的。
三、文化視域下宗教與倫理結(jié)合的模式
倡導(dǎo)“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已經(jīng)有了充分的闡述,對(duì)此筆者深表贊同。然而,目標(biāo)(想要解決的問題)基本一致不會(huì)自然而然地帶來進(jìn)路的一致。在學(xué)者的思想活動(dòng)中,目標(biāo)明確之后,下一邏輯進(jìn)程無疑就是理論上的建構(gòu),而不同的關(guān)注點(diǎn)對(duì)理論思考必然有影響。我們或許可以臨時(shí)虛擬一個(gè)無焦點(diǎn)的文化平臺(tái),視宗教與道德為平等與并列關(guān)系。為什么要這樣做?理由很簡(jiǎn)單:無論具體文化的現(xiàn)實(shí)狀況如何千差萬別,研究的重點(diǎn)放在哪個(gè)方面,若思想者不能在建構(gòu)全球倫理的初始階段在這個(gè)虛擬的文化平臺(tái)中賦予宗教與倫理(道德)并列的地位,那么其邏輯推演就很容易趨向于宗教與倫理的相互取代或宗教與道德的泛化。
孔漢思先生在倡導(dǎo)全球倫理的過程中,對(duì)宗教與倫理結(jié)合的可能性作過一些理論上的分析。他指出:第一、如果以為全球倫理是沒有宗教的倫理,那是“對(duì)全球倫理計(jì)劃的根本的誤解”,盡管自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要倫理,不要宗教”,“要倫理教育,不要宗教教育”已經(jīng)成為流行的口號(hào)。第二、可以在普遍人性的基礎(chǔ)上建立沒有宗教的倫理,但是這種倫理相對(duì)于宗教來說有四方面的局限性,因?yàn)椋澳軌騻鬟_(dá)一個(gè)特殊深度、綜合層面的對(duì)于正面價(jià)值和負(fù)面價(jià)值的理解”、“自身能夠無條件地保證價(jià)值、規(guī)則、動(dòng)機(jī)和理想的正當(dāng)性,并同時(shí)使它們具體化”、“能夠通過共同的儀式和符號(hào)以及共同的歷史觀和希望前景,創(chuàng)造精神安全、信任和希望的家園”、“能夠動(dòng)員人民抗議和抵抗非正義的條件”的,只能是宗教而不是普遍倫理。第三、全球倫理的精神基礎(chǔ)是宗教性的,但它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不能與現(xiàn)實(shí)隔離,而應(yīng)當(dāng)能應(yīng)付當(dāng)今世界經(jīng)濟(jì)、政治和社會(huì)問題。紒紞矠結(jié)合孔漢思先生的其他論述,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反對(duì)把宗教歸結(jié)為倫理,另一方面也反對(duì)把倫理歸結(jié)為宗教,更反對(duì)超越普遍人性的宗教狂熱,并將其視之為全球倫理的一條死路。這也就是說,在談及宗教與倫理結(jié)合時(shí),他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承認(rèn)了宗教與倫理的并列關(guān)系,各有其相對(duì)獨(dú)立的界限,只有在進(jìn)到論述宗教與倫理如何結(jié)合這一步,方可言及二者的互滲。
萬俊人教授對(duì)“道德與宗教文化所享有的文化親緣關(guān)系”作了許多精彩的解釋紒紟矠,提出了以宗教為一種道德資源的充分理由,從而為他建構(gòu)“普世倫理”奠定了基礎(chǔ)。然而筆者認(rèn)為,盡管以宗教為道德資源也和宗教與倫理的結(jié)合有關(guān),但非二者完全意義上的結(jié)合。由于這個(gè)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萬俊人教授堅(jiān)決反對(duì)宗教與倫理的相互替代紒紡矠,但無法避免倫理的泛化(我們?cè)谥行砸饬x上使用這個(gè)詞),例如“信念倫理”的提法及其論證。紒紣矠萬俊人教授這樣做并非沒有道理,但其理論上的直接后果則是宗教特性的消解與倫理的泛化,并將影響到對(duì)宗教與倫理結(jié)合方式的全面探索。因此我們似乎可說,在萬俊人教授的“普世倫理”中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宗教與倫理的結(jié)合,而只有倫理對(duì)宗教的汲取。
孔漢思先生建構(gòu)全球倫理的模式是清楚的,這就是:以宗教信念為基礎(chǔ),以世俗倫理為具體形式建構(gòu)全球倫理。這種普遍倫理不是某種具體宗教的倫理,也不是若干世界宗教倫理的共同成分,而是世界各個(gè)民族、各種文化普遍認(rèn)可的倫理。在一個(gè)以宗教為聚焦點(diǎn)的文化視域下,從宗教進(jìn)入一般倫理,進(jìn)而探討宗教與世俗倫理相結(jié)合的可能性,最后以多宗教的共同信念為基礎(chǔ),以世俗倫理為具體表現(xiàn)形式,倡導(dǎo)有形可見的“全球倫理”,我把孔漢思先生的這個(gè)理論建構(gòu)過程稱作“弱宗教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強(qiáng)調(diào)宗教與倫理的結(jié)合。
萬俊人教授尋求普世倫理的模式也很清楚,這就是:以人類公共理性和共享的價(jià)值秩序?yàn)榛A(chǔ)整合各種倫理資源,通過對(duì)若干人類普遍擁有的理念(人權(quán)、正義、自由、平等、寬容)所蘊(yùn)涵的倫理意義之闡釋來確定人類的道德共識(shí)和相融互通的倫理理念,通過道德教育使普遍倫理規(guī)范能夠獲取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各民族人民的廣泛認(rèn)同和支持,最終使之內(nèi)化為全體社會(huì)公民(在普世倫理的視野內(nèi)即是“世界公民”)的有效方式。我把萬俊人教授的這個(gè)理論建構(gòu)過程稱作“強(qiáng)倫理模式”,其最大特點(diǎn)是倫理道德的最大程度的彰明以及經(jīng)濟(jì)、政治、法律、宗教等文化子系統(tǒng)對(duì)倫理道德所具有的制約作用的弱化。
“弱宗教模式”在理論上是對(duì)以往關(guān)于宗教與倫理結(jié)合的既有模式(把宗教歸結(jié)為倫理、把倫理歸結(jié)為宗教、用宗教超越倫理)的一種突破,尤其從宗教神學(xué)的現(xiàn)代發(fā)展來看更是如此。而“強(qiáng)倫理模式”的重要意義在于打通宗教與倫理的界限,參與了創(chuàng)建“全球倫理”的思想運(yùn)動(dòng)。凡了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以往對(duì)宗教與倫理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的學(xué)者,不難體會(huì)到邁出這一步的艱難。
“全球倫理”這一思想運(yùn)動(dòng)沒有完,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的理論建構(gòu)也沒有完。我們已經(jīng)有了“弱宗教模式”和“強(qiáng)倫理模式”,這些模式雖然還有一些問題亟待說明,但筆者深信這方面的努力還將繼續(xù)下去。
四、實(shí)現(xiàn)“全球倫理”的可能性
創(chuàng)建“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有著十分迫切的現(xiàn)實(shí)需要,但又極易被人們斥為烏托邦。盡管烏托邦在人類歷史和思想史上并非毫無積極作用,但“全球倫理”倡導(dǎo)者決不希望把自己的理論建構(gòu)成為“一種新的人類道德烏托邦設(shè)想”。紒紤矠倡導(dǎo)的主旨是為了達(dá)成,但是闡述現(xiàn)實(shí)的迫切需要無法確保“全球倫理”理論上的正確無誤,因此在全球倫理的創(chuàng)導(dǎo)者們已經(jīng)提出相當(dāng)完整的理論框架以后,筆者想說一下全球倫理的滑鐵盧。用“滑鐵盧”這個(gè)詞,筆者并非想要預(yù)言這一思想運(yùn)動(dòng)的失敗,而是要考慮“全球倫理”的理論架構(gòu)亟待解決的問題,或者說可能招致失誤之處。
信仰或信念問題是全球倫理必然要涉及的問題,這個(gè)問題既是“弱宗教模式”的滑鐵盧,也是“強(qiáng)倫理模式”的滑鐵盧。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的倡導(dǎo)者想要突破全球宗教教派與意識(shí)形態(tài)紛爭(zhēng)的束縛,尋找并確定一種新型倫理以解決世界性的道德危機(jī)問題,然而無論是弱宗教模式還是強(qiáng)倫理模式在尋求這些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有約束性的價(jià)值觀和基本準(zhǔn)則時(shí)必然要以抽掉或淡化解決道德危機(jī)所需要的信仰(或信念)為代價(jià),因?yàn)閭€(gè)體、社群、民族、國(guó)家由于信仰上的差異所帶來的紛爭(zhēng)正是他們要加以突破的東西。可是,為了解決道德危機(jī)必須懸置信仰差異嗎?信仰上的差異只能對(duì)解決紛爭(zhēng)起負(fù)面作用嗎?在展開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間的對(duì)話時(shí),參與對(duì)話者必然要以放棄自身的立場(chǎng)為先決條件,否則就不可能嗎?把話再說透一些,孔漢思先生提出來的那些“有約束性的”基本原則或萬俊人教授提出來的“規(guī)范性倫理原則”可以沒有信仰或信念作支撐嗎?恐怕還得具體分析。
在筆者看來,道德危機(jī)不是孤立出現(xiàn)的,它至少與信仰危機(jī)和認(rèn)識(shí)危機(jī)相伴。而就道德對(duì)信仰的依附性及其自身信仰化的趨勢(shì)和發(fā)揮作用的途徑而言,道德危機(jī)為表,信仰危機(jī)為里。哀莫大于心死,信仰危機(jī)比道德危機(jī)更深層,更根本,信仰的動(dòng)搖和真理的相對(duì)化,必然導(dǎo)致傳統(tǒng)道德觀念和倫理標(biāo)準(zhǔn)的失效。信仰是溝通宗教與道德的中介,因此解決道德危機(jī)可以從信仰入手,反之則治表不治本。因此我們需要具體地研究信仰的特性及其與倫理和宗教的關(guān)系,為倡導(dǎo)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論說明。
限于本文的主旨,我們無法詳細(xì)展開這方面的討論。僅以下述文字表明筆者對(duì)這一問題的最基本看法:
在人類歷史上,宗教信仰是年代最悠久的一種信仰,道德與宗教信仰的結(jié)合是最牢固的一種結(jié)合,人類的道德在宗教中找到歸宿是一種必然,而不是偶然現(xiàn)象。道德的出現(xiàn)也許早于宗教、哲學(xué)、政治、藝術(shù)等意識(shí)形式,幾乎與人類的自身同時(shí)產(chǎn)生,但在其以后的發(fā)展中,道德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卻越來越失去其獨(dú)立地位,靠依附于一定的信仰體系而存在并得以施行。這一方面是因?yàn)樾叛鲎鳛槿祟惖淖罡咭庾R(shí)形式,有包容、統(tǒng)攝其他意識(shí)形式的奢望和能力,藉此給道德以理論的根據(jù)和指導(dǎo);另一方面是道德自身發(fā)展的神圣化,權(quán)威化而自覺地趨向于信仰的結(jié)果。在此意義上,我們說,道德的信仰化與神圣化是道德發(fā)揮社會(huì)作用和功能的必由之路,道德的歸宿是信仰,但宗教信仰不是道德的惟一宿主,因?yàn)樾叛龌c神圣化并不等于宗教化。
歷史上任何一種系統(tǒng)宗教或意識(shí)形態(tài)都有其相應(yīng)的道德規(guī)范,而這些規(guī)范都已經(jīng)融入信仰體系。道德之所以能起作用,就在于信仰這種意識(shí)形式所起的保證作用。不能帶來道德力量的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議的,不能帶來道德力量的非宗教信仰也是不可思議的。道德的歸宿是信仰,至于這個(gè)宿主是宗教信仰還是非宗教信仰,視具體文化環(huán)境而定。
由是觀之,全球倫理那些“有約束性的基本原則”或“規(guī)范性倫理原則”要想成為人類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道德準(zhǔn)則,并起到重整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秩序的作用,也要經(jīng)歷一個(gè)信仰化或信念化的過程,而目前我們還無法知道這些普遍倫理規(guī)范已經(jīng)或能夠內(nèi)化到什么程度,或在多大范圍內(nèi)化。
注釋:
①約爾丹(L.H.Jordan):《比較宗教學(xué)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頁。
②北大張祥龍教授曾解釋說:“視野”、“視域”、“境域”、“境界”、“緣境”、“境”是一組同義詞。參閱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guó)天道》第16頁,三聯(lián),1996年。
③Tylor煟牛B.煟保福罰雹煟校潁椋恚椋簦椋觶澹茫酰歟簦酰潁澧煟蹋錚睿洌錚睿泰勒:《原始文化》,英文版,第1頁。
④Tillichi煟校煟保梗擔(dān)耿煟裕瑁澹錚歟錚紓ofCulture煟希fordUniversityPress.蒂利希:《文化神學(xué)》,英文版,第42頁。
⑤儒家是否宗教與本文要旨無涉,在此不予討論。
⑥萬俊人:《尋求普世倫理》,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
⑦萬俊人教授本人的用語是“一種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種道德傳統(tǒng)的全景式視閾”,見萬著第62頁。
⑧《尋求普世倫理》,第29頁。
⑨《尋求普世倫理》,第45頁。
10《尋求普世倫理》,第13頁。
11《尋求普世倫理》,第77頁。
12《尋求普世倫理》,第77頁。
13HansKueng煟保梗梗發(fā)煟粒牽歟錚猓幔歟牛簦瑁椋悖媯錚潁牽歟錚猓幔歟校錚歟椋簦椋悖螅幔睿洌牛悖錚睿錚恚椋悖螈煟蹋錚睿洌錚睥煟穡穡142-3。
14《尋求普世倫理》第43頁以下。
15《尋求普世倫理》第66頁以下)
16《尋求普世倫理》第72頁以下)
17萬俊人語,該書第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