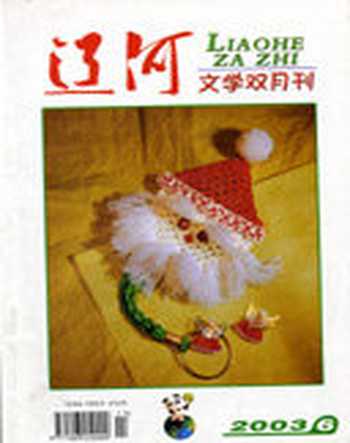“罪己詔”
馬 競
那年去景山,在崇禎上吊的那棵小樹旁,佇立良久,倒不.是緬懷一個亡國之君、封建皇帝,而實在是覺得朱由檢與數千年封建史上的約350余位君王不一樣。他在自己王朝統治的最后歲月,不到一個月內竟然兩次下“罪已詔”,向群臣與百姓袒露自己的過錯、“罪行”,不論他的初衷如何,這不也難得嗎?就連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咬破手指,在自己的衣襟上寫道:“……任賊碎裂朕尸,但弗傷我百姓。”可不可以算得上心里記掛百姓的皇帝呢?那年是崇禎17年3月19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崇禎只有33歲。還好,崇禎也不孤單,黃泉路上還有一個叫王承恩的宦官伴隨。那棵小樹太小了,它讓人懷疑,它怎么能承受得起一個坐過江山之人的軀體呢?難怪幾百年過去了,它依然長得不高不大,它已經被沉重的歷史壓住了。
在崇禎前面,朱家天下從太祖朱元璋(洪武)算起已統治了200多年,歷經16位皇帝,到了崇禎手里,實在是時乖命舛,關外有滿清虎狼之兵,中原有李自成勢如烈火的義軍,內憂外患,愈演愈烈;200多年的官場腐敗與濁氣籠罩朝廷上下,實在說,明王朝“內里已經盡上來了”。據《明季北略》卷十三載,甲申年的二月中旬,崇禎頒下了第一道“罪己詔”,并要求“傳諭天下”,在分析了自己“缺功少德,身心笨拙,罪過深重”之后,把貪官腐敗的丑德惡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鞭撻。國家存亡之際,他想到了是趄廷腐敗所致,禍起于蕭墻之內。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回扣),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豁免,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乘機自潤……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屈承。……”
崇禎在反思自己17年的統治,不,他在反思200多年的朱家統治。在中國歷史上,從反貪污腐敗的角度講,明王朝是打擊最激烈、殺罰最重的時期。還是在洪武的時候,朱元璋連自己的親侄子朱文正也殺了(朱丈正官拜大都督,鎮守江南,貪聲色,荒淫驕侈),附馬歐陽倫也殺了(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安慶公主為馬皇后所生,歐陽倫仗恃自己是皇親國戚,收受賄賂,偷運私茶到邊境販賣,縱使下屬侮辱地方官吏,朱元璋把他殺了)。朱由檢是朱元璋第十七世孫,第十七任皇帝,從開國洪武皇帝朱元璋到亡國之君崇禎皇帝束由檢;朱家都在反腐敗。對朱姓皇帝來說能認識到這個問題,是他們的英明之處;能采取措施,制定相關法律(《大明律》等)甚至施以極刑進行抑制,是他們的難能之處;終不能根除痼疾因暴政與腐敗導致江山易手,君王暴尸荒野,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悲哀。大明政權不是敗在滿清之乎,也不是敗在李自成義軍之手,而是敗在腐敗上。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這樣的事實,歷代統治者都看到了,同樣感到了它的可怕,可是都沒能找到有效的根治辦法。
·
讀《明史》知道,就在朱由檢頒發第一道“罪已詔”不久,李自成義軍已兵臨城下,那隆隆的炮聲,已經遠近可聞,朝廷已是既無可征之兵,又無搞軍之餉,朝野上下計無可出。甲申三月十一日,崇禎下了第二道“罪己詔”,其詔書說:
“朕承鴻業已十又七年,感上天之威嚴,知托付之任重,宵旦兢惕,,不敢怠荒。然災害不斷,盜賊叛道聲勢日重,其忘大明代代豢養之恩,二十年來恣意兇殘,朕為百姓父母,不能保護;百姓為朕之子,不得懷抱。坐視秦、豫為廢墟,江、楚血雨腥風,皆朕之罪也;百姓遭致兵刃、踏水火、血流成河、骸積成山,皆朕之罪也;百姓輸草交糧,捐贈資財,加賦多征,受預支之苦,又朕之罪也;百姓房屋殘破,田園荒蕪,忍饑挨餓,不勝寒冷,朕之罪也;百姓年年苦難,旱澇雙至,病疾災禍,上犯天,下怨民,朕之罪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文官首鼠兩端不能良策,武將驕懦不能建功勛,皆由朕撫馭無道。朕終夜以思,無地自容,故布告天下……”
不到一個月,連下兩道“罪己詔”,崇禎真是自察自省的模范皇帝了。單就詔書而言,前一詔書認識到了腐敗是“敗國”的禍害,后一詔書則承認了自己統治的無能。但是,一切都為時晚矣!就算是真龍天子也無力回天了。就在第二道“罪己詔”頒發后的第八天,統治了200多年的大明江山,在李自成義軍勢如破竹的攻勢下,轟然倒塌,江山易主。
好多年前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只注意到郭老分析義軍進北京城后的行為,及導致義軍迅速崩潰的原因,并沒有深刻地注意到它另一面的沉痛教訓。曾試想,如果崇禎不作為皇帝,他只是一個普通的丈夫,普通的父親,災難來臨的時候,眼見妻子懸梁(周皇后懸梁于坤寧宮),能不能連聲說:“好!好-!”;對號哭不止的女兒,能不能說:“誰讓你生在我家?”一劍一劍地砍去?(崇禎上吊前殺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長女樂安公主以手擋劍,左手被斬斷);能不能對自盡未死的妃子,一劍一劍地補去(袁貴妃上吊自縊,繩斷跌地,崇禎連補三劍)。能“罪已”,能“自省”的封建皇帝,畢竟不是普通的丈夫與普通的父親,為了保全帝王的“尊嚴”與妻女的“名節”,他不能不這樣做,不知道歷史如何評說,我想,這不能算他的罪過。
學習中國歷史,也曾讀過一些皇帝傳記,能“罪己”者寥寥,像崇禎這樣坦誠“罪己”的絕無僅有。皇帝是上天的化身,是天之子,“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位居“九五”,“金口玉牙”,掌握一切生殺予奪大權,他是一切社會財富包括老百姓生命的擁有者,他能有什么“錯”?他能有什么“罪”?一切錯與罪都是別人的。崇禎改變了這一數千年的傳統觀念,他向國人承認自己有罪,承認自己有錯,不能不讓人對這樣的帝王投以審慎的目光,哪怕他是亡國之君。
傳統觀念+般是代代相襲的,也是,自上而下相傳的。今天,一些掌握權力和有些地位的人都從來沒有什么錯,更談不上有什么罪。誰發現他們有錯,誰本身就錯了,如果再把他們的錯講出來,那就是犯了無法彌補的錯誤。因為那些掌握權力與有些地位的人幾乎都從封建社會那里繼承來了“順我都昌,逆我都亡”的官念,還要“一個聲音喊到底”,不能有異議。誰在那里自己標榜‘民主”,那肯定是他精神有問題。“批評”別人可以,“自我批評”很難,有權力有地位的人有過,可以文過,有非,可以飾非,許多人在“自省”“自察”上,恐怕連崇禎這個封建皇帝“罪己”的勇氣都沒有。
歷史上明王朝反腐的酷刑最重,然而它的吏治也最腐敗。崇禎的“罪己詔”,就算是認識到了自己有罪,也沒有辦法挽救封建王朝垮臺的命運,“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罪已詔”至多能給后人一些啟發與反思,意義也許能超過上面這些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