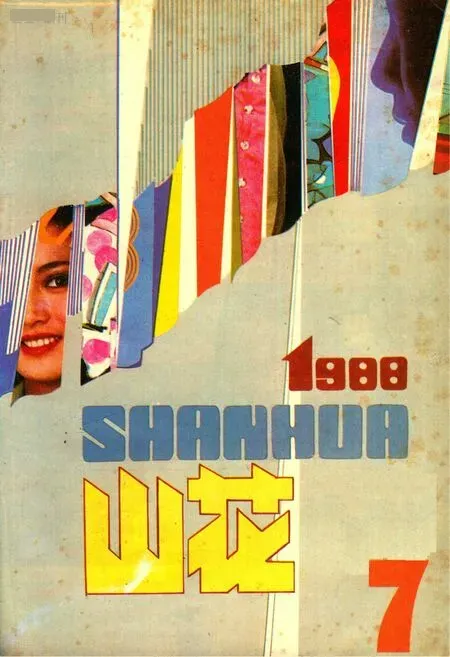我們沒有改變什么
君昌龍
無論我們給“文化”一詞作什么樣的界定,但只要承認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只要是人類行為,就必然具有文化性——那么,我們就會在那些冷冰冰的物質形態背后,看到藏蘊其中的人類夢想、激情、虛榮甚至庸俗。
正是憑著這一設定,我們進入了一種叫做“住宅文化”的表述中。通過這一表述,我們將發現那些被帶入到物質的住宅中的某種集體性觀念和記憶。
這是一種人化的過程,而柯布在《走向新建筑》一書中,對“住家”的論述堪稱經典,他說:“住家是人類所界定出來的范圍,圍繞著我們,將我們與有害的自然現象隔離,賦予我們人為的環境,使我們成為人類。”
“莊嚴的棲居”
當前歐美學界寧愿用Housing來指稱“住宅”,其用意就在于作出一種區分。House偏重于建筑和物質的含義,而Housing則強調一種行為或過程,即人的特性。
住宅及人的思考路向,在中國早已有之:“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沒有這個基本假設,也就沒有《黃帝宅經》的煌煌宏論。
盡管東西方學界都承認在人宅關系前提下導入對住宅文化的把握,必須看到,同樣是住宅,各自的背后卻延續一個不同的傳統。一種被抽象化了的“人性”,在各自的住宅體系中展示出如此豐富又如此差異的理念。
如果我們承認“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么,文化也就帶有一種類性或群性,或者說,民族性。相應地,在住宅文化中,我們除了一般性地發現人性之外,更發現民族性。正是這種民族性使住宅與住宅相區別,并以人的類群為單位,形成了一個最基本的分類。
之所以要進行上述的前提推論,其目的就在于發現一種在城市化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住宅文化或住宅觀念難被遮掩的民族印記。雖然都是摩天大樓、高層公寓、私家別墅,但就是它們的背后或它們的內部,一種以民族為單位的集體心理依然在頑固地尋找著它們的表現形式。
每個民族都會在它的集體行為中留下“共識”,但是因為各自的傳統,在其對表達方式的選擇上,又各有側重點和興奮點。所謂“吃在中國,住在俄羅斯,穿在法國,玩在美國”的說法,似乎中國人把心思全花在吃上面了。
其實,就用心的程度而言,中國人在“住”而不是在“吃”上面投入了或寄托了大部分的精力。對于這個民族來說,“住哪兒”和“如何住”,往往是尊嚴、權力、地位和身份的最有代表性的表達。
與“住”相比,“吃”似乎只是“雕蟲小技”,一時所為,而“住”則是一輩子的事業,是“壯夫”的追求。正因為中國人把住宅視為一種“宏偉敘事”來建構,所以,從他們對于住宅的一生的奮斗中,似乎很難找到一種輕松的閑適,而一朝立起大廈,則所謂“詩意的棲居”倒不妨直言為“莊嚴的棲居”,宅居成了生命中無法承受又必須承受的重量。
想想墨子的話:“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居”的問題已經被上升到人生大問題的高度,成了快樂和幸福的必要的原則了。
當然,正因為“居”的問題被附加了如此沉重的念想,所謂“樂”常常就變成了“苦”,謂“苦中作樂”是也。如果再想想阿房宮下的累累白骨,想想耗盡民脂民膏的朱門,真不知道樂從何來。當然,這么說可能是另一個問題了。
“自己的宅屋”
對住屋的那種近乎拜教式的迷戀,早已貫穿在這個民族的民間追求中,而“自己的宅屋”(不一定就是豪宅)也成了尋常百姓夢寐以求的一種信仰。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個寫農民生活的高手——高曉聲,在他的一篇名作《李順大造屋》中,寫了一個叫李順大的農民,如何在“造屋”的夢想中耗費了一輩子的心血,世易時移而癡心不改。如果要問李順大,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房子”。
在他的答復中,回蕩著的幾乎是8億農民共同的心聲。看到那些先富起來的農民兄弟,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手拿皺巴巴的圖紙,與鄉村建筑師們自豪地比劃時,就覺得無論有錢還是沒錢,李順大式的追求完全沒有改變,而只有在規劃和建設自己的房子時,我們才發現類似翻了身的農民指點江山的豪氣。
當然,對房子的追求還不僅僅是農民兄弟,想到那些“無私地”展露在房產科長家門口的一張張笑臉,以及堆在屋里燦爛的禮物,就可以知道,工人老大哥們房子追求一點也不輕松。而對于那些生活在“單位”中的人們來說,房子成了他們最需要分享的公共財產,而權力的頂峰就是那只操縱著分房計劃的大手。
一個正在消失的時代
西方人只要打好一個背包,駕著車就到另一個城市去生活了,而在中國,房子將一個人的脊背甚至整個生活幾乎壓成了一條曲線。同樣是房子,竟然有如此不同的重量。
當然,我們盡可以從中找到生活水平和經濟實力方面的差異,但聯系到民族或歷史的因素,就發現其背后潛藏著深長的文化原由。
“安土重遷”這個詞最生動也最深刻地說明了這個生活在亞熱帶季風氣候下的河流兩岸的民族,它是如此頑固地將農耕文明含化成了傳統。這種農耕文明把人與大地的關系演繹在它的文化圖式中,而宅居不妨視為人與大地的關系的象征物。
大地對人類溫暖的呵護,不僅體現在廣袤的田野和它的饋贈上,也體現在那些大小不一的宅基上。它們阻擋了來自西伯利亞寒冷的北風,或來自熱帶海洋灼人的氣浪。
正因為“構本為巢”而帶來的安全、溫暖與尊嚴,宅居才可能被抽象為一種價值,或內在為一種象征。
當然,我們盡可以說我們已經在逐步告別處于日落時分的農耕文明,隨之而來,那些被附加在宅居上的價值也在慢慢地損消。那些流浪在都市里、出入于出租屋中的操著外省口音的年輕人,已經擴大成了群落,而他們以其對土地和老宅的告別,說明了一個“安土重遷”的時代正在消失。
但是,觀念的革命絕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特別是當住宅文化已經成為一個民族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時,它的變遷常常是緩慢的。而當我們理解了“文化總是滯后的”這一論斷之后,就會發現,住宅對于中國人的心理重量似乎并沒有減輕多少。就說那些流浪于都市的外省青年吧,那些時不時泛起的不切實際的“思鄉病”,以及深藏內心的買房置地、安居樂業的夢想,就已經說明居住文化依然代表了一種價值,它作為安定和幸福的象征,這一點并沒有多少改變。
就說那些已經先富起來并安定下來的人們,從他們對宅居的不懈追求中,同樣可以看見這種住宅文化的影子。像江浙農村那些越蓋越奢華的“豪宅”,沿海發達城市那些貼金掛銀的“華庭”,其實是對宅居拜物教式的迷戀的現代表達。
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在對這些“豪宅”和“華庭”的奢華深表震驚之后,曾經感慨中國只能出地主而出不了資本家。他要提醒人們的,正是一種以宅居為象征的文化和傳統。
盡管我們仿佛已經“全球化”甚至“西方化”了,但吃麥當勞或看進口大片,并不就能改變一切。其實,文化就像海面之下的冰水,它的遷移是緩慢的,在浮動的表像背后,我們改變的東西往往并不多。譬如說,說到房子我們會照例睜大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