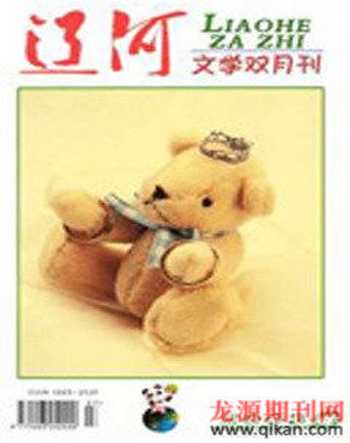踏遍青山人未老
柴福善
王充閭,當代散文大家。其作品常見諸報刊,品讀之余,便隨手剪輯。透過字里行間,章脈文心,總覺作者與我同齡。及至日前相逢于中國作代會,才知已六十有七,長我二十余歲,當為前輩了。會后,王老寄我一本《淡寫流年》,散文精品集,近五百頁薄厚,簡直沉甸甸打手。連日總沉醉其中,一讀再讀,我終于讀出了王老的“流年”,哪怕是一筆“淡寫”。
遼東南部醫巫閭山腳下,有個盤山縣大荒鄉后狐貍崗子的偏僻荒村,當年王充閭就降生于此。隆冬雪花,數九寒風,接納了他。也許出于對醫巫閭山的感激與崇敬,父親便給他起名“充閭”,從此供世人呼喚了。小時,他親眼目睹姐姐、哥哥被病魔奪走,“衰門忍見死喪多”,以至母親眼淚哭干。幼小心靈便經歷了如此殘酷的死亡悲劇,對于生命與幻滅的體驗,遠遠超出了常人。這種痛苦體驗和悲劇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一生及一生的散文寫作。
他是“大自然之子”,故鄉原本森林茂盛,沼澤密布,尤其那大沙崗子,濃蔭蔽日,雜草叢生,甚至狐貍出沒。他的童年,幾乎整天與森林、河流為伴,看螞蟻不知勞累地搬家,看狐貍機智聰明地跳躍,看鸕鶿水邊悠然踱步……在大自然的生命律動里,尋覓到人生最初的意義與快樂,無形中培孕了他珍視自然與珍愛生命的深沉情感。及至后來雖多年從政,他依然是仁者智者,樂山樂水,“業余”著文,空靈灑脫,清新飄逸,不能不說是童年感悟體察大自然情感的延續與外化。而“物我交融”、“景情合一”,就成為他生命境界與藝術境界的體現了。
六歲進入“私塾”,“束發”開蒙,盡管那已是1941年,抗戰歲月了。受業于“關東碩儒”劉壁亭,先生國學功底深厚,飽覽經史子集,詩詞文章俱佳,曾任府學督學和縣志總纂,因不愿仰日本人鼻息,便借故還鄉。外面和學堂都誦讀偽滿康德皇帝的《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及《國民訓》,老先生卻依舊講“四書五經”,講《古文觀止》,講《唐詩合解》,也講《笠翁對韻》,朗朗書聲里,這座茅舍小院簡直成了世外桃源!那時,沒有鐘表,便燃香作記,三排香燃盡,約略一個時辰。就這樣,充閭度過私塾八個春秋,奠定了國學堅實基礎。后來他在散文創作中體現出的哲學意識與美學精神,精湛的史學根底與深厚的文學功力,謙謙君子與儒雅敦厚的人格品性,應該說得益于八年私塾,得益于劉先生,以至于花甲之年回顧來路,依然念念不忘,縈系于心,并專門撰文《青燈有味憶兒時》,以抒情懷。
當他以優異成績考取盤山縣最高學府——盤山中學,從此走出荒村茅舍,走到山野之外,接受新式文明與新式教育,年僅十四歲。母親幫他穿好新衣,父親前面走著,他后面跟著,,一步一回頭,母親站在門前沙崗上眺望。在他心目中,這不是沙崗,而是一座望兒山!那時,學校藏書寥寥,很快他就瀏覽了全部文學書籍。因表現出眾,提前畢業,考取沈陽師范中文系。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恨不得讀盡天下之書!然而,怎奈新中國初建,百廢待興,亟需人才,他又提前回母校盤山中學任教。之后,相繼調縣城小報、營口日報任編輯。就在他因才華初露、工作勤懇而走進營口市委大門時,“文革”爆發,他被揪回報社批斗。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古訓銘記于心,無論在“游行示威”的口號下,在“造反有理”的日子里,還是“文攻武衛”、“反修防修”的吶喊中,他于陋屋斗室中,翻出精心珍藏的書本,系統閱讀了經史子集,觀覽了外國佳作,尤其精讀了許多俄羅斯經典名著。在生命逆境中,通過書籍,與古人對話,與外國作家交流,使他心如止水,超然物外,蓄志養氣。動亂年代,浩劫之時,不讓生命河流空白流逝,實在難能可貴。“文革”后,先后任營口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遼寧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省人大副主任,乃至前不久,在中國六次作代會上,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可謂春風得意,官高位顯了。
而他本質上是一個文人。小時一次元宵節,街上鑼鼓喧天,高蹺成隊。私塾先生喊他“對句”,且出上聯:
歌鼓喧闐,窗外腳高高腳腳;
讓他用眼前事對下聯。他忽見先生躺枕頭上吸鴉片,靈機一動,對出下聯:
云煙吐納,燈前頭枕枕頭頭。
口吐錦繡,年少才高,先生忘了鴉片,而忙不迭為他喝彩。初走上編輯崗位,正處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特殊歷史境遇,環境雖然不太寬松和諧,工作之余,仍以極大熱情,創作了短篇小說《搬家》,發表于《遼寧日報》文藝副刊,這是他正式創作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的漫漫生涯,哪怕最終沒有成為小說家,而成就了一位散文大家,但畢竟是從這里起步的。起步便是“業余”,直到現在,還是“業余”,從政為文各得其所,這在中國實不多見。1964年至1977年,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未發表一篇作品,擱筆達14年之久!1978年春節,追憶兒時往昔,創作了散文《高蹺憶》、《故壘情思》,文筆清新,結構靈巧,富有獨特的審美意趣,引起讀者好評。這年春天,走煙臺,訪蓬萊,踏威海,于輪船上構思了散文《海上述懷》,情景交融,意境優美,聯想豐富,已初露其散文特色的端倪。
進入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文藝復興,煥發了他極大的藝術激情。一方面為官,一方面為文,另一方面還傾心為學,探究哲學與美學,熱衷于邏輯思辨和直覺領悟,沉醉于歷史和人物的考證評價,創作中,他自覺地將藝術的靈感、哲學的思辨、歷史的分析及美學的領悟結合于散文創作中,使作品風光奇異,內蘊精深。1986年,《柳蔭絮語》出版,這是他第一本散文集。隨后,他守望著山水情懷,登臨觀覽,暢神林泉,走向大自然,走進名勝古跡,以自我的生命與情思同山水進行無聲的對話,叩問滄桑,追詢歷史,流連沉思。1990年,他觀瞻蕭紅故居,寫出散文《青天一縷霞》,全篇以“云”作為象征,,以對“云”不同想象與幻覺,以主體飄逸的意識流動,傳神而感傷地勾畫出才情浪漫、命運坎坷、自我流浪的女作家蕭紅的人生蹤跡,可謂精品妙筆,奇思佳構,被中央電視臺改編為“電視散文”,多次播出,受到讀者與觀眾交口稱贊。1991年,第三本散文集《清風白水》出版,產生廣泛影響,從而由一個東北地域的作家而走向全國!
1993年,58歲的他被醫院診斷為肺癌,年輕時曾患過肺結核,想不到40年后竟轉化為癌!縱然是初期,也幾乎將他打倒,終歸人類永遠征服不了死神。一時間,使他困惑、憂郁、浮躁、壓抑、焦慮、恐懼、失望、悲傷,一切希望與抱負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原來的壯懷激烈變成意冷心灰。包括文學,也曾下狠心揮手告別,無奈“凡心”難退,畢竟創作本身也是一種誘惑,一種歡愉,一種享受,更是一種責任。因此,他不甘心受命運擺布,依然讀書、思考、寫作,他要戰勝命運,戰勝死亡!也許命運明白他還沒有達到散文藝術的頂峰,也許未來中國就應該出現一位散文大家,病魔悄然隱退了,他創造了一個生命奇跡!他的人生之路,繞過山窮水盡,步入了柳暗花明!1995年,散文集《春寬夢窄》出版。他的散文,是歷史與美學的對話,是詩歌與散文的組合,總體屬于歷史文化散文,樸素自然,化情思為藝術,主體融入對象的特殊感悟,不落痕跡的靈言妙語,充滿大匠之氣,故有“南余(秋雨)北王”之譽。此書一出,旋印再版,頓使洛陽紙貴。1998年春,《春窄夢寬》眾望所歸,榮獲魯迅文學獎,這是我國最高大獎。標志著文學界對他散文的評判,標志著全社會對他散文的認同。這時,他已是63歲的老人了,距他第一篇作品發表,整整四十個春秋!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年,他默默地流淚了,這是慰藉的淚,幸福的淚。當然,他不會沉浸于淚水里,而是擦干眼淚,繼續揮筆散文,相繼出版了《面對歷史的蒼茫》、《滄桑無語》等。尤其《滄桑無語》,豁然大氣,以一條心絲穿透千百年時光,使已逝的風煙,重現華采,是真正潛入文化的游心工作,是真正面對歷史的大散文杰作。他能夠一只腳站在往事如煙的歷史塵埃上,另一只腳又牢牢立足于現在。立足于現在與歷史交談,是一種真正的歷史對話,但絕非簡單地再現,從對過去的追憶、闡釋中提示其對現在的影響和歷史的內存意義。作家文政雙棲,具有詩人本色,史家風范,獨具品格。此書一出,即在全國產生極大反響,幾度重印,幾度售罄,從而他的散文獲得了更為廣闊的接受空間,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審美檢驗,進一步確立了優秀散文家的文壇地位。
一位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大學者。王充閭就是這樣一位散文作家。因此,他無愧于魯迅文學大獎的榮譽,無愧于散文大家的桂冠。然而他不會滿足于過去,萬卷書還在讀,萬里路還在走,雖說已踏遍青山,而人未老,以更放開的心境,更蕩開的文筆,更寬松的心態,更從容的文勢,擁抱每一個明天,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的散文天地里,必有他高大矯健的身姿!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