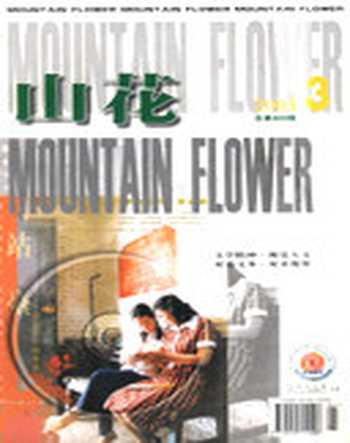當代詩歌的南京場景
鄔 蘇
1.南京詩歌的當代背景
自80年代以來,南京一直是中國詩歌的重鎮,這一點毋庸質疑。在整個80年代,南京詩人以非常活躍的姿態參與了當代詩歌的進程,那些風起云涌的詩歌社團可以被用作重要的佐證,如韓東、小海等人發起的"他們",海波、葉輝等人發起的"日常主義",朱春鶴、趙剛等人發起的"新口語",以及"超感覺"、"東方人"、"闡釋"、"呼吸派"、"色彩派"等等,這些都是參加了1986年"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展"的詩歌群體,后來還有周俊等人發起的"對話使節"和車前子、黃梵等人發起的"原樣"等等。在這些熱烈的詩歌群體活動中,涌現出了一些獨特的詩人個體和新鮮的詩歌觀念與手法。
在某種程度上,南京詩歌的狀況構成了當代詩歌變遷的一個縮影。如果說80年代南京詩歌群落和詩人個體的蜂起,在當代詩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以后,南京詩歌社團的趨于瓦解和詩歌面貌的混沌無序,也打上了當代詩歌嬗變的烙印。可以看到,就當代詩歌的整體格局而言,90年代詩歌與80年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異,與后者的基本有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90年代詩歌處于一種無序的各自為陣的狀態。80年代盡管所謂"第三代詩歌運動"帶來了喧嘩與騷動,但這種喧嘩與騷動本身,最終還是被納入了一種既定的詩歌理想之中。90年代詩歌無序的最大表征就是,文化消解力量的進一步增強,詩歌的游戲色彩愈加濃厚:在一片混沌的煙霧中,90年代出現了一批受80年代"反文化""非理性"風氣熏染的后繼者或模仿者,在他們批量復制的詩里,還固守或沿襲著低俗的口語直至口水的惡習,使得詩歌成為激情泛濫的口水式排泄物;或者,他們認為詩僅僅是一種即時的、即景的敘寫,結果寫作成了與個人的內心觸動、與時代的焦慮完全無關的文字積木。這既是90年代以后滲透在中國當代詩歌里的某種摧毀性潮流,也較深地輻射到南京詩歌的寫作之中。事實證明,盡管類似的詩在一些詩人飛揚的筆下層出不窮,但從詩藝上說,這樣的寫作已經難以為繼了。
在這樣一種整體無序的狀態中,在南京卻有另一種詩歌場景在默默生長著。我們在朱朱、黃梵、代薇、馬鈴薯兄弟、葉輝、沈娟蕾(木槿)、張桃洲等詩人那里,讀到了與上述完全不同的詩歌寫作。雖然這些詩人還不是目前南京詩歌面貌的全部,但無疑,他們的作品一定意義上顯示了南京詩歌近些年的實績。如果對這兩種不同詩歌寫作進行細致的比較,是沒有必要的。這里,我只想指出:這批詩人試圖通過一種嚴肅的寫作,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詩歌與那種流俗的貌似時尚的詩歌區分開來;他們希冀在一片喧囂的言辭泡沫中,開辟一小塊安靜的詩歌領地。顯然,詩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觀念的差異。而在我看來,這兩種詩歌寫作的最大分界點就在于,如何看待詩歌與生活的關系,即如何在詩歌中處理伸手可即、我們每天遭遇的生活。我以為對于這個時代的詩人而言,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正是在這一似乎簡單的命題面前,很多人跌了跟頭。由這一命題出發,詩人們可以被分為兩種:謹慎地對待生活的和輕率地對待生活的。當然,這種分岐和分野,也可以說是當前中國詩歌的基本分歧和分野之一,體現了整個詩壇的實際狀況。
幾年前,當南京小說家趙剛有針對性地低聲喊"生活:中國文學的劫數"時,他事實上同時揭示了當代詩歌的一個致命癥結:普遍地低于生活。置身于無可抵擋的商業主義和大眾文化浪潮中,大批詩人在"躲避崇高"的幌子下、在即時行樂欲念的驅策下、在"口語化"沖動的鼓噪下、在技巧(或花樣)翻新的誘惑下……總之,在一派匆促與慌亂的自我放逐中,乘時代的飛車疾馳而行,一路上不斷地制造著語言的泡沫和垃圾。對于生活,他們斷然采取虛浮或趨附的極端態度,他們不是津津樂道于一些生活的瑣碎和皮毛,就是緊緊迫逐著生活拱道騰空而起的煙塵。他們沉迷于放縱的嬉戲,卻被掩沒在生活的迷霧里不能自拔。在這里,談論詩歌與生活并非為詩歌寫作提供某種既定的標準,不,詩歌與生活的關系無法構成評判詩歌的絕對標尺,我們誰不是置身在生活之中呢?對于詩歌來說,生活首先不是題材的問題,并沒有任何不可以進入詩歌世界的所謂題材;同時,也不是要求詩歌去勉力深究生活的微言大義,也許詩歌能夠貢獻比哲學、歷史乃至其他文學種類更深的洞察力,但詩歌并沒有表現它自身之外功能的義務。這一點,使我想到詩人臧棣的一個富于辯證的表述:"生活的深度,其實絲毫不值得我們去研究,只有生活的表面,值得我們真正為之傾注如潮的心血"。我想,詩歌與生活這一命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用詩歌提純來自生活(包括歷史、個人)的各種經驗、賦予生活某種高于其上的意義(哪怕是無意義的意義)?用緩慢的、充滿疑慮的姿態抵抗生活和時代的加速度?用一種頑強的虛構糾正、重塑充滿雜質的現實,既然"虛構是現實的源頭"(黃梵語)?
對南京詩歌近幾年的進展略作打量的人都會注意到,正是一批有著自覺意識的詩人,正通過堅實的寫作改變著一度處于低迷的南京詩歌圖景。毫無疑問,一方面,他們的詩歌沒有遠離時代的生活場景,而與他們身處南京這一都市的境遇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一種新的浮泛的"本土派"和"后現代"論調不同,他們并不倚重詩歌外在樣態的遷移,而是更注重詩歌內在質地的培育。就這批詩人作為都市詩人而言,他們可能會遭遇某種居心叵測的詰問:如果說有波德萊爾的憂郁的巴黎、艾略特的多霧的倫敦,哪里是你們(詩歌)的北京、上海還有南京呢?在這里,將南京詩歌作為一個集合名稱提出,并非出于地域或題材的考慮,毋寧說這樣的稱呼強化了南京的整體氛圍:那似乎沉睡的悠長歷史和一般人所習見的江南氣息,那些映襯著文化面影的建筑、園林、街道甚至地名--它們"大多與日常生活相關,具體而細微,令人稱道。這些地名并不僅僅是生活之外的政治意象或修辭學,相反,它更像一面鏡子,體現出對生活細節的敏感。這些地名幫助營造了一種特殊的城市情調,城市文化個性也因之更加強烈"(黃梵《南京:蒙面的城市》)。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的烘托下,南京的詩人們向當代供奉了值得考究的詩歌寫作個案。
2.南京詩歌的個案分析
90年代中期我路過南京時,聽一位友人講,目前南京只有朱朱一人還在寫詩。這位蓄著一頭長發、臉上始終流露出淡淡的高傲表情、曾被詩歌界稱為"碩果僅存"的詩人,一直保持著特立獨行的處世態度和寫作風格。學法律出身的他,在經過一番輾轉后最終定居南京,蛩居于南京東郊的一幢別墅式小樓里,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在一些隨意的交談和文字中,他對南京的熱愛溢于言表。毫無疑問,朱朱在他那一輩詩人里,始終處于最優秀者的行列。有論者曾評價他"以他的細密精致、優雅從容以及類似自由賦格曲的語調重新恢復了抒情詩的尊嚴和原生狀態。而他古典式的詞語配件、短促的句式與華彩樂章般的即興感在同類詩歌中更是卓爾不群"。的確,朱朱詩歌最鮮明的特征就在于,語言簡約而豐沛,具有纖細而強勁的質感;形體顯得精致乃至精粹,呈現雕塑般的刻痕,卻又了無蹤跡。這些品質,在他90年代初的一些詩篇如《揚州郊外的黃昏》、《下午不能被說出》、組詩《小鎮的巴洛克》等中,就已初步確定。較有代表性的如短詩《樓梯上》:
此刻樓梯上的男人數不勝數
上樓,黑暗中已有肖邦。
下樓,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
其簡約句式在瞬間的展開給人閱讀上的震驚,凸顯了現代漢語所蘊藏的詩意彈性。90年代中期,朱朱在他的《一個中年詩人的畫像》中顯示了高超的"敘事"能力;近年來則有《枯草上的鹽》(組詩)、《清河縣》(組詩)、長詩《魯濱遜》等。詩風逐漸豐富,開闊。《魯濱遜》的迂回曲折,《清河縣·頑童》對西門慶語氣的反諷式戲擬,顯示了朱朱在詩歌結構方式上的多樣化特點:
現在雨大得像一種無法伸量的物質
來適應你和我,
姐姐啊我的絞刑臺,
讓我走上來一腳把踏板踩空。
在南京詩人中,黃梵是較多地表現出優異的文學才能的一個。這里的文學才能,一方面是指他善于運用多種文學樣式進行寫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作為小說家的聲名超過他的詩名),另一方面是指他對文學公益事業的有力組織和推動。尤其后一點可以說有目共睹,如早年的《先鋒詩報》、《原樣》,后來的"南京評論"網站,都體現了一種奉獻品質和敬業精神。也許黃梵自己也沒有想到,在熟練地掌握一套與"飛行動力"有關的艱深理論后,在后來的歲月中幾乎不再碰它,而是朝另一完全不同的領域走進去,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但學生時代所受的專業訓練顯然有益于他的寫作,譬如,他至今也沒放棄的對數學論證的熱衷,賦予了他作品結構的精確與內在繁復。他巧妙地習得了理工科思維的嚴謹、縝密,而后者的刻板、教條與他豪不沾邊。這些促成了他早期詩歌的唯美傾向與思辨色彩,促成了諸如"在燕子的繞行中,在船舶靜靜的停泊處/她已經看見那被稱頌的淚水在趨向最后一招"(《"等待云雨中陰黑的鞭子落下來"》)、"雨霧中的一陣車鳴/像記憶中的無法下葬的錯誤/像紛飛的嘆息"(《溫暖春天里的一場呼嘯的大風"》)、"飛嗎?在浮云無法攀親的高度,/直到城鄉在大地的圖景上靜下來,直到幸福追得上腳趾的腫脹"(《列車上》)的華美詩句和令人感到詫異的語詞間的跨跳風格:
難以察覺,一座城市銅像
失眠的側影
忽然掉下來的尷尬
即便他是龐大的入城式隊列中的飛蛾
穿過了紅燈之間
失去幻想的廣場
--《城市之光》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其他文體寫作的滲入,黃梵的詩風有較大改變。我不知道他自己如何看待詩歌寫作與其他文體比如小說寫作的關系。而在我看來,其他文學樣式帶給他詩歌寫作最大的益處就是,更多異質成分的加入使得他的詩歌表達方式更加變化多端,更加尖銳,能夠處理甚至有些"病態"的題材。這些充分體現在他近年來的短詩如《幸福》、《制花工》、《墜落》和最近的《沙塵暴》、《灰色》、《落日》等詩篇中。
學芭蕾出身的女詩人代薇,她的詩中一直有一種與這種高難度舞蹈藝術相對稱的形體、功力和氣質,那就是:優美、勻稱、富于內在的節奏,也沒有過于冗長的篇幅。然而,也許與她對于地域遷徒(從重慶到南京)的敏感有關,在她美麗、平和的外貌之下,卻有一種深深的無可名狀的異鄉感,這使得她的很多詩篇透出罕見的凜冽與鋒利。如《鴿群從臉上散開》:"翅膀在高處試到風速/在強烈的反光下/像一些飛起來的刀片/將天空劃開又合上",強調的是鴿子飛翔的高度而不是其安詳的身姿,并用一個尖利的意象("刀片")突出了這一高度。大約在1997年前后,代薇詩中的這種凜冽感越發濃烈,在她的《再度降落》、《美國黑人雙人舞》、《大地的胸前靠著月亮的臉》、《易碎品》、《旅途》等詩中均有所展示,而尤其體現在這首堪稱杰作的《無題》中:
猛一回頭,你的臉在飛旋的落葉間迅速散盡
我張開手指,摸到你留在風中飛揚的衣襟
記憶的細節與現實的情景融為一體,跳躍的幻象與可感觸的具象交錯呈現,某種難以言述的痛楚彌漫其間。代薇同時是一位寫散文的能手,與她的詩歌相得益彰。因而從總體上來說,盡管她的文字是細膩的,卻顯示了與陰柔的南方氣息并不一致的女性特點。即使表達愛情的詩篇如《早晨》,歡愉中的抑制和微妙的分寸感是一般女性詩歌少有的:
在鄉間醒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陽光照射進來
像一杯剛剛擠出來的泛著泡沫的牛奶
還帶著牛棚和干草的氣味
睡衣的顏色
身體像鏤空的花邊一般單純
正如我對你的想念
它已沒有欲望
我會想念你
但我不再愛你
今年9月,在南京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網絡詩歌結集《中國網絡詩典》,書的編選者就是馬鈴薯兄弟。他既是以于奎潮之名、在出版這部詩選的出版社任職的一名編輯,又是近年來在各大詩歌報刊、網站上十分活躍的一位詩人。也許少有人知道,馬鈴薯兄弟是一位已有二十余年詩齡的詩寫者,同時是一位十分難得的持嚴肅態度的高產詩人--據說有時他一天能寫十來首長短不一的詩,但這些詩都不是隨意寫成的游戲之作。他本人在內心里對詩歌懷抱著很強烈的虔敬和很高遠的理想,這些年他一直在苦苦地思考和探索詩歌的變革之路,而他的寫作實踐也不斷向更高的境界邁進。馬鈴薯兄弟的詩歌旨趣集中在對都市世俗生活的審視,他對發生在都市的日常景象和潛隱于其中的人生痛苦,進行了精細的刻畫和深刻的剖析,如《曖昧的街》、《戰國女士》、《早晨通過一匹馬的身》、《黑衣婦人》等,這些詩篇看似隨意、輕松,實則隱含著不容忽視的主題。在他的一些詩里,顯示出某種輕微的"邪",但他能夠熟練地保持莊與諧之間的平衡。他的詩歌在語言運用上也這樣,較多精短的句式,顯得自然、輕逸,散發著日常生活的氣息:"一些小蛇/在油菜花下/它們渾身圓潤柔軟/像一截截水管∥一些游春的女孩/走過油菜田埂/她們快樂地驚叫/因為小蛇/從她們的腿間/游過"(《春日》)。正是在這平淡的外表下,生活的某些本質被直接有力地揭示出來:
這一刻
他感覺到的是愛情
他卻希望她是一個妓女
--《生活習慣》
近年來較少在詩壇拋頭露面的詩人葉輝,一直在他的出生地--南京某郊縣的一所國稅局當公務員。他曾參加過轟轟烈烈的"第三代詩歌運動",后來的寫作卻遠離了這一運動所鼓搗起來的喧囂,基本上處于一種潛伏的狀態。葉輝屬于那種具有深刻獨立見解、對自己詩歌的未來保持清醒認識的詩人。在為參加1986年"詩群大展"草擬的《日常主義宣言》(與海波合作)中,他寫道:"我們要為自己確定一條自由的、日漸擴張的藝術空間的途徑";那就是,"在對日常事件的陌生與困惑里,運用從容且較為正規的表達方式,努力縮短抽象觀念與理性結構之間的跑離,從而訴諸于更廣泛的精神現狀的表白"。"第三代詩歌運動"作為一種事件和觀念已經成為歷史,葉輝本人也通過這些年的獨立寫作,逐步調整、豐富著自己的詩歌路向。在他近些年的《一個年輕木匠的故事》、《小鎮的考古學家》、《老式電話》、《合上影集》、《果樹開花的季節》等詩篇中,"日常主義"的信念依稀留存,但某種刻意而為的印痕消失了。他不是讓生活從某個可見的正面進入詩歌,而是從表面或側面進入;他的詩句也是沿著細碎的生活側面,輕輕地掠過:
我想著其他的事情:一匹馬或一個人
在陌生的地方,展開
全部生活的戲劇、告別、相聚
一個淚水和信件的國度
我躺在想象的暖流中
不想成為我看到的每個人
--《在糖果店》
沈木槿是南京詩壇的一名后起之秀,曾以令人驚訝的年輕參加了《詩刊》社舉辦的"青春詩會"。她雖然至1998年才開始寫詩,但無疑具有很高的起點,表現了對詩歌藝術深入本質的悟性。她最初的一批詩顯示出不俗的品質,震動了西渡、龐培等詩人。沈木槿的某些詩篇,可能與她早年在鄉間的生活有關,她對那些散落在記憶里的美好、質樸的瞬間進行了詩意的捕捉,比如這首散發著雨后清新氣息的《草》:
把大雨打濕的草抱回羊棚。
看它們把下巴埋入草里。一只老羊
銜著草,低低叫了一聲。
我沒有回頭,知道祖父從后門進來了。
一早我睡著,聽見他在磨刀。
"要下雨呢。"
他是去河邊那片低地割草。
昨天我打那兒路過,告訴他草長得很深。
全詩的結構自然天成,語言顯得干凈利落,詩句與詩句之間作著渾樸的呼吸。這在《暮色》、《早晨》、《歸途》等詩篇中也有所體現。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她過于單純的經歷(她曾擔任小學教師八年),她不得不把筆觸轉向內心的開掘,試圖通過某種內斂的力量支撐稍顯單薄的詩句,如《信》、《練習曲》、《讀》等。正如詩人龐培評價說,"她單純、清澈的詩行里積蓄了一種克制著的深沉、強大、甚或反叛的力量"。《凝聚》恰如其分地顯示了這種努力,它讓我們知道,一旦集束的內力散開,就會光彩四溢:
醒來的身體
溢出微小的驚慌。
看我入睡的人已離去。
留下一個屋頂,傾斜著雪。
一只檸檬,在桌上
凝聚著光。
作為這幾位詩人中唯一一位具有更濃的所謂"學院"背景的詩人,張桃洲的詩名實際上鮮為人知,盡管出人意料的是他已有十數年的寫詩歷程。他在以一篇研究詩歌話語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后就留校教書,一邊做詩歌方面的研究和評論,一邊寫詩,同時在講臺上給學生開的課程也是詩歌課。張桃洲一直處于一種較封閉和隱蔽的寫作狀態,只是最近幾年,他的一些詩篇才在友人之間傳閱。顯然地,他是一個冷峻的觀察者、思索者,而不是熱忱的歌頌者、抒情者。他早年的詩具有鮮明的形而上特征,這一特征一直延續到后來的《死者》、《木偶戲》等;直到寫于南京的幾個組詩如《南京十四行》、《穿過學堂的拱門》等,他才在詩里貫注某種豐厚的品質,顯示出一個具有理性精神的詩人對生活境遇的縝密洞察。他的詩注重語氣、語感的精心調配,顯得從容和沉靜。在他的近作《家樂福超市》里,他能夠把對個人生存處境的觀視與對生命意義的終極思考、將戲謔式敘述與謹嚴的場景刻繪較為圓熟地融匯起來。而他的《地鐵站》則在構思上顯出創意,與很多同類主題的詩歌不同的是,這首詩并沒有關注、處理代表了都市景觀,如時間一樣圍聚在地鐵站的熙攘的人群,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某種"未完成性"上,體現了不一樣的對現實處境的觀察和處理方式。
我是否需要在這里,在一處
尚未竣工的地鐵站中轉?這樣
想著,公交車已繞過新街口
闖入一片昏黃的燈火。
因而詩中所展示的,也是懸在半空的、進行中的內心迷惘,這種迷惘隨著這種"未完成性"而縈繞在都市"一片昏黃的燈火"中。
3.南京詩歌的嶄新氣象
以上通過對幾位南京詩人的粗略討論,我有理由指出,正是倚靠他們的嚴肅、執著和勇于探索的寫作,南京詩歌才呈現出嶄新的氣象。同時,他們展示的較為均衡的實力和成績,也為當代中國詩歌注入了某些新質和活力。總的說來,這批詩人已經表現出如下可予期待的潛力。
首先,在這批詩人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點是,除沈木槿外其余幾位都有十年以上的寫作經歷。應該說,十幾年的寫作能夠為一位詩人鍛造很好的基礎。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并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長期堅持不懈的累積的--不僅在詩歌技藝方面進行訓練,而且也要進行心智的磨礪。那么,經過多年的沉潛與蓄積,這些詩人的基本品質已經穩固,當他們浮出水面時,水面之下實際上潛隱著厚重的底座。也就是說,他們的寫作建基于一種良性的積淀,這種寫作的有效性即來源于這種長期累積的強大支撐。
其次,多年的寫作經歷,使得這些詩人有機會與某些詩歌傳統進行切實的溝通,哪怕這些傳統是駁雜的。但無疑,他們詩歌的豐富與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們豐富的詩歌實踐。比如,葉輝是感受過80年代"第三代詩歌運動"的熱烈與騷動的,這一經歷對他的寫作的重要意義在于,一方面他通過參與、親歷那樣的詩歌氛圍,不僅從中獲得詩學的滋養,而且能夠比較清醒地意識到其間的創造與局限;另一方面在后來的持續寫作中,他通過自覺的對以往詩歌的反思和修正,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寫作路數。同時,這種長期寫作帶來的時間跨度,也便于他們詩歌技藝、心態乃至風格的變化與轉型。這方面的突出例證如黃梵,他的寫作明顯地被90年代中期劃分為兩個時段,后期同前期相比其轉換是巨大的,后期的尖銳、靈巧與前期的唯美、鋪飾形成對照。當然,這種具有明顯分期性質的轉換,在黃梵那里還會延續下去。其他幾位詩人也多少完成過類似的轉換。
再次,這些詩人保持了嚴肅的詩藝探索的態度,并已顯出銳意進取的趨勢。我想,沖破既定秩序、為詩歌爭取更大的自由空間,放棄墨守成規、尋求詩歌表達的多種可能,是多數詩人孜孜以求的事情。不過,在詩藝不斷突破的取向上,有些詩人是建構性的,有些詩人則是拆解性的。南京的這批詩人無疑屬于前者。可以看到,這些詩人立足于漢語本身和現時代的語境,嘗試著多種進入詩歌的方式;他們的探索有別于那種泡沫似的鼓噪,而是通過一些有意義的創構,為漢語詩歌寫作提供了值得考究的范型,比如朱朱的克制敘述與縝密質感,黃梵的遠距離騰躍與語詞變焦,代薇的外部精巧與內在激越的奔瀉,馬鈴薯兄弟在句式快速滑動與主題沉陷之間的調諧,葉輝的旁敲側擊與共時呈現,沈木槿的輕度寫意,張桃洲的層層深進與平面鋪陳的結合,等等。
我感到,這批詩人已經為南京詩歌的未來生長營造了良好的氛圍。雖然他們的作品尚未得到充分展示和評價,但毫無疑問,其重要性正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覺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