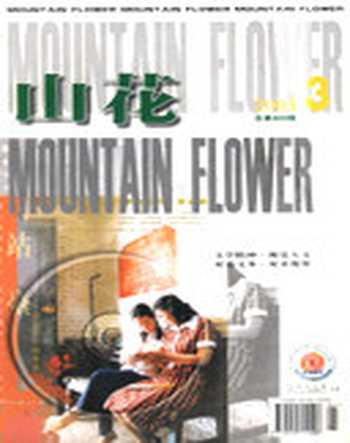讀書:靈魂之間碰撞的契機
閻連科 梁 鴻
閻連科,當代著名作家(以下簡稱閻)
梁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以下簡稱梁)
地點:閻連科家中。
時間:2002年3月14日
卡夫卡、福克納和馬爾克斯
梁:今天我們談談讀書。我注意到你正在讀《古拉格群島》,你平常是怎么讀書的?喜歡讀些什么書?讀書的經歷是什么樣呢?
閻:就我來說,是中國作家書讀得較少的一位。在最需讀書的年齡,我們這一代讀的是《解放軍文藝》、《金光大道》、《艷陽天》、《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等。因此,讀這樣一些書,你的寫作起點自然非常低。當80年代中期,有條件接觸到西方作品時,我的悟性又比較差。如《百年孤獨》這樣的書,它最走紅的時候,我也買了,居然沒有讀下去。
梁:為什么?
閻:這可能是我的文化基因決定的。就像一個人從小生活在封閉的鄉村,突然之間,你讓他進入城市會有一種不適應,有一種陷入感,無所適從;還如一個人從小就吃中國菜,突然來一桌西洋大餐,吃幾口,他就會覺得還是中國菜更好吃。但是,到九一年、九二年,那時候我腰疼得厲害,整天只能躺著,再看《百年孤獨》時,才發現它居然是這么好的作品,了不得的作品。
梁:為什么會有這種讀書的情況?
閻:說不清原因。如卡夫卡的《變形記》,我并沒有馬爾克斯讀卡夫卡時那樣的震動,馬爾克斯看完《變形記》之后,他被震撼了,驚得目瞪口呆。他在一瞬間忽然明白:"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馬爾克斯是站在卡夫卡的肩膀上向世界文學沖刺的。而我可能只是站在浩然的肩膀上向世界東張西望的。這種起點的結果你可想而知。人家是站在山頂之上,而你是站在山腳之下,不要說是寫作,就是數星星,站在山上也不知要比站在山下多數出多少來。
還說卡夫卡--好像談讀書不談卡夫卡就是不行。我真正喜歡卡夫卡是在前年,2000年,你看這是多么的晚,比起同代作家晚了十幾年。2000年我去西安治病,重又看了以前沒有看下去的《城堡》和《審判》,覺得的確不得了。首先,這種不得了來自于一個作家的敏感,原來覺得生活和想象是創作的源泉,現在忽然發現,原來一個人的敏感也可以成為創作的源泉。他抓到了這一點,而別人沒有抓到。我們五十年代抓到是"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現在一些人堅信"想象是創作的源泉",卡夫卡告訴我們,"敏感也可以成為創作的源泉",它可以是他取之不盡的源泉。其次,通過卡夫卡,我發現了我的遲鈍。我的遲鈍使我震驚。這種遲鈍甚至近似一種麻木。
梁:你怎么看待卡夫卡的敏感與寫作的關系?
閻:我沒有看過卡夫卡的傳記,但我知道一些,我堅信,他的那些經歷,對我們這些來自鄉村,有各種各樣的生活經歷和貧窮、渺小的家庭背景的人來說,算不得什么。卡夫卡的經歷,就像我們出門餓了一天肚子、回家時又走錯了路一樣。照他的經歷,中國作家寫一部小說也就夠了。可能還是一部很一般的小說。但是,卡夫卡卻不是一部、他在那么短的生命之內,竟然寫了幾部對整個世界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為什么會是這樣?說穿了,就是因為他的敏感。
梁:能把敏感說的更具體、形象一些嗎?
閻:你比如說,有一根針落在卡夫卡頭上,他一定感到那根針把他的心扎出了血,而一架房梁落在我們頭上,我們可能把頭上的灰土擦掉就算了。這就是敏感和遲鈍的差別。落下的那根針,卡夫卡感到整個世界都受到了傷害,而落在我們頭上的那根房梁,睡一覺我們就忘記了。敏感,對于寫作,有著巨大的決定性的意義;而遲鈍,只對生活、對我們說的過日子有些意義。
梁:那你說,我們沒有敏感怎么辦?
閻:卡夫卡的敏感是天生的,我們的遲鈍也是天生的。天生的沒有敏感,就只能靠后天慢慢去減少遲鈍了。
梁:你是不是覺得你對卡夫卡的理解晚了些?
閻:對,我遲鈍、麻木,這是沒辦法的事,是寫作的天敵。
梁:喜歡福克納的作品嗎?
閻:喜歡。但和別人喜歡的不太一樣。
梁:哪里不一樣?
閻:我至今沒有看完《喧嘩與躁動》,而他的《八月之光》、《熊》、《我彌留之際》,我卻看得津津有味。為什么沒有看完《喧嘩與躁動》,我卻說不清,不知道為什么。有時候,一部好的作品與作家產生碰撞是需要契機的,尤其那種靈魂的碰撞,是需要靈魂溝通的契機。如果有了這種契機,可能你讀幾頁,甚至幾行就使你領會了他作品的全部,之所以你還要把他的作品繼續讀下去,僅僅是為了證明那種契機、溝通的正確。
梁:是不是處在生命的寂靜時刻和沉靜狀態,才更容易體會小說真正的含義?它可能使人的思維處于一種澄明的情況之下。
閻:也不完全是這樣。比如原來對《變形記》,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現在發現,《變形記》的的確確是非常偉大的。我大概是81年或是82年看的《變形記》,老實說,我一點不喜歡。這種不喜歡不是看不懂,是不喜歡一夜之間把人變成蟲。我覺得卡夫卡讓他變得太生硬,不自然,缺少說服力。但是,90年,當我因生病躺在病床上,才打開《百年孤獨》的第一頁,就讓我目瞪口呆了,馬爾克斯這樣寫道:"他拽著兩塊磁鐵挨家串戶的走著,大伙兒驚異地看到鐵鍋、鐵鉗、小鐵爐紛紛從原地落下,木板因鐵釘和螺絲沒命地掙脫出來而嘎嘎作響,甚至連那些遺失很久的東西,居然也從人們尋找多遍的地方鉆了出來,成群結隊地跟在那兩塊魔鐵后面亂滾",這種寫法令我著迷,我發現卡夫卡的確成為了馬爾克斯的階梯。卡夫卡讓人變成蟲,他的偉大在這一個"變",而馬爾克斯則在這一"變的過程"。馬爾克斯比卡夫卡更接近于真實,卡夫卡比馬爾克斯更接近抽象。卡夫卡沒有把變成甲蟲的過程寫出來,盡管他也寫了作為甲蟲的人的活動情形,但這個過程肯定不是一下子變成的。卡夫卡沒有給我的"過程",馬爾克斯替他給我了。可是,沒有卡夫卡,又哪里有馬爾克斯呢?沒有《變形記》,又哪里有《百年孤獨》呢?馬爾克斯使卡夫卡的"變"--變得完全可信了。對于《變形記》和《百年孤獨》,我完全是從《百年孤獨》第一頁的兩句話開始領會的。其實,真正給我啟示的,就是閱讀第一頁的那一瞬之間。
梁:是那種思維,忽然產生了一種通透的感覺吧?
閻:是那種通透,一下子就來了。
梁:剛才你提到《城堡》、《審判》,其實它們表達的都是一種意念,如《審判》,就是寫的人的一種狀態:一個無形的力量支配著你的生活,但你又找不到具體的對象。
閻:中國作家老是爭論作家是先有意念啊,還是先有經驗;是先有生活還是先有意念,如此等等,我覺得對于卡夫卡來說,毫無疑問,肯定是先有意念的。但是,是什么支持了他的意念?使他的意念變得如此真實而又堅實,產生出如此偉大的作品?我以為--那就是敏感。他感受生活的方式就是這種敏感。敏感可能成為生活和意念之間的橋梁。什么能成為我們自己的某一橋梁,使你達到一種頂峰?如是找到的話,那你可以從此岸到彼岸。找不到的話,你就永遠在此岸。尋找那樣一種過渡的東西,而不是一種情節,或一個細節和寫作方式,應該是作家最最重要的。
梁:對,它肯定不僅僅屬于技巧性的東西,而是你進入世界的一種思維。
閻:如果找到的話,那么,一個作家可能就真的非常了不得。
川端、大江與安部公房
梁:你對日本的小說感覺怎么樣?如川端康成和現在非常流行的大江健三郎等等。
閻: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川端的作品。我們不要拿長篇來評價他,他的長篇可能沒有一部在結構上是完整的、成功的。如《雪國》、《千只鶴》等等,就長篇而言,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是,他的文學成就無可挑剔,如他的語言。我個人欣賞他,是因為他的語言更有東方文化的神韻。
梁:可能是他傳達出的那種憂傷與細膩的氣息更接近我們的心靈。
閻:還有那種對女性的珍愛,那種憂傷的美和美的憂傷并不是每個作家都有的。對美的憂傷是川端從此岸到彼岸的過往之橋。
梁:他把人類最細微的情緒表達到一種極致:那種對人類情感最深處的細致的靈魂關照。
閻:你再想一下沈從文,他的美不言而喻,但是,他的憂傷卻遠遠不如川端。沈從文對我們來說是了不得的,但是,他的確缺乏這種來自于靈魂深處的憂傷。
梁:這種憂傷其實是人性一種本質的東西,缺乏這樣一種憂傷是否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有關?
閻:也不盡是這樣。我們看川端的簡歷,會發現他從小多災多病,家庭極其不幸,這種經歷形成的性格,決定了他對日本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持悲觀態度。而沈從文離開湘西,對湘西進行無盡贊美的時候,這種憂傷自然就會少得多。
梁:大江健三郎呢?
閻:說實話,他的作品我沒有一部看完的,也談不出什么東西來。這并不是說他的作品不偉大,也許他的作品非常偉大,但是,對于我來說,要喜歡上他的作品,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契機。現在,大江在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影響很大,但像我這樣沒有看完他一本書的也不在少數。
梁:應該說他的作品比較難"看",但對人的沖擊力非常大,尤其是他對日本當代社會的精神狀態的描寫非常獨到,對日本民眾的那種空虛、扭曲和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
閻:我讀書的毛病比較多。如村上春樹的小說那么多人看,可我前前后后,三次花了三個半天的時間也沒看下去。我知道我讀書太狹窄。
梁:看沒看安部公房的作品?我覺得你們之間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他的《砂女》、《箱男》等。
閻:對,我很喜歡他的作品。但他的小說也有某種把人變成蟲的生硬感。比如《箱男》,一個人背著箱子如何如何,有某種非常明顯的概念化的東西和先驗的理念在里面。
梁:可能太理念化了。
閻:這種理念如何和讀者日常經驗溝通的時候,我覺得其中缺少某種過渡的橋梁。理念可能非常偉大、非常了不得,也很有哲學意味,但是,就小說藝術而言,仍缺乏一點東西。
梁:像《砂女》,背景是海邊,人們生活在沙挖的房子里,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不停地從房子里往外倒沙,一天不倒,沙就可能填滿你和你的房子。這種生存動作的反復性和對生存的韌性形成一種寓言意義,并且跟你小說中的先爺和尤四婆的生存狀態有某種相似和相通的地方。
閻:這也有可能。但對我來說,看他這篇小說的時候,最驚奇的是人為什么住在那樣的地方呢?后來看到一個資料,說海水里面的鹽可能會形成某種堅固性的東西,使人們能夠筑屋挖洞。后來,我又到三門峽去,發現了一種"天井院",從平地上挖出一個大坑,然后從坑下往四處擴散再挖,里面有客廳,臥室,還有水井等等一整套的東西。看到這種建筑之后,我才對安部公房的小說有一個新的理解,它還是有真實性的經驗在里面的。
梁:當時我看完《砂女》后,有一種特別受震動的感覺,不僅僅是他們生存的艱難,而是作品中對這一行為的不停的、細致的刻畫,讓你不由自主的感受到某種抽象的意味,就像你《年月日》中的先爺,讓玉米在自己身上汲取營養,特別具有一種寓言化的因素。你剛才也講到卡夫卡小說的意念和敏感性的東西。其實,到最后,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巨大的沖擊力。這種沖擊力可能也就是一個東西,一個事件。如《審判》,通篇就是被審判者尋找要審判他的人,兩者都不知道力量來自于哪里。人物就在這樣一種無名的壓力下一天天地活下去。作者運用各種形式各種場景來描述處于這樣一種狀態中的人。
閻:在寫作之中,思考得多了,你會發現,其實人類巨大的疑問常常可能被一個簡單的、抽象的場景所包容。如果你抓住了它,一個優秀的作品也就產生了。
梁:你前面所提到的"痛苦的激情",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點,激情也是一種作品的凝聚力,它形成一個完整的內核,產生一種爆發力和沖擊力。
閻:可是,小說抓住了這樣一個契機,又如何讓它和真實接軌?這中間有一個過渡,卡夫卡運用了他的敏感和那種神經質,馬爾克斯用了他想象和魔幻。而我,可能是在作品通過激情來完成這樣一種過渡的,這肯定是一種很笨的方法。在沒有找到一種其它方式之前,我只能用它和某種真實與日常接軌,至少在目前對于我來說激情能完成這樣一個要求。但激情又不一定是獨特的,若它完成了你的過渡,過渡過來,你的思考就可能表達了出來。否則,可能三句話就完了,一切都完了。
梁:是不是可能這樣說,小說最初的來源是一個意念,最終也以一個抽象的意念而結束,而這其中,是通過作者自身某種巨大的能量傳達出來的?
閻:我想,肯定有一種小說是這樣。說到底,這種小說的作者,都對世界有著巨大的疑問。寫作,是疑問的表達。
梁:日本作家,你還喜歡誰的作品?
閻:喜歡大岡升平的《野火》,喜歡橫光利一的一些短篇,最喜歡德田秋聲的《縮影》。我以為《縮影》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無技巧"、渾然天成的小說。
喬伊斯與博爾赫斯
梁:你對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一類作品如何看?它們和福克納的小說完全不是一個類型。
閻:毫無疑問,它們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偉大作品。但是,它們和我個人還缺乏某種溝通性,或者說,我和它們之間缺乏某種契合。這樣的作品我在閱讀時,總像隔著一層紙。但他們對世界看法的表達能力讓我驚訝。包括博爾赫斯。這樣一批作家,我讀得最多的是后者。我非常認真地看完了博氏的大部分小說,因為它們都非常短,不像《尤利西斯》那么洋洋灑灑,得需要極大的耐心。我覺得,我還是和它們缺乏溝通。當然,你不能說他不是偉大的作家。這樣一類作家達到這樣一種高度,他們的高度抽象能力、知識的淵博和某種哲學感悟力無可挑剔,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哲學具有某種天賦。對我來說,博氏語言的精煉給我帶來小說語言的思考。就我個人而言,尤其是長篇,我還是喜歡具有沖擊力的作品,但它又不是落入俗套、平鋪直敘的,講個故事什么的。
梁: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深層思維和意識的沖擊和震撼。
閻:可是,他們的作品并沒有給我帶來沖擊和震撼,至少目前我還沒有感受到。我覺得一批作家的作品暫時無法接納也好,這給以后的閱讀留下一點空間,一下子都接納完了,可能就不知道再讀什么了,寫什么了。
梁:你正在看《古拉格群島》,你怎么看俄國這樣一批作家?他們帶有明顯的知識分子傾向,包括《日瓦戈醫生》。
閻:俄羅斯的歷史和中國歷史太相像了。看了《古拉格群島》,認識了蘇聯的歷史,你就會了解中國的某些歷史或某一革命階段的來源。借助《古拉格群島》,你想的是中國的歷史。但是,看了《古拉格群島》之后,你會明白,真正人類偉大的具有震撼力的東西,是不需要技巧的。你會發現,技巧在人類苦難的真實面前,只能是一種樸素。就是說,在巨大的痛苦面前,是沒有技巧可言的。
某種東西是不能去想象的,必須來自于真實。我們必須意識到,當你真的面臨著這么一個古拉格群島,要把記憶留給人類的時候,一切語言和技巧都是淺薄的。后來我就想,如果有可能,身體也允許的話,我會去調查河南上蔡縣的艾滋病。如果我能真實地記錄下這樣一個世界性災難在中國鄉村的狀況,我會放棄一切小說的技巧和文學修養。這至少是我的一個心愿。河南有許多事情需要一個作家去做。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河南餓死了幾十萬人,好像是因為饑荒,蝗蟲。其實,從資料顯示,那三年有很多地方還似乎有些風調雨順。當然這種事情過去了,人們只能靠"想象"來說是"自然災害"。可是,究竟是什么造成這么大的災難呢?這需要一個作家去思考、去調查,去研究。現在,河南的艾滋病問題,我覺得它和"三年自然災害"同等重要,需要作家去關注。作家所能完成的是當他們得了艾滋病之后,他們的精神狀況,生存境遇,內心的痛苦,這決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和電視畫面所能表達的。今年,如果我能把我計劃中的一部小長篇完成的話,我想去試著做這一件事情。寫完之后,可能也不會發表,放在抽屜里,但我想作家應該去做。這就是我看《古拉格群島》的收獲。
梁:河南的愛滋病,是人類的大悲劇。劉震云寫的《溫故一九四二》,表達的也是這樣一個主題。它用一種大的歷史話語掩蓋了個體生命的需求和真實的境像,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會去想是什么東西把他們、把人類推到這種境地。
閻:《溫故一九四二》,畢竟還存在那么一場大的災害,而"三年自然災害"的三年,和正常的年份其實并不差多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完全把真實的歷史掩蓋了。對這段歷史,一旦有真實性作品問世,很可能會像《心靈史》一樣具有一種震撼力。
梁:我們期待著早日看到你寫出這類"真實性作品"。
閻:當然,《心靈史》帶有某種宗教傾向,但作為正常人去閱讀,也是非常震撼的。那么,如果我們能寫出這樣一個大的人類愛滋病的悲劇存在,可能會是一個作家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梁:其實,它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它的悲劇性超出了人類的想象力。
閻:社會問題可能三言兩語就交待清楚了,但是,交待不清的東西誰來交待?這就是需要作家來做。
梁:你看沒看過英國作家奧威爾的《一八九四》?
閻:沒有。
梁:它主要描繪了在極權時期人的生存境況,在那里,人無時無刻不受著監視,并因為"思想罪"被逮捕或永遠消失。書中的男主人公溫斯頓是一個在"真理部"工作的有點反抗意識和懷疑意識的人,但是,正是因為他這點意識的流露,他被抓了起來,被放置于最殘酷的環境,最后,他背叛了愛情和自己,成為一個完全沒有自我的人,他的生活才恢復了平靜。這本書被看作是"反烏托邦主義"的典范之作。
閻:人家的作品,總是能深入人類的內心,輪到我們,卻又總是不行。
梁:你對知識分子是怎樣看待呢?
閻:毫無疑問,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讓我寫一個農民的生活可以,如果讓我寫教授,你可以想象他的情感和農民相似的一面,但我寫不出他們情感的另一面。而這另一面,恰恰是他們本質的東西,而這卻是我無法把握的。
梁:博爾赫斯是作家的作家,作家中的知識分子,你怎么看博爾赫斯?
閻:博爾赫斯好像是全世界作家的老師,他太受崇拜了。中國作家對博爾赫斯的崇拜,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作家的敬仰。連那些沒有讀懂、沒有讀完、沒有讀或者讀了看不進去的作家都非常崇拜他。可有一點我不明白,既然你沒有讀他的作品,或者沒有讀懂他的作品,你為什么要崇拜他?當然,有一部分作家,他們尊敬他、崇拜他是有道理的,應該的,因為他們畢竟從他那里獲得了某種東西。但是,像我這樣還沒有和他達成某種溝通,如果也去崇拜就有些盲目了。那種依賴哲學思考和哲理寫作的作家是非常偉大的作家,對這樣的作家,我可以尊敬你,但你不會成為我的圣人。因為我不是知識分子。我眼中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學問、知識,大都是來自于書本,來自于因歷史積淀而留下來的紙頁,而我的所謂的知識,更多地來自于經驗和感悟,來自書本的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和博氏的小說有一種隔離感,但我非常尊敬這些作家的作品,我期待著有一天,我能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某種教益,而不是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了一些詞句。
梁:你平常看的小說中,對你啟發最大的是哪些?
閻:剛才我們已經說到,許多小說我都沒有看完。但是,有的小說就幾頁中或某些章節,就能給你很大的啟示,并達成某種溝通。還以日本作家德田秋聲的《縮影》為例,我喜歡的不得了,他的語言達到了極為精雕細刻而又異常自然的境界,寫一個藝妓的日常生活,一部長篇,幾乎毫無故事可談,但非常令人感動。作品中有一種巨大的憐憫心,是來自于內心深處的對人的理解與同情。這本小說我看了兩、三遍,都是一字不拉地看完的,而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第二遍就只是看某些章節了。然而,《縮影》至今我還沒有從中獲得教益,但有的一本書,可能只有幾行字就比其它整本書給你的啟發大。
梁:為什么會這樣?
閻:可能有的小說是專門讓你享受的,有的小說是專門給你教益的吧。
梁:《縮影》的什么給你帶來了享受呢?
閻:就是他的語言和巨大的同情心。
梁:其實也是那種對人類的悲憫之情,它和托爾斯泰的同情心有什么區別?
閻:我覺得相比之下,托爾斯泰還是太高高在上了,作為一個作家,他是偉大的,他對人類的同情心,和上帝相仿,但到德田秋聲這里,是一個普通人對另一個普通人的同情心,相比之下,你會覺得德田更親切,更質樸,更自然。
"民間書籍"與"社會政治小說"
梁:除了文學書籍,你平常還閱讀些什么書?
閻:我特別愛看一些地方志、史料、民間傳說等,這大約是種"民間書籍"。
梁:看這種東西沒有什么特別意義嗎?
閻:隨便看看,沒什么講究,也沒什么明確的意義。但很有意思,你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比如傳說,你會發現少數民族的民間傳說幾乎和漢族的民間傳說一模一樣。
梁:是不是漢民族剽竊少數民族的東西?
閻:那倒不一定。漢族有文字的歷史畢竟要比少數民族有文字的歷史長。但從這些大同小異的傳說中,你會發現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侵害,也會發現中國文化傳統的統一性非常強大,它有一種穿透力。
梁:其實東西方的古老神話,也都有許多相通的地方。
閻:那可能更多的是人類思維的相通之處,而不是誰同化誰的問題。前輩作家李準曾經給我講過一個奇怪的事情。說當他到美洲,在亞馬遜河上漂流的時候,發現印第安人在做一種"拆交"的游戲(把繩子綁成圓形,用手做成各種形狀,另一個人去拆解),和我們少年時做的拆交游戲一模一樣。這個游戲應該不是中國人傳過去的吧,當然也不會是從他們那邊傳過來的。它說明人類在一定的環境中會產生思維的相通性。
梁:從這個角度去講,你覺得你所看到的、聽到的那些神話、傳說即"民間書"對你的創作有沒有幫助?或者說一種什么樣的啟示?
閻:像我這樣的經歷,第一,沒有讀過大學,不可能像錢鐘書一樣去寫《圍城》那樣的小說,也不可能像博爾赫斯、喬伊斯那樣的人,去寫充滿"哲思"那樣的小說。他們對你可能有一些啟發,但是,你肯定做不了那樣的作家。第二,我天生的記憶力差,而他們,都有一種天生超常的記憶力,過目不忘。我已經四十多歲,記憶力在逐漸衰退,不可能再突然獲得一種什么天賦。像我這樣的閱歷、文化和知識結構,只能向民間的方向走,而其他別的選擇,肯定都是盲目的、不明智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梁:應該說你小說的民間性是你獲得成功的一大原因。在你所有的小說中,那種在鄉村大地生存的"根性"的東西特別深刻,具有一種極強的穿透力,這是你的同輩作家很少有的。而這種穿透力不是你有意去理解、選擇的,而是一種自然的情感選擇,你的生命和他們緊密相連、息息相通,因此,作品才有那種闊大、深情的民間性和巨大的張力。
閻:其實,小說的根非常多,土地是根,書本是根,那種冥思玄想也是根。并不像我們所說的土地才是所有作家的根。
梁:對,是這樣。這種"根性",其實是作家作為一個作家的自我意識和價值選擇,可還有許多作家缺少的正是這種自我意識和選擇。
閻:也不是沒有選擇,比如有的作家,他們要做人民與國家的代言人,這就是他們的選擇。但是,人民真正想什么,他們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或者說知道了也不愿去說。一個作家如果對"下層人"、"小人物"缺少深刻的了解,你就別天天在那里民族呀、人民呀、國家呀地哇哇亂叫。
梁:他們缺乏托爾斯泰的意識,那種對人類的大的溫和感和深沉的宗教情懷。
閻:但他們不缺乏托爾斯泰的嗓子。說真的,一個人在生活中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個作家在寫作中也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找到了,他就可能擁有自己的獨特個性,即使成不了優秀的作家,至少也可以有自己的獨特的聲音。
梁:我覺得,在中國有這樣一大批專寫"社會政治"的、沒有特性的作家,或者說,是缺少一種對自我的定位和認識。
閻:這樣的作家,也許還是當紅作家。如果追溯一下,他們的"根"是顯而易見的,這一定有脈絡可循。趙樹理這樣寫了,他畢竟還有《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三里灣》那樣一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可是,那一代作家并非只有趙樹理,還有許多作家,許多作品。歷史到了今天,文學發展到了今天,時間已經證明他們作品的"價值"了。我們不僅要從他們這些作家、作品中汲取營養,更要從中汲取教訓。這是當代作家必須認清的、明白的。但是,話又說回來,也許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有這樣的作家付出代價,犧牲他們的才華,虛擲他們的青春。也許正是有人家在前臺歌舞,你才能在后臺靜心創作。從這個角度去講,他們也應該得到尊敬與理解。
梁:就是說,不管他們這種犧牲是有意還是無意,是自覺自愿還是一種被迫,都在客觀上為另外一批人創造了條件是吧?
閻:對。
梁:但是,這和他作品的價值完全是兩碼事。
閻:我覺得,這樣的作家,重要的還是個人的問題,人格問題。像雨果,他的小說其實和社會聯系得非常緊密,為什么他就能發現那么尖銳的社會矛盾并寫出不朽之作?包括巴爾扎克也是這樣。說到底,還是一個作家是否找到"根"的問題,說俗一點,就是寫作的"出發點"和"大方向"。他們對民族并沒有什么憂思,只對自己才有考慮。
梁:其實,中國有許多作家,始終隔在一個誤區里不能拔出來,包括對政治的不自覺的認同和對日常生活的媚俗。
閻:更重要的是,這樣一批人逃脫不了現實的誘惑,如一些現實利益。反過來說,還有一個原因,中國老百姓也有一種政治情結,事實上,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政治,因此他們喜歡這樣的作品。當然應該有人去寫。比如農民,是最以生存為本的人,但他們中間,有很多都特別關心政治,關心社會,不管是大政治還是小政治,大社會還是小社會。有這樣的大眾要求,就勢必有這樣的作家存在。
梁:只是你不應該為了此一目的,而放棄或忽略了對藝術的追求和更深層的精神的要求。
閻:現在的這類作家是太容易放棄。"社會政治小說"往往成了社會政治的報告。因此,中國作家不僅僅需要政治的良知,也應該更多地考慮到藝術的良知。
梁:如果你寫這類小說你會怎么寫?
閻:其實,我也非常關注這種東西。如我早期的"瑤溝系列"等小說,還有近期的《堅硬如水》,但寫作的態度、立場,完全不一樣。
梁:是更批判一些?
閻:應該說,是更民間一些,更個人化一些。
閱讀與寫作
梁:我們再來談談你說過的寫作中的"出發點"與"大方向"--就是文學的立場。法國的普魯斯特后半生足不出戶,但卻寫出了偉大的《追憶逝水年華》,這應該是人類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對此你有什么想法?
閻:問題是,人家普魯斯特雖然人不出門,足不出戶,但他讀的書、他所處的環境,都與世界具有共通的東西。他走在大街上,是走在世界性的大街上。而我們呢?讀到的書和世界有什么關系?你所處的環境是那樣的封閉,又與世界有什么樣的關系?
梁:應該說普魯斯特所處的文學位置是一種開放性的和生成性的,而我們相當一個時期所處的環境卻是封閉的,保守的。
閻:你說,為什么三十年代的作家能寫出那么一大批好的中短篇?主要不就是因為他們處于一個開放性的環境嘛。言論自由、交流自由,而我們這一代,語言的斷裂、文化的斷裂加上思想交流的斷裂,這是很可悲的。幸虧這二十年來,什么樣的書大家都可以讀到,把我們和前幾十年與西方、與傳統割斷的東西全又續上了。文學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其實都和讀書與接受的過程有關系。雖然接受的不完整,但畢竟都知道一些了。中國當代作家的中短篇還是了不得的。
梁:那你覺得長篇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這幾年長篇其實更繁榮。
閻:長篇是繁榮,但中、短篇更成熟。現在,什么樣主義或形式的中短篇都有,有各種各樣的代表作,而長篇,正處在一個發展期。
梁:你覺得文學的下一步發展該往哪里走?如它的形式。
閻:這就是作家的困惑,老是覺得無路可走。讀的書少,可能你寫的東西別人都寫過了。就像科學試驗一樣,可能花了10億人民幣、幾十年的時間研究出一個成果來,而別人早就在十年、二十年前研究出來了。文學也是這樣,不開放,你就永遠在自己的封閉圈里打轉轉;開放了,接觸多了,你又發現,你所有的東西,以為是新的,其實又都是舊的,是別人使用過的。
梁:覺得沒路可走不是?
閻:即使是無路可走,也必須走下去。在擠壓中尋找一點新的東西。如果不開放,所有的東西就百分之百都是舊的了。
梁:這非常可笑、無奈。現在有一種感覺,包括我們這些常看小說的人也有看不下去的感覺。這也是大部分普通讀者的感受。
閻:那要看你在看什么樣的小說,愛看什么樣的小說。小說至少有三類可以劃分。一類小說是純粹供人們消遣的,如金庸、古龍、瓊瑤和我們經常在地攤上可以看到的那一種。另一類不僅是供消遣的,還是供發泄和思考用的,如社會問題小說。現在的問題是,這類小說能給人帶來發泄,而沒有帶來思考。比如成批的"反腐題材",看了很痛快,痛快之后就完了。
梁:就像"侃大山"一樣,"侃"完之后就完了,一片空虛,什么也沒有。
閻:這種小說有些像"巨能鈣",聽宣傳吃一片就可能把骨頭變成鐵,可結果呢?吃了一百盒就等于喝了一碗豆腐腦。還有一類小說,就是你找不到坐在大街上或門口看的那一類,如《紅樓夢》,如魯迅的小說,但恰恰是這樣一類,數量不多,但是卻支撐著文化的發展。它們才代表這文化的高峰。
梁:應該說你說的第三類就是精英文化。
閻:"精英文化"這個詞給人一種隔離感,既然是"精英",就與大眾無關,與我無關,我就可以不管,一般人會產生這樣的排斥心理。就這三類小說而言,你愛看什么,你就去找什么,千萬別看錯位。錯位了你就覺得小說不好看了。
梁:問題是,我們所說的第三類作品,誰看了都會說好,但大家都不看,或者說,很少有人去看,這幾乎成了一種文化的悖論。包括那些畢業幾年的大學生,在學校里面,可能都是看第三類小說的人,可是隨著生活的壓力和時間的推移,他們和文學越來越遠。感覺看這些小說太累,與"日子"、人生不協調。
閻:我們正處在一個消費時代,作家、研究者只能面對這種景況,默認這種景況。
梁:的確是這樣的。在大學里面,文學社團、詩歌會特別多,可這些人到了社會之后,就像劉震云小說《單位》里面的小林一樣,激情被慢慢地磨損掉了,最后成為一個為生活而奔波的小公務員。從書本中獲得的精神感受越來越少,最后,不僅喪失了閱讀,而且也喪失了沉思的習慣。
閻:這還與中國人的生存狀況有關。進入社會之后,物質的擠壓,自然會使你把書本拋到一邊。
梁:這是不是中國大的文化素養決定的?
閻:對,中國人讀書的傳統正面臨著現代科技文明的挑戰,作家正無奈地抵抗。也許等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就好了。我見過一些特別有錢、又非常熱愛讀書的人。他們是由讀書而向金錢奮斗,成功之后,又回到讀書。這時的讀書,便是真正的欣賞與思考。我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多,讀書的人應該會越來越多。不過,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梁:現在的小說處于某種尷尬的地位。
閻:這就需要作家去堅持。雖然,能進入徹底的精神狀態的人很少,但真正的好東西會從邊緣走向主流的。就像張愛玲。最重要的是要寫出好東西來。
梁:你對現代中國作家那些比較欣賞?
閻:比如張愛玲、沈從文和蕭紅等。
梁:魯迅呢?
閻:那當然。就說魯迅的語言,直到今天還依舊能給我們提供很多的東西。
梁:我覺得蕭紅和魯迅是從苦難中提升出來的美。
閻:這種美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有一種直接的關系。而沈從文筆下的美和我們的漢語有一種直接的關系。
梁:其實,沈并沒有寫出真正的鄉村人的精神。
閻:他更多的是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心態。就像一個人到鄉下看,發現什么都是好的。魯迅雖然也是地主,但他是一種落魄的心態,他有一種內心的痛苦。
梁:我覺得魯迅這種"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一種托爾斯泰的宗教情懷,是一種對民族的大的關愛,而沈從文更多在是展現構筑世界的愿望。
閻:這樣說罷,沈從文是生活在花園里的小說家,而魯迅是生活在廢園里的小說家。沈從文的花園是旺盛的,而魯迅的花園是頹敗的、凋謝的。
梁:但我覺得魯迅的小說是更有力量的。
閻:毫無疑問,那種廢棄是具有沖擊力的。在沈從文那里,美遠遠大于痛苦,而在魯迅那里,痛苦遠遠大于美。我也特別喜歡柔石的小說,讀柔石的小說有一種針扎的感覺。
梁:那你對周作人、廢名他們的作品怎么看?
閻:我喜歡他們的語言。
梁:你好像說過中國當代很難產生傳世之作,那么,你認為中國當代時期,對作家最大的影響或制約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閻:就長篇小說來說,文學發展到今天,我以為,沒有結構就等于沒有長篇。可是,中國的長篇小說,幾十年來根本沒有結構可談。從新文化到現在,三十年代本質上沒有長篇,中間又一直是空白。五十年代長篇好像很繁榮,回過頭來看,其實仍是一片空白,沒有價值。就說《家》、《子夜》等,這些一直是我們倍感驕傲的長篇,當你從文體上去考察它時,也會覺得它們留下了許多遺憾。有很多我們一直認為好的小說,但在文體上,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啟示和傳統。從這一點說,當代作家,必須從頭開始。如拉美的《百年孤獨》是多少年的積累,多少年才走出一個馬爾克斯。
更重要的,我們的文學正處于一個沒有好壞標準的時代,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混亂過,這種混亂,湮沒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作家,誘導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作家進入一種誤區寫作。可能有人知道這樣一個作品的好壞標準,可是作家不知道,至少說,我個人不知道怎么樣寫好,怎么樣寫不好。或者說,你知道的可能是錯的。社會、讀者、專家、學者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很少有人有真正的自我意識。這個時代,一方面真正的作家已經能夠靜心創作,另一方面,作家在寫作中總處在一種困惑和不安里。
梁:你認為這樣一個標準應該由誰來定呢?而定出來的又怎么知道是對是錯呢?
閻:肯定是得由一個大的歷史文化環境來規定。三十年代百花齊放,才造成那樣一種文學繁榮的局面。而現在,缺少的是那樣的文學環境。
梁:應該說當代作家都大量地閱讀西方的作品,并且大部分營養來自于他們,如福克納,馬爾克斯,卡夫卡、博爾赫斯等。你認為,西方作家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影響是什么?
閻:最大的好處是他們為你提供了一個坐標。告訴你文學的邊界有多遠,多寬,而它又為何層巒疊嶂,使你不致于盲目,不會以為自己天下第一。一方面,你為他們對各種文學樣式的占有而苦惱;另一方面,也會為有所超越而高興。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要想在世界文學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在比較中發展自己。這樣才能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當然,這里說的不是我,我永遠不會去做那樣的夢。
梁:是不是可以說,你們這一代正是中國白話小說或文學的成長期、積累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探索的階段,這就必然具有過渡性質和不成熟的痕跡。
閻:也可能是一個迷茫期。你無法表達你的真實思想。人最可怕的不是你直接受到什么處罰,而是一種無形的環境和你所受到的教育對你的制約性處罰,使你形成一種潛在的、無法改變的思維定勢、你的思維其實是一種"死過的思維"。這對作家寫作是非常可怕的。你所看到的都是太陽照到的地方,照不到的地方你永遠不知道,時間長了,你連到底有沒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也都忽略了,忘記了,如此,你的寫作還有什么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