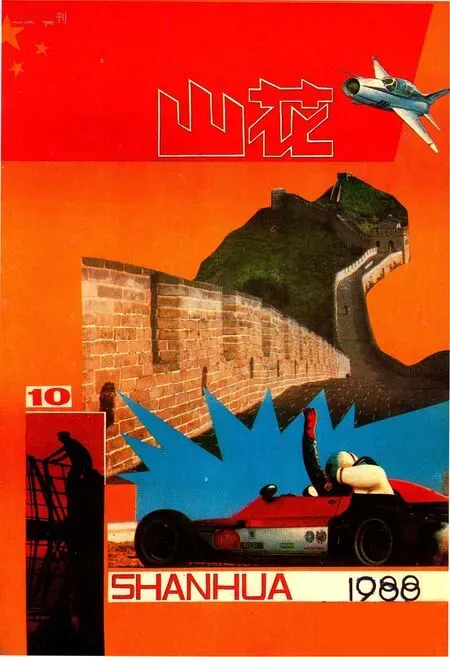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與藝術
江 梅
中國當代藝術走到今天,再來討論女性藝術,相信各方面心態都會比較平和、冷靜,也會更多地從藝術的角度來切入話題。某些認為女性藝術只是乖柔順從、小情小調、自我陶醉式的閨閣藝術,或反之認為其是雌螳螂般吞噬雄性的“動物兇猛”類的攻擊型藝術的偏見之聲,隨著國內女性藝術面貌的日趨成熟,事實上在逐漸減弱。中國當代女性藝術的發展,在經歷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萌發、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長階段后,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已形成了一種穩健的成熟態勢。無論是女性藝術的創作者還是女性藝術的推動者、研究者,對于女性藝術的思考也越來越具有一種客觀深度的、歷史性的文化全局特征。
“女性藝術”一詞盡管前面有“女性”這兩個字來修飾與定義,然而這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罷了,這個以性別標識的語詞,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與男性藝術進行區分,體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東西,如女性的生活內容、氣質和趣味等等,而其深層的目的和意義則遠非如此簡單,它不僅僅是單純地呈現和表達,哪怕有的女性藝術家如是解釋自己的創作,它也不僅僅
是為了藝術研究者便于對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與女性有關的藝術事實進行梳理,一般性地總結女藝術家的創作實踐和經驗,在其背后,實際上有著更為廣大的時空背景,隱現著深遠而特殊的有關性別的社會政治和人文歷史的內涵和價值。所以,女性藝術所體現的內容和經驗,不是單單屬于女人這一性別的人類,如果是這樣的話,女性藝術將無法超越自身,而與“男性”藝術并駕齊驅(補充:歷史上并無“男性藝術”一詞,由于女性藝術創作在有跡可尋的歷史文本中顯現的微弱,“男性藝術”通常等同于“藝術”),成為人類的藝術家庭中平等的另一半。女性藝術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與藝術的目標相一致,是要超越女性自身的局限與束縛,來為探索人性中人類精神與審美的深度與廣度而努力并作出貢獻的。美國女性藝術家貝絲·畢(BethB)說得很好:“女性主義為我面對人們時提供了一雙眼睛,可以看到他們的特質,而非性別。女性主義主要是確定我們怎樣可以超越自己,而非我們傳統的女人角色。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創作一種對待社會中人們更積極的方式。透過看待性別,你消除了偏見。女性主義擴展了我的選擇,為我們提供了探索以前男人占的世界的可能性。”
和西方女性藝術的成長伴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洶涌澎湃的女權運動不大一樣,中國當代女性藝術的成長所汲取的資源和養分有著自身特點。當西方女性為爭取平等的社會政治地位自下而上吶喊奔走之時,中國女性在中國共產黨政府自上而下頒布的政策下,一下子就輕易解決了這個問題,“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在當時深入人心,女性與男性一樣肩并肩地工作在國家需要的各個崗位。幾千年來中國女性受壓迫歧視的地位在一夜間似乎全然改變過來,然而這種改變是以抹殺女性特質為代價的,在“鐵姑娘”的形象下,女性所持有經驗與氣質遭到忽視和貶抑,中國女性在輕易獲得西方女性通過長時間艱苦斗爭換取的社會政治地位平等的同時,屬于女性自身的價值被遮蔽。女性的自我實現在時代的洪流面前顯現得那么蒼白無力,甚至不可言語。女畫家們畫著和男畫家們一樣題材的作品,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做宣傳服務,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女性藝術。中國當代藝術中女性意識的萌芽是在文革以后。→
隨著思想意識形態的解凍和人性的復蘇與回歸,有些女藝術家開始將目光投注到因性別差異而形成的女性身上所特有的情感與美,像周思聰畫的那些充滿母性或輕靈嫵媚的少數民族女性形象。而隨后發生在中國文學藝術領域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美術界人們通常稱之為“八五”新潮美術運動,不僅給了當時急于求變突破、反傳統的中國藝術家一次西方現代藝術的大洗禮,同時也讓中國的女藝術家接觸到一些有關西方女權主義思想和女性主義藝術的文獻資料,開闊了眼界,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女性藝術的萌發和成長作了重要的思想啟蒙和理論準備。雖然現在很難推舉出那個時期可以歸入女性藝術創作范疇的代表性藝術家和作品,但是詩歌界的女詩人翟永明創作于八十年代中期的長詩《女人》,以其具有人性深度的關于女性獨特生命經驗的表述,名噪一時,成為中國當代女性詩歌當仁不讓的表率。女性意識的提出,文學界可以說早于美術界。因而,改革開放以后到九十年代以前的這段時間,美術領域中嶄露頭角的女性藝術家是鳳毛麟角,具有明確女性意識的作品難覓蹤跡。中國女性從文革時期的“鐵姑娘”角色中掙脫,從幾千年形成的傳統女性角色中掙脫,歷經著艱難的轉變過程。
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過去后,經過非常短暫的沉寂,九十年代初期,中國
當代藝術有了新的發展,出現“新生代”、“玩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等藝術現象,并且有些藝術家開始走出國門,進入國際藝術舞臺,與此同時,有關西方現當代藝術的信息也更為直接便捷地傳入國內,其中系統介紹西方女權思想、女性主義藝術的理論著作、女性藝術家的傳記、畫冊等等更是豐富了眾多中國女性藝術家的視野,鼓舞了她們成為勇敢正視自身性別、挖掘自身內在潛力的獨立自主型藝
術家的信心。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女性藝術家出現并開始活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領域,在一些關注女性藝術的策劃人和批評家的推動下,各種女性藝術專題展覽、研討會等學術性活動應運而生,它們為中國當代女性藝術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女性藝術漸漸成為中國當代藝術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它不僅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關注中國的目光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藝術家也開始登上國際當代藝術的舞臺,她們通過獨特的女性視角或方式,剖析自我并審視世界,從而表明自己的態度與立場,以視覺的形式體現自己的精神、情感、智慧和美學。在此過程中,女性經驗所涉及的范疇也漸漸由起初較為私人化的空間向公共話語空間蔓延、擴展。
中國女性藝術就這樣一路走來,它那復雜的社會、政治、思想基礎,使她與西方國家的女性主義藝術相比有著自己的特殊性:一、有著西方女性主義藝術成長缺乏的現成的政治土壤——不需要自己爭取就從政府那獲得的“半邊天”權利和相應承擔與男人一樣的勞動義務,反過來看,因為權利不是通過自己爭取得來的,社會身份、政治身份明確了,而對自我女性身份的確認卻顯得模糊,女性屬性成為人們注意力的盲區;二、綿延數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中國古代封建思想仍然具有潛在的影響力,制約女性向更廣闊的天地發展;三、榜樣的力量——西方女性主義藝術與理論對中國女性藝術家的熏陶和借鑒作用。
這種復雜性,也導致敢于大膽宣傳自己是女性主義藝術家的人屬于少數,大部分的中國女藝術家不太愿意公開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藝術家,盡管她們的作品常常具有女性主義藝術的關懷,同時在私底下她們也會關注女性主義藝術,認同一些女性主義的思想。原因可能主要有這樣兩個方面:一是不愿被歸入另類,將自己孤立在主流的男性藝術之外,中國女性藝術家內心還是希望建立一個兩性平等和諧共處的局面;二是擔心“女性主義”這個詞所具有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會影響對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意義的判斷,將她們的作品狹隘化。
我曾經在一篇剖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中國女性藝術的文章中從“自我凝視”、“性與身體”、“歷史與女性身份”以及“回歸自然與詩性”這四個方面對其進行了類型化的分析。
“自我凝視”是指對“自我”形象的凝眸、注視與審察,這在女性主義藝術創作中占據了相當的成分,這個“自我”有時是抽象化、普遍性的作為某種性別角色的自我,而大多數往往是女藝術家的自畫像,因而表現的既有女藝術家內心對女性角色的假想與認知,同時又有她們對現實處境中自身方位感進行自我確認的企望,這些作品中的“她們”強烈地暗示著:我們是存在著的,不僅存在著,我們還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著,我們渴望處在與世界的平等關系之中;同時也由于這種渴求在現實中常常遭遇到困頓,“她們”又會在經意不經意間流露出孤獨、冷漠迷茫甚至無助的情緒。女性的“自我”在既成為審視與表現主體又同時成為被審視與被表現的客體的雙重凝視中獲得了自覺。喻紅、申玲、劉虹、奉家麗、劉曼文等女畫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性與身體”是指女性創作中反映出來希冀重新獲得對性與身體的主動權,表達女性對性與身體的各種感覺,諸如快樂與痛苦、幸福與幻滅、生命與死亡、愛情與欲望等等的個人體驗,藝術家常常采用感官效果強烈的表現形式,以情感宣泄的、直截了當的方式展示對自己身體的觀察和感覺,傳達在“性”的認識上女性所具有的獨特經驗,蔡錦、陳妍音、廖海英等女性藝術家表現具有強烈性器特征的作品是其代表。
“歷史與女性身份”指的是女性藝術創作中出現有關女性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女性身份如何在現實中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認同等問題的探討,韋蓉調侃傳統男性至上歷史的畫作、尹秀珍于平凡中顯示女性生活沉穩獨立的存在力量的裝置以及張新顯示女性自我價值實現與現存社會規范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的雕塑稱得上其中的佳作。
“回歸自然與詩性”是指一些女性創作在審美上、在終極關懷上,向自然與詩性的回歸。具體地反映就是,在創作材料的擇取上常常不約而同地偏向宣紙、棉線、竹子、木筷、石子、蒲扇等天然屬性的物品,在構思和經營上更多地考慮作品與自然、環境之間和諧共生關系,努力在日常中建立一種“詩意的棲居”的精神家園,在制作上,除了像秦玉芬、尹秀珍對現成品的巧妙運用外,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她們大都充滿耐心、不厭其煩地將材料按構想進行手工揉搓、粘貼、裹扎及纏繞,而完成的作品通常都是樸素而親和的,形態上往往體現出某種敏感柔韌、具女性意象又帶有尖銳性的獨特氣質,但無疑是具有美感和詩意的,具體如施慧的《巢》與《結》系列、徐虹的《喜瑪拉雅的風》與《山木》、秦玉芬的《風荷》、尹秀珍的《樹琴》、林天苗的《纏的擴散》等。
文章最后我得出結論,即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創作總體而言是私人性的、自我滿足式的,注重的是自我修煉與自我完善。她們較少參與或至少不是那么主動地投身于公共話語空間,用藝術的手段發表自己對當代國際國內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的態度和觀點。
然而,情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產生變化。
一方面,一些語言風格成熟的女性藝術家在不斷拓展自己作品的關注范圍并向深度挖掘。例如,喻紅新近創作的將自己的個人成長經歷與充滿變數與曲折的宏大國家歷史沿革相比照的寫實主義系列繪畫,奉家麗將帶著批判色彩的“粉臉”圖像從油畫布面延展至竹器、痰盂、牛仔服等現實日常生活用具上的轉換性實驗,林天苗參加2002年上海雙年展的作品這里?或那里?》(與王功新合作)中體現出來的在現實與歷史記憶之間如鬼魅般飄忽不定的“偶人”形象……。在這些作品中,女性藝術家已然將對女性自我的內在發掘與對外部世界的感受與經驗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在實現自我精神情感宣泄、滿足的同時實現了對公共經驗的表述。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新一代的女性藝術家成長起來。由于生活環境、文化背景和她們的前輩相比更為有利,她們省卻了許多關于性別、身份等問題的糾纏困擾和自我確認。從一開始,她們就能認知自己的女性特點,找到屬于自己的創作者語言和表述方式。這些新一代女性藝術家生長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成熟于一個國際化的信息時代。傳統包袱、性別壓力對她們來說非常之小。正視自己的存在,正視自己的性別,做到不必刻意強調也不必刻意回避,對她們來說非常自然。同時,她們中的一些膽子更大,敢于冒險,敢于挑戰禁區。對女性自我身體的認知和反思上,前輩的女性藝術家基本上還是借助繪畫、雕塑等媒介來體現,方式相對還是顯得間接委婉。而年輕一代女性藝術家在這方面走得更激進,像陳羚羊、倪俊、闞宣的一些作品,覆蓋在女性身體上的神秘外紗被掀除,身體還原為身體,但女性特殊的生理結構、狀況所引發的歷史政治和社會學禁忌卻在她們的作品中得到極端蔑視和嘲弄,她們自由使用自己的身體來創作,將傳統觀念中認為污穢不潔的女性事物如月經、生育等用真實或者逼真的方式展現給觀眾,撞擊觀眾的心理限度,以此來表達身為女性所遭受的肉體與精神的困擾或痛苦,展現具有普遍差異性的女性經驗。此外,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在如今日益科技化、時尚化的時代,一些年輕的女性藝術家作品中出現的面對光怪陸離、喧囂嘈雜世界所大視野產生的不安和焦灼感。大量的信息,泛濫的圖像,世界不再明確穩定,美麗的物質后面究竟隱藏著什么?象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女藝術家王一武畫面溫馨美好的觀念攝影《過家家》、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女藝術家梁碨帶著濃郁青春氣息和優美浪漫情調的錄像與攝影作品,事實上都潛在地涉及了這些問題。
另外,和前輩采用的媒介方式繪畫、雕塑、裝置、注重手工的綜合材料作品有所不同,這些年輕的女性藝術家,接觸錄像、數碼技術等高科技媒價比較多,因而她們中的不少人都非常自然地采用錄像、攝影以及行為表演等新的藝術形式。當然,從目前的狀況,還很難判斷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創作最后能走到怎樣的程度。然而她們無居無束的自由想象和大膽的實踐精神讓我們充滿期待。
回顧二十多年來中國女性藝術的發展歷程及其成果無疑是令人驕傲的,女性藝術家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束縛中突圍,在進行自我實現的同時也在勇敢地努力承擔做為一個獨立自由的藝術家的使命。個體是渺小的同時又是偉大的,當女性藝術家們那個人性的創造匯聚在一起時,也就形成了當代藝術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價值支撐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