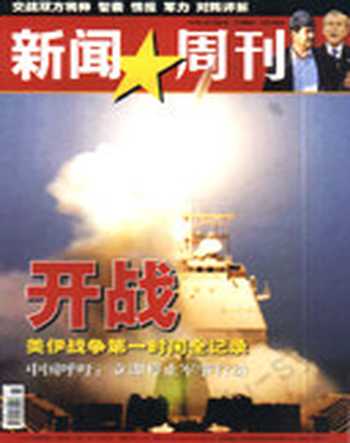我仿佛看見他們慢慢走向死亡
安 替
日期:2003-03-16 21∶14∶00
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底格里斯河毫無動靜地在眼前流過,河的另一半是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一處宮殿,據當地人說,沒有人能活著游過對岸,因為你尚未游過中線,就有不知哪里的暗槍擊中了你。
那天下午在湖畔,我看到了總統兒子烏代開著名貴的歐洲跑車在身邊飛馳過去,我才意識到,只有底格里斯河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伊拉克。
底格里斯河上的大橋都被炸過,這次戰爭也不會被放過。但是來自日本的妙山寺和尚卻要和他三個洋弟子在拉希德大橋上從3月17日開始做一周的法事,為伊拉克孩子祈福。這是秀嗎?說實話,秀到不要命的地步,我們也只能表示尊重。每次見到妙山寺和尚,他總是對我笑,我卻一直在想他未來的死亡。
還有至少70多個來自各國的人盾已經決定要和電廠、水廠、煉油廠、電信公司共存亡了,我仿佛看見他們慢慢走向死亡。
翻看地圖,這些地方都是美軍1991年首先密集轟炸的場所,1998年也不曾放過,這次被轟炸應該是“理所當然”——美國人當然會先把城市的能源、通訊、物資供應徹底切斷,然后趁天黑“好辦事”。
你知道這是多么令人難過的事情,我每天都和這些將死的人們談話,他們開心地活著,疲倦地反戰,其中有一對瑞典戀人,剛剛18歲,“和平”對于他們來說,現在是一次次游行,是類似狂歡節,他們目前還并不知道“和平”兩個字是多么沉重,甚至于要用生命去承擔。
我想我恐怕是患了朋友潘文所說的戰地記者病,也許到戰后很久,我才會為我看到的一切落淚。
當所有的大使館都準備撤離的時候,梵蒂岡大使神父先生和我同機抵達,他要為和平留到戰后,以向人們證明,此次戰爭并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戰爭,而是一場發生在兩個總統之間的戰爭。
當大多數媒體都開始離開危險之地的時候,菲律賓和韓國的電視媒體按計劃抵達,他們要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見證歷史。
在殘酷的戰爭面前,竟然有這么多不可思議的人為了宗教、理想、職業而不惜一切代價。
事實上,你發現你越了解這個城市的人民,你越希望和平能真正到來。這種和平并不只是美國不發動戰爭,而是指那種真正自由生活的和平。
我總是對我的伊拉克朋友說,如果真正有那么一天,和平完全到來,我一定要在伊拉克住很長時間,因為這里實在太可愛了。
“戰爭”與“和平”從沒有像在今天的伊拉克這樣,同時奇怪而和諧地反映出來。我的同伴說,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才會想起這里將會發生戰爭。因為所有人的臉現在都是平安的,幾乎所有的記者剛來到巴格達的時候,都徹底蒙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來這里簡直像度假!
但是,這是假象。
了解這個城市越深入,恐怖之情越濃重,今天已經恐怖到我無法在這里寫出來。巴格達此時就是臺風眼,如果戰爭打起來,這里將是新式武器的試驗廠,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可能將死亡,它不僅僅因為美軍的強硬,還因為伊軍的不顧一切。
死亡的場景已經在我眼中預演。有那么幾個小時,我甚至再不想做記者了。我更愿意做一個商人,到巴格達賣一點他們需要的東西,然后用賺到的錢和我的女友在中東游玩。
我還記得我在迪拜機場的感覺:恍惚間以為到了《第五元素》所說的外星度假場所,身旁的歐洲人、亞洲人、中東人仿佛來自各個星際帝國。司機說,如果不打了,他帶我去看看巴比倫,那里很美;我說,算了吧,現在想巴比倫實在是太奢侈了。
我發現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感情。也許因為這里的人是我看見過最好的民族,或者就是因為底格里斯河太美了。可要命的是,我和數百萬巴格達平民一起,正在底格里斯河畔等待一場結果未知的轟炸。
很多人在看網絡看電視看報紙了解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只是在看一個很有懸念的電視連續劇,越刺激越好。這無可厚非,但請在好奇的同時也稍稍想一件事:對于另一些人,這場戰爭是無法抗拒也無法挽回的生離死別。
我真的很希望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這些天我其實在做個夢,一覺醒來就是北京的早晨,雖然有沙塵暴,但卻沒有悲傷。
巴格達難掩內心恐懼
日期2003-3-20 13∶05∶46
此文寫作于戰爭爆發前一天
赤尾邦和與今村正啟,是來自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的兩名和平志愿者,他們聲稱來到巴格達是為了保衛伊拉克人民。他們和目前還在巴格達的大部分記者和和平志愿者一樣,住在相對安全的、由總統之子烏代·薩達姆·侯賽因擁有的巴勒斯坦飯店。
原來各國記者居住的拉希德飯店和曼蘇爾飯店,在戰前最后幾天逐步因為可能要被轟炸的傳聞被撤空。
今村在和中國記者聊天的時候,談起了對戰前巴格達形勢的感覺,他的說法可能是所有外國記者對巴格達的印象。他說,現在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要打仗,才不會把這里當成曼谷,否則,一點點戰爭的感覺都沒有,外國人在這里仿佛是度假。
來自各國媒體的記者都曾經四處尋找巴格達備戰的證據,但除了街上零落的沙袋、常常舉行的反戰游行之外,并沒有發現多少發現。沙袋的數量也和地點的重要性不相稱,無論是大橋、政府部門,沙袋的數量也只能供兩三個軍人打巷戰做掩護。
在薩達姆電視講話之前,商店并沒有各國媒體渲染的紛紛關閉。事實上,記者們忽視了周五和周六是伊拉克的周末,任何商店和餐館必須關閉,所有人如果想買東西必須到地攤和市場中購買。在其他日子中,商店供應還算正常,但是一些出售貴重物品的商店的確關閉了。
中國記者得到機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參觀,了解伊拉克老百姓對戰爭真實的感覺。在17日最后撤退之前,中國記者走訪了巴格達的各個地區,如醫院內部、公共浴室、清真寺、博物館、薩達姆大學、類似中關村的電子一條街、什葉族穆斯林居住區、人體盾牌所在場所、電影院、紅燈區、網吧、庫爾德人居住地區、土耳其人居住地區、使館區、書市、夜市、精品商店一條街等等,除了在政府部門遇到阻礙之外,所有的采訪都很順利,伊拉克人非常配合,也樂于被拍攝,表達也很坦誠。
他們都表現得出奇平靜,這讓帶了防化服和防彈衣到巴格達的中國記者感到自己是杞人憂天。記者了解到,在巴格達市民的心目中,即將到來的美國轟炸也就類似1991年美軍對巴格達的轟炸,呆在家里四天,然后就可以出來了。因此,一般市民都購買了大約一個星期的水、蠟燭和食物儲備。
伊拉克政府對所有巴格達市民都下達了命令,禁止戰時出街,否則格殺勿論。根據當地人解釋,這樣的規定也是擔心一旦戰爭打響、巴格達內亂,有伊拉克人會乘機打劫和報復殺人。在電視的宣傳中,政府告訴伊拉克人,美軍的侵略會造成伊拉克人民的大規模死亡,因為美國人會燒殺搶掠,甚至會使用核武器。因此,很多人家都準備了槍支,一旦有美軍闖入家宅,就準備還擊。另一方面,政府也告訴市民,美國人一定會遭到沉痛的打擊,布什政府所作所為是一次“愚蠢的侵略”。
雖然政府對新聞進行控制,所有的伊拉克媒體都在進行備戰宣傳,但巴格達市民很多也收聽西方電臺的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廣播。一位司機甚至問中國記者,美國人真的會像廣播里面說的那樣,不殘殺無辜,而且還要重建新伊拉克嗎?甚至他還告訴中國記者,美國允諾的新政府的總統就是他的遠房親戚,他說這在未來是個好消息。
與巴格達看上去的平靜相比,記者、和平志愿者、使館官員、聯合國核查人員的紛紛撤退凸現未來戰爭的恐懼。這些情緒也影響了伊拉克人,那些為外國人服務的司機,也從16日開始突然提高了服務價格,如通過公路撤往安曼的車費,從16日的200美元直線上漲,僅第二天就長到350美元,后幾天沖破1000美元。賓館服務人員要的小費開始以10美元計,而通過海關需要的賄賂也從幾個月前的幾美元到目前的幾百、幾千美元。這些直接接觸外界信息的伊拉克人開始加快最后賺錢的速度,希望戰時能保留相當充分的硬通貨。
布什48小時最后通牒下達之后,更多的記者、和平志愿者、外交官開始撤離,剩下的媒體人員都在巴勒斯坦飯店儲備了足夠的純凈水和食品,而西方媒體也希望盡早撤離新聞中心搬到巴勒斯坦飯店,但遭到了政府的拒絕。巴格達也有更多的商店關閉,晚上的車流明顯減少。學校也開始不上課,人們都希望待在家里等待美軍轟炸。
但巴格達市民卻表現寧靜。一位當地人薩卡試圖對中國記者解釋巴格達市民如此鎮靜的原因:“我們經歷了波斯人(伊朗人)的戰爭、經歷過1991年和1998年的美軍轟炸,這么多年,戰爭沒有結束,我們習慣了。除了在家里等待之外,我們還能做什么?”
伊拉克政府也嚴禁巴格達人逃難,所有的公共汽車和長途汽車都隨時被政府控制,巴格達市民只能花數百美元才能租車到外地。而對于一個月只有幾美元到幾十美元收入的普通巴格達市民,怎么可能有錢出逃呢。況且政府下令稱,所有在戰時逃亡的伊拉克人都會遭叛國罪處罰。
司機薩卡幸運地有自己的汽車,他到汽車配件市場買了新輪胎,準備在戰前一天把全家載到郊外去,等待美軍轟炸。如果情況不嚴重,就返回巴格達。但大部分普通巴格達市民只能無望地等待美國人所說的薩達姆不遵守決議的“后果”,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如果生化武器參與戰爭,那一切就無法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