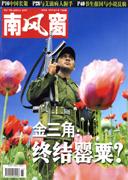日本對華投資“第三波”
劉群鋒
2003年,日本在時隔5年之后悄然取代美國,再度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國。
今年的植樹節,位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庫布齊沙漠的恩格貝沙漠開發試驗場少了一位身穿工作服,手拿鐵鍬的老人。2月27日,遠山正瑛,這位于1991年設立了日本沙漠綠化實踐協會,感化和召喚了大批日本志愿者在恩格貝種下300多萬株樹木的97歲老人平靜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從1990年開始,年過八旬的遠山正瑛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恩格貝。為表彰他對中國治沙綠化所做出的突出貢獻,2002年,遠山正瑛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中日友好使者”稱號。
歲月無情,近年來,日本有一大批從事中日友好的老人紛紛故去。可是中日關系中逝去的又豈止是這些老人而已?
3月8日,日本政府決定再次削減對華日元貸款,削減幅度為20%。經過這一次削減,對華貸款額將在1989年以來的14年中首次跌破1000億日元。在貸款接受國的名單上,中國從1999年以來一直保持的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排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之后。
日中經貿“井噴”
老一輩的日本友人和官方援助少了,可是商人和企業家來得多了,貿易和投資也開始“井噴”。
近年中日貿易增長速度驚人,2001年雙邊貿易額為877億美元,2002年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達到1019億美元。中國海關近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中日貿易額達到了1335.8億美元,日本連續第11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已經連續7年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總額占其全部進口金額的比重達到18.3%,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進口來源國。如果把港臺計算在內,2003年日本對“大中國地區”的出口總額首次超過了對美國的出口額。
不僅是雙邊貿易,按照國別計算實際利用外資的數量,2003年,日本在時隔5年之后悄然取代美國,再度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國。目前,日本在中國沿海大城市的直接投資已經超過美國、香港地區而在世界各國和地區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中居第一位。
除了直接投資創建企業,日本對華間接投資也初具規模,且受益匪淺。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各證券公司2003年第四季度財務決算報告顯示,由于買賣在中國內地和香港上市的股票,利潤大幅增長。日本設立的43個投資中國企業股票的基金,其資產在去年的一年中增值了40%至70%。近日,一本名為《投資中國股市讓我掙了1億日元》的書登上了日本暢銷書排行榜。2003年香港H股大幅上漲同日本資金大量入場不無關系。
翻開上海報紙上的人才招聘廣告,其中很多日資企業的崗位都對應聘者日語的水平提出了要求,既懂技術又懂日語的復合型人才,非常難得,尤其是應屆大學畢業生,要么是學日文專業的不懂技術,要么是懂技術不會日語。盡管日本政府決定提高2004年4月外國留學生的入學門檻,對申請者的日語能力和經費支付人的支付能力加大了審核力度,但是上海的各類日語進修學校的招生依然火爆。因為很多人學日語是為了去日企工作。
不可否認,日本的某些產品仍享有較高的聲譽,日資對中國市場的更加重視和投入,在投資目的和投資類型上的改弦更張,意味著中國民族企業在某些行業將面臨更加殘酷的競爭,對某些不成熟的行業可能沖擊更大。這一次,“日本武士”來真的了。
日資在華新動向
中日建交以來,日本先后有過三波對華投資的高潮。
1984年,中國開放14個沿海城市,拉開了以渤海灣為中心的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序幕。1985年日本接受“廣場協議”后日元急劇升值等因素掀起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第一次高潮,在1988年達到頂點。隨后,在華日資進入觀望、試探階段,新增投資集中在見效快,風險低的服務行業,以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投資為主。
1992年鄧公南巡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迎來了第二次高潮,實際投資額連續5年大幅遞增,1997年達到巔峰。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在華日資對制造業的投資比重首次超過非制造業,達到53%,以后逐年擴大,成為對華直接投資的主流。投資地區也由以往集中在長江以北沿海城市為主,逐步擴展到以珠江三角洲為主的長江以南沿海城市和少數內陸地區。在此期間,占領中國市場開始成為日企進入中國的另一個主要動機。
但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強度指數連續下降,直到2001年才發生轉折。這一年,由于美國在經歷了10年多的“新經濟”幸福時光后還是陷入了衰退,“9·11”又給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日本對美、歐的出口都是負增長,唯獨對華出口增長率高達28%。于是,日本對華投資第三波高潮開始了,200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僅占其對外總投資的2.1%,而2001年就躍為4.5%,2002年占4.9%。
和前兩波投資高潮相比,這一波出現了新特點;首先,2002年日本的財經界領袖達成共識,把中國的崛起視為日本的機遇,將日本的經濟戰略重點轉向中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2002年4月15日的博鰲亞洲論壇首屆年會上演講時表示,“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構成威脅。我不這樣認為。我相信,中國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將對日本既提出挑戰,也提供了機會。”
其次,中國在日企投資布局中的地位上升。以往中國是“生產出口基地”,因此與投資相伴的并非是最先進的技術,技術轉讓成分較低。而今高速成長的中國市場成了日企無法抗拒的誘惑。日本國際協力銀行1995年調查日資對華投資理由時,回答“市場需求將增大”的為56.7%,“勞動力便宜”的為61.9%;而2003年的數據分別是82.3%,74.9%。并且,根據日中投資促進機構的調查,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80%出現盈利。
日本企業苦心經營其在華子公司,還因為歐美跨國公司爭相在華投資設廠,日本已不是高技術的唯一擁有者。在全球化時代,如果再向中國市場銷售二流產品,無疑是自廢武功。尤其在面臨本土市場巨虧的局面下,深耕中國更是成為日企的不二選擇。有的公司干脆以中國作為推出新產品的第一站。2003年,索尼公司就把它全球首款300萬像素攝錄放一體機放到中國設計、生產和銷售。有的甚至專門針對中國市場開發產品。
受中國內需拉動,日本的對華經貿活動更加注意地區平衡,向華東地區有所傾斜,投資規模上也有較大增幅。1986-2000年間,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為134.12萬美元;而2001~2002年則為179.23萬美元,有不少大手筆。例如,2003年,日產汽車公司以約10億美元購得東風汽車有限公司50%的股份。2003年底,新日鐵簽字投入24.7億人民幣,獲得與寶鋼、阿塞勒合作年產能170萬噸的板材項目38%的股權。
在組織架構上,以前日本公司在華各項投資由于直接向其總部相關事業部負責,不免出現重復投資,經營分散的現象,不但增加了投資成本,還導致缺乏靈活性。近幾年,日本公司開始梳理在華業務,籌劃建立地區性公司總部。2003年,松下中國公司正式擔負起地域統擴協調職能,獲得投資和直銷權。在市場策略上,也入鄉隨俗,出現了通過擴大本地化生產規模,降低價格,爭取更多市場份額的跡象。例如,索尼在數碼攝像機和數碼照相機,松下在等離子電視(PDP)上都開始出招。
最后,在投資的產業、行業分布上,隨著中國履行人世承諾,明年底過渡期的結束,第三產業尤其足習企具有優勢的社會服務業成為新的投資增長點。2003年,以排名世界500強的伊藤忠商社為首,日企南下北上,大舉進入中國物流行業。
博弈:技術與政治
從東道國的立場來看,對外資企業的期望主要有:(1)出口創匯;(2)增加就業;(3)技術轉讓;(4)培養相關產業。其中,后兩項的實現與否是決定該投資在東道國經濟環境中能否長久發展和發揮積極作用的關鍵。在中國,日資企業在所有外資企業中科研實力最差,基本不進行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2000年度,美國在華企業研發費用在銷售額中所占比例為1.9%,而日本這一數據為0.2%。這和其本士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日本的研發經費占GDP之比重多年來保持在3%。
歷史上,日本經常在技術轉移方面采取控制轉移的方法,較多轉讓一些操作、維修等適用性技術,而對技術設計、新產品與設備開發等高技術的轉讓比例進行控制,并把這種控制作為保持雁行“梯次”轉移的一種戰略手段。多年來,韓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一直維持在100億美元以上,原因之一就是在關鍵技術、沒備、零部件上依賴日本。在相關產業的培養上,日本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2002年9月,日產與東風全面合作后,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其供應商在規定的時間在湖北設立子公司,否則將斷絕所有合作。于是,50多家日本供應商尾隨而到湖北設廠。東風原來的零部件廠家面臨巨大壓力。當然,這并不能抹殺日本是中國主要技術來源國的事實,1994年2月朱镕基副總理在訪日期間就曾說過,“日本對中國的技術出口貿易占中國技術進口的28%,居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對內陸地區的投資比例遠低于其他外資,這不利于縮小沿海和內陸地區的經濟差距。盡管中日經貿正如火如茶,但是中國在日本對外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并不大,2002年也只占4.9%。歐美一直并且仍是日本投資的重點所在,更不用說累積投資額。如果兩國國民關心的中日之間的其他問題得到妥善處理,可以預計兩國的經貿關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春江水暖鴨先知”,也許正因為中日間火熱的經貿關系,曾經宣揚過“中國戚脅論”,“中國崩潰淪”,“中國向日本輸出通貨緊縮”,“中國造成日本制造業空心化”的日本媒體從2003年下半年有一些輿論的變化,認為由于對中國出口的大幅增加,極大地促進了設備投資增長,使得日本經濟自1990年以來出現了首次的增長飛躍。比較權威的預測是今年3月底結算的2003年度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約為3%。曾經火力炒作“人民幣升值”的日本,一些經濟界的有識之士近來紛紛撰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人民幣升值”不僅會損害中國經濟的增長,最終也將影響到日本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