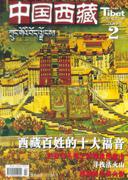馱鹽與西藏民俗文化
王德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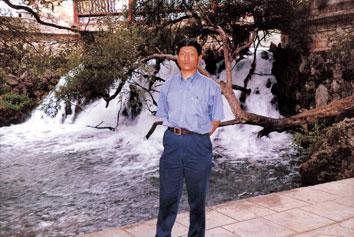
西藏是一塊風水寶地。近年來,有關西藏的圖文書紅火起來。這些書(如《藏地牛皮書》等)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充分展現了西藏的神秘、神奇之處,對許多沒有去過西藏的讀者來說,可以說是一場視覺的盛宴。而冷靜地審視這些圖書,就會發現它們擁有一個共同點,即大都是從旅游者的角度切入,只是作浮光掠影式的介紹,局限于對西藏自然風光、風土人情的描繪,往往帶有獵奇的成分,帶著故作姿態的夸張,給讀者呈現的是旁觀者眼中的西藏。而《西藏,最后的馱隊》一書則明顯地超越了這些圖書,它帶有史詩的特質,抵達了西藏文化地層的腹地,呈現出來的是本色的真實的西藏。
《西藏,最后的馱隊》的作者是著名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熱,他出身牧民,去馱過鹽,并自學藏文。發表過許多詩歌、小說、紀實作品。現為西藏文聯編輯事務部主任、西藏作協常務副主席。
《西藏,最后的馱隊》以加央西熱的親身經歷和他帶領中央電視臺紀錄片攝制組跟拍馱鹽隊為線索,以詩一般優美流暢的文筆,全面真實地介紹了西藏北部牧民歷經數月,趕著牦牛,艱苦跋涉,找鹽、采鹽、馱鹽的全過程,展現了馱鹽儀式、馱鹽用語、馱鹽歌等馱鹽文化習俗,還描繪了眾多牧民家庭及牧人的現實生活,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和重要的文化和民俗研究價值。由于用汽車拉鹽的普及,加上1998年政府對加碘鹽的推廣,具有神秘色彩的馱鹽正成為歷史。本書以豐富多彩的圖片和翔實的文字,全面真實地記錄了這即將消失的珍貴的歷史瞬間。
難能可貴的是,加央西熱對馱鹽隊的敘述完全采用第一手資料,對所寫的主要事件,例如馱鹽與鹽糧交換,大都是作者的親歷親為,對民族記憶作了珍貴的書寫。文化人類學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作者所做的努力可以說是非常出色的田野調查。作者通過親自參與馱鹽,重走馱鹽、鹽糧交換大道,走訪當事人,收集相關的民間神話傳說,記錄、整理鹽歌與婚禮歌,發掘、記錄、整理與研究鹽語等等種種方式,在進行充分調查的基礎上——用加央西熱自己的話來說,這本書是他多年“懷胎”所生的“兒子”——力求敘述的客觀性乃至科學性,同時又避免了論文的枯燥與乏味,講究紀實文學的生動形象性,講究行文的詩性之美。
《西藏,最后的馱隊》的一個突出特色是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價值。馱鹽是一種古老的勞作方式,其重要性可以說是關乎藏民族的生存延續。大約一千多年以來,藏北男人每年都要趕著牦牛去鹽湖馱鹽,一般行程幾百里甚至上千里,十分辛勞,以至作者將浸透汗水的馱運路看作是自己民族的縮影。依循古人的說法,如果一個男人一生參加九次馱鹽,就能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馱鹽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沉淀,其意義早已超過了一種勞作方式本身,而更多地被賦予了宗教式的神圣,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具有濃郁的民俗特色,負載了豐富的文化符碼。譬如,馱鹽隊拒絕女人參加,馱鹽的男人們要專門組成臨時家庭,由“爸爸”、“媽媽”、法官、煨桑師、“保布”(第一次參加馱鹽的人)等組成,各司其責。“爸爸”統管整個馱隊的事務,“媽媽”負責做飯燒茶,法官執法,煨桑師念經。馱鹽隊離開了家鄉,就失去了家神的保護,為了要朝見偉大的鹽湖母親,法官要宣布戒律,規定馱鹽人要說鹽語(一種與性有關的隱語,迥異于日常生活語言,只有馱鹽人才聽得懂),要拒絕女色,絕對不能說出“天”、“地”、“野驢”這幾個字,不能隨意與“黑屁股”(指當地人,鹽人自稱為“白屁股”)見面,不要讓乞丐、女人和狗在鹽隊營地附近留宿。如果鹽人不守戒律,就要受到懲罰。在鹽湖采鹽時,鹽人要唱許多韻味十足的采鹽歌,采完鹽要舉行隆重的祭湖儀式,由保布獻“昨母”(面牛),眾人唱《祭祀歌》,騎馬繞著經幡飄揚的祭臺轉圈,以此答謝鹽湖母親,祈請鹽湖來年再賜給珍貴的鹽巴。
加央西熱在詳細敘述跟拍馱鹽隊的經歷時,不僅插入了“文革”中自己17歲去參加生產隊組織的馱鹽隊的經歷,描寫了在當時特定政治氛圍下馱鹽所具有的革命色彩,還請馱鹽首領、老鹽人格桑旺堆回顧了自己的馱鹽生涯。作者又將筆觸深入到歷史的縱深處,敘述了鹽湖的傳說,回溯了馱鹽的由來以及馱鹽戒律、馱鹽習俗的變遷。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中,勾勒了馱鹽變化的軌跡,從而更為立體更為全面地展現馱鹽的文化內涵,揭示其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價值。
《西藏,最后的馱隊》對西藏地域文化和藏族民族性格作了準確的解讀。由于作者加央西熱是一位藏族作家,曾參與過馱鹽,被稱為“藏北第一導游”。作者的親歷加上他對西藏風俗地理的熟稔,使他能夠從更內在更本色的視角,對西藏雄闊的地理風貌進行描繪和對馱鹽文化進行詳盡的解讀,在經幡的飄揚與歌聲的繚繞中,準確地揭示西藏地域文化和藏族民族性格的精髓。

加央西熱在書中反復寫到藏民族的那種內心的澄澈、寡欲:“家里有了一個佛龕、心中有了一尊活佛、門前有了一群牛羊,心安理得,知足者常樂。”寫到牧民的可貴品格:“他們生來不畏懼高官,也不欺壓弱小”。大到對賽馬會、苯教葬禮、婚俗場面等的描繪,小到對“央袋”、鞍具、牛糞等的介紹,作者站在一個牧民的角度,如數家珍,深入淺出,其準確、深刻與精當的程度,遠非一般以旁觀者的角度介紹西藏的圖書所能比擬。
《西藏,最后的馱隊》中貫穿著十分強烈的現實精神,對藏族牧民的生存狀態作了真實的反映,洋溢著濃郁的時代氣息。作者告訴我們:在西藏,不僅有藍天、白云、雪山、喇嘛、寺廟、經幡,更為重要的是還有廣大的藏族人民,他們才是這片高原大陸的真正主人,表現他們的生存狀態才是最有意義和價值的。加央西熱在這本書的第三部分《村里的故事》里集中描寫了牧民的生存狀態,筆觸涉及到幾十位牧民,其中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點寫了五個牧民家庭的生活情景,塑造了格桑旺堆、旺青、頓加、頓珠、布瓊、雍措、秋吉、索加、日地等一些個性鮮明的牧民形象。書的核心人物是格桑旺堆,許多故事都是圍繞著他而展開。格桑旺堆既是馱鹽隊的首領,又是一個精明的商人,系當地的首富,還是一個出色的牧民,他的精明果斷、他的口若懸河的演講、他在牧民心目中的威望,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桑旺堆的兒子旺青勤儉持家而又揚棄了格桑旺堆對財產無度的追求欲望,代表了許多藏族牧民追求的理想的精神境界。頓加結婚后又離婚,獨自面對孤獨而苦澀的生活。“打狗”的戀愛方式產生了許多不利的后果……
作者在敘述牧民生活的悲歡離合時,揭示了其內在的民俗文化內涵,如藏北傳統婚禮的繁瑣程序與載歌載舞的熱鬧場面,剪羊毛時過剪毛節,唱剪毛歌。作者將筆墨重點還放在了對延續了千百年的牧民生活所發生的深刻變化的表現上。作者寫到了如下的變化:因新的運輸工具——汽車的興起,用馱隊進行馱鹽和鹽糧交換作為一種舊的勞作方式已告終結;短短的二十余年間,牧民們告別了用了幾千年的牛毛帳篷,住進了房屋,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一些牧民,如格桑旺堆,買了汽車,往返于城市與鄉村之間,成為當地有名的大富戶……書中跳動著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反映了西藏日新月異的變化。
《西藏,最后的馱隊》精心收錄了近140幅彩色圖片,許多是有關馱鹽的珍貴圖片,但更多的是展現了藏族牧民的日常生活圖景。關注牧民的眾生相,這是本書的圖與文共同的主旨。
最后,我引用加央西熱的《鹽湖》一詩中的詩句來結束本文:
多少世紀的季風在這里刮過
鹽湖的臉上總是掛著孤寂的淚水
無言地仰望重疊的山峰間盤旋的鷹
石縫里流淌的溪水凝固成無聲的瀑布
在陽光下閃耀
像獻給山神的哈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