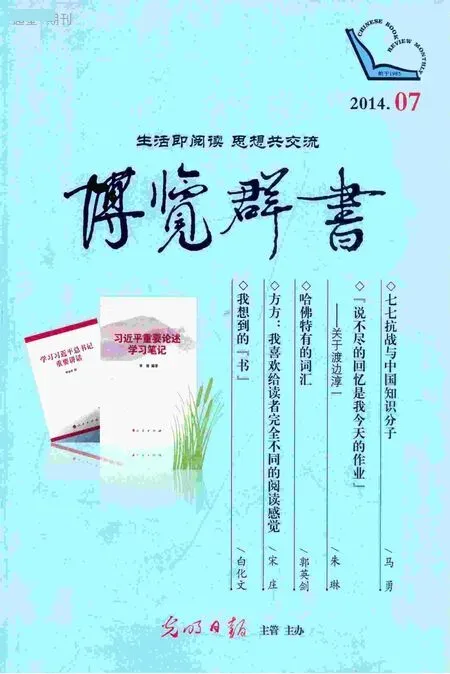當代的亞當·斯密
馮務中
1998年,也就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亞當·斯密離開人世后的第208年,一位東方人走上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獎臺。他就是印度籍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說來有趣,作為印度的第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名字來自于印度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泰戈爾。當阿馬蒂亞·森初生時,他時任泰戈爾秘書的外祖父請求泰翁為其女兒的兒子起名字,泰戈爾給孩子起名A-martya,意思是“另一個世界的”,并說“我可以看出這孩子將成為一個杰出的人”。這無疑又是諾貝爾獎歷史上的一段佳話。獲獎之時,阿馬蒂亞·森剛從美國哈佛大學退休,回到母校劍橋大學擔任著名的三一學院的院長。這無疑是哈佛大學的一大損失,但卻不能說是劍橋大學的意外收獲。因為森長期以來就是以瓊·羅賓遜夫人為首的經濟學劍橋學派的重要成員。可能在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的眼里,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森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印度國籍,也由于他的思想世界。森多才多藝,他曾在《紐約書評》上發表評論泰戈爾詩歌繪畫的精彩文章,并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一定的研究。即使在學術領域,森的地位也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所能概括的。與亞當·斯密一樣,森同時又是一個倫理學家。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中這樣寫道:“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一系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后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倫理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是森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森獲得巨大社會聲望的主要源泉。正由于茲,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索羅不無公允地稱森為“經濟學的良心”。而我更愿意將森稱為“當代的亞當·斯密”,因為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超常的激情使我們回到了永遠也說不完的亞當·斯密,因為他以“接著講”的方式在斯密的基礎上“重建”(而非“開拓”)了經濟學的倫理層面。
與森的另一本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原名為《Development As Freedom》,譯為《作為自由的發展》似乎更妥,并可與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相對應)不同,《倫理學與經濟學》寫作于森獲諾獎之前的1980年代,因而可以看做是森獲諾獎的一個學術資本。相同的是,在森的這兩本書中,亞當·斯密的影響顯而易見。特別的是,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我們發現亞當·斯密的影子幾乎無處不在。唯一不同的是,通過《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舉一反三的頁腳注釋、無所不包的參考文獻、細致詳盡的人名索引和名詞索引,我們發現森是一個現代學者而非亞當·斯密式的古典學者。但是,他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常常被人們稱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其實是一個理論通才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作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斯密教學和研究的領域涉及到了我們后來所細分而成的諸多學科,主要包括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而其中的政治學,又包括我們后來所熟知的政治經濟學。同時,政治學又與當時的倫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這可以從亞氏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和《政治學》這兩本傳世之作中看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科曾經認為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第8頁)。森的這一說法大抵是忠于歷史的。正是在斯密作為道德哲學教授和經濟學源于倫理學這兩個基本事實的啟示下,森堅定地認為經濟學與倫理學不可相互分離。
但斯密對森的啟發性并不僅限于此,斯密對森影響最大的地方恐怕在于他對人性復雜性的看法。在斯密的著作中,對人性的探索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的良師益友——同樣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休謨曾經不無深刻地指出:“所有各種科學都或多或少地與人類本性有關,而且無論其中的某幾種科學從表面看來距離人類本性有多么遙遠,它們也都仍然要通過某種途徑回到這種本性上來。甚至數學、自然哲學,也都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人們的認識范圍,并且要由他們的權力和能力來判斷。”(《人性論引論》)我們無從得知斯密是否受到休謨這種思想的直接影響,但是可以看出斯密是這種思想的積極實踐者。
斯密關于人性的理論最有影響的可能就是“經濟人”理論了。它來源于斯密《國富論》中那段膾炙人口的話語:“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我們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好處。”(《國富論》)斯密之后,西尼爾從定量方面提出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又在斯密和西尼爾的基礎上提煉出了“經濟人”假設,最后“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這個特定名詞由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帕累托引進到了經濟學中。時至今日,肇端于斯密的“經濟人”理論依然是西方社會最有解釋力的人性假設,甚至成了一種不吉自明的意識形態。但斯密關于人性的看法并不限于“經濟人”假設。在早于《國富論》的《道德情操論》中,斯密為我們描述了人性的另外三個方面。斯密認為,人其實都有同情心和正義感(合宜感),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利他主義傾向。這些其實都是人道德性的體現。斯密的這種思想后來被人發展為“道德人”理論。但即使是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也沒有忘記人具有自利性:“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道德情操論》)。斯密用作書名的“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一詞本來表示的就是作出克制自私這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為的能力。一般認為,“社會人”思想的提出者為社會學家涂爾干和管理學家梅奧,其實在早于他們的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有了“社會人”思想的雛形。斯密發揮斯多葛學派的理論說:“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人應當隨時地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道德情操論》)除此而外,斯密還發現了一種他稱之為“制度人”的人:“制度人容易自作聰明,常常對自己設想的理想管理計劃的完美性如此迷戀,以致不能容忍對這一計劃的任何一部分的最微小偏差……那就是自負地認為,自己是社會中唯一的聰明和高尚的人,其同胞公民應該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他,而不是他適應他們。”(《道德情操論》)斯密對“制度人”的描述和批判是斯密人性理論的特殊表達。從以上幾種人性思想可以看出,斯密關于人性的看法非常豐富也非常復雜的。但偉大如斯密者也擺脫不了大思想家總是被人誤解和被人分解的歷史命運。如此豐富的人性理論卻使斯密成了“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和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并進而產生了所謂“亞當·斯密問題”。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亞當·斯密問題”是一個建立在誤解基礎上的佯謬。這其實也是一個誤解。“亞當·斯密問題”有兩個義項,一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這兩部著作的人性論基礎不盡一致的問題,二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沖突問題。就義項一而言,“亞當·斯密問題”的確為一偽問題。因為不論是在《國富論》還是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都毫不含糊地認為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的,而且自利更為根本。區別僅僅在于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想用“道德情操”制約人的自利性,而在《國富論》中斯密想用“看不見的手”引導人的自利性。而就義項二而言,“亞當·斯密問題”為一真問題。其實早在十七世紀中葉,霍布斯就提出了類似問題。在與斯密同時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謨那里,也有類似問題。休謨之后的康德也提出了此類問題。到了現代,在社會學家帕森斯和哲學家哈貝馬斯那里,又出現了這個問題。如此眾多立場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思想大家不約而同地對這一問題產生興趣,這顯然不是思想史上的巧合,而是說明“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沖突問題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重大理論問題。現在也有人承認“亞當·斯密問題”的真實性,但又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其實,斯密本人的兩部著作就可以看作是對這一問題的初步解答,而森的《倫理學與經濟學》則是對斯密解答的繼續。
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森意味深長地指出:“經濟學所關注的應該是真實的人。”森在這里提出的是一個應然命題,這個應然命題所針對的是現代經濟學不假思索地將自私的“經濟人”作為經濟科學的理論起點并進行層層推演這一事實。這一命題的理論含量是相當巨大的。它至少可以說明:經濟學和倫理學一樣,它們都可以成為關于人的學問。
斯蒂里茨曾不無形象地指出二十世紀的經濟學患上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他主要指的是現代經濟學內部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脫節。其實經濟學的“精神分裂癥”更深刻地表現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邏輯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分離。在森看來,這種分離其實就是經濟學兩個根源之間的分離。森認為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根源,“一方面經濟學可以聯系到‘倫理學,另一方面經濟學又與我們或許可以稱為‘工程學的東西聯系在一起。”(第9頁)前一根源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而后一根源可以追溯至威廉·配第。后來的經濟學家們,有的更重視倫理學問題,如穆勒、馬克思和埃奇沃思;有的更重視工程學問題,如魁奈、李嘉圖、瓦爾拉斯、古諾等。森公允地承認,經濟學兩個根源的分化曾經對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問題在于,隨著現代經濟學的數學化與公理化,經濟學的倫理學維度被多數經濟學家不屑一顧或者干脆拒之門外。這正如森所批評的:“被稱為‘實驗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多樣的倫理考慮,而這些倫理考慮是能夠影響人類實際行為的。”(第13頁)顯而易見,森認為對人的行為的倫理考慮不僅是一個規范問題(正如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而且是一個實證問題(即一個在現實中的的確確發生作用的問題)。這一清醒認識顯然與森認為“經濟學應該關注真實的人”的思想有關。所謂“真實的人”,絕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強性經濟人”,當然也不是那種大公無私的“超驗道德人”。“真實的人”是一個“復雜人”。在這個“復雜人”的行為因素中,至少倫理考慮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與斯密一樣,森堅決反對那種將人僅僅看作是“理性經濟人”的觀點,他認為人類的行為動機是豐富多彩的:“這個世界的確是由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和奧賽羅等組成的。冷靜的范例充滿了我們的教科書,但是,現實世界卻更為豐富多彩。”(第17頁)理性行為或許是一個有用的假設,但它不是人類真實行為的寫照。這一點可以從“囚徒困境”和“最后通牒”這兩個著名博弈案例中得到證實。森指出,對理性自利行為假設的濫用已經嚴重地損害了經濟分析,同時也嚴重損害了經濟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森反對的是理性自利行為假設的絕對化、惟一化和濫用,而不是理性自利行為假設本身:“否認人們總是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做事,并不意味著人們總是不自私地做事,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第24頁)正如有人所辯護的那樣:“這一假設(理性行為假設——引者注)可能會導致一些錯誤,但問題在于,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第17頁)因此,問題不在于人是利己主義者還是利他主義者,因為任何利己主義者都不可能是徹底的,除非他是個利他主義者;而任何利他主義者也都不可能是徹底的,除非他是個利已主義者;也不在于人到底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因為人的這兩種類型在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的行為中都能找到一定的佐證。“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
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這就是我所謂的“阿馬蒂亞·森問題”(第25頁)。阿馬蒂亞·森問題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它既與“蘇格拉底問題”即“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是森多次提及的問題)有關,也與“亞當·斯密問題”即“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沖實問題有關。它所針對的是人類自利行為的唯一性。森本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清晰的:“人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約減的‘二元性。我們可以就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方面來看這個人,認識和關注他或她建立目標、承擔義務、實現價值等的能力;我們也可以就福利方面來看這個人,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第44頁)一言以蔽之,人的行為動機并非只是自利而是具有多元性的。森的這種回答又使我們想到了斯密。斯密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除了自利和自愛,還有同情心、自制、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而且,這些非自利的動機并不能完全被還原為自利動機。也就是說,這些非自利的動機不僅具有工具價值,而且它們本身就有內在價值。它們是人之為人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更為細致的意義上,森支持了斯密的看法。
對人的單向度理解即把人僅僅假定為“理性經濟人”使政治經濟學一淪而為經濟學,再淪而為邏輯經濟學,最終使現代經濟學變得盲目而危險。只有與倫理學再度聯姻,經濟學才有可能重新獲得良心。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沒有宗教的科學是瘸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這個比喻對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也是適用的。的確,沒有倫理學的經濟學是盲目的,沒有經濟學的倫理學是蹩腳的。倫理學沒有必要先人為主地認為自己無需其它學科的介入。森客氣地指出,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不僅對于經濟學的發展是不利的,對于倫理學的發展也是不幸的。就像經濟學應該向倫理學取經一樣,倫理學也應該向經濟學取經。“在經濟學經常使用的一些標準方法中,尤其是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學研究的。”(第15頁)有鑒于此,我們才說森不僅是為經濟學立心的人,而且極有可能是為倫理學立命的人;森不僅是經濟學的“良心”,而且極有可能成為倫理學的“大腦”。而森之所以能有此種貢獻,是因為他對人及人性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有著深入而不凡的認識。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說森是當代的亞當·斯密。正如亞當·斯密是英國的也是世界的一樣,阿馬蒂亞·森是印度的也是世界的,當然也是中國的。在中國學界為“經濟學要不要講道德”、“倫理學要不要科學化”諸如此類的問題吵得不亦樂乎的今天,在當代中國患得患失于效率與平等、發展與代價、經濟與道德、自由與公正之間的情況下,讀讀阿馬蒂亞·森的這本書,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