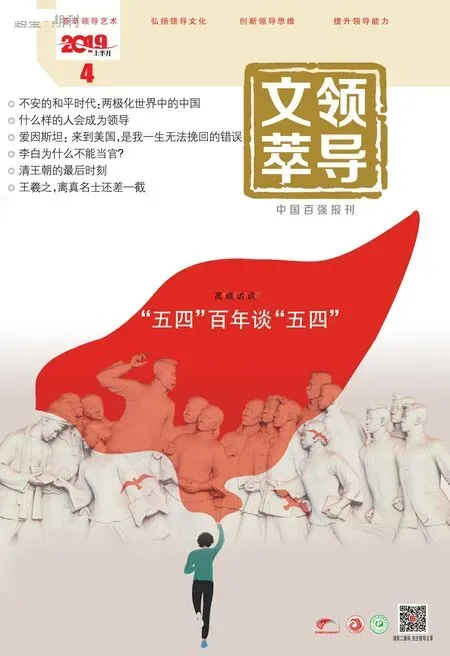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全球治理”挑戰國家主權
楊海坤
過去的幾年里,我們已經領略過一系列超越民族國家地理疆域的全球性難題。無論是SARS,還是地球環境污染、全球氣候惡化、跨國恐怖犯罪、跨國毒品交易,這些在各國以“國內問題”面貌呈現的難題,都遠非單個國家的力量所能解決,甚至是眾多國家聯合起來也都難以徹底解決的,而需要國家以及非國家的、公共的和私人的諸多全球性力量共同參與解決。顯然,傳統的倚靠單個政府進行統制的管理模式已經不合時宜。于是,“全球治理”概念應運而生,傳統的國家主權不可讓渡的原則遇到了挑戰。
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凡主權國家就可以為所欲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主權國家不僅要遵循公認的國際交往準則,還要對更多的“世界性法律”予以普遍認同和遵守。
毫無疑問,全球化已經對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構成了現實挑戰。過去,我們一般認為,主權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獨立自主地處理其內外事務的最高權力,它體現為對內的最高權和對外的獨立權。傳統的主權觀念認為,主權不僅是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而且還是絕對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團體凌駕于主權之上,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動搖主權的絕對權威性。到了20世紀,這種絕對主權論開始發生變化,相對主權論逐漸盛行。英國國際法學家勞特派特就曾說:“國際法的進步、國際和平的維持,以及隨之而來的獨立民族國家的維護,從長遠來看,是以各國交出一部分主權為條件的,這樣才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國際立法,并在必然之限范圍內實現具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法庭而確立的法治。”
事實上,主權概念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家主權的范圍已從政治擴展到經濟、文化乃至環境,從陸地擴展到海洋甚至外層空間。一種新的“國家主權讓渡論”開始流行,這一理論認為,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國際間的合作不斷深入,國際組織的管轄深度和廣度都在發生變化。
有學者指出,國家讓渡部分主權,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通過相互讓渡而得到某種協調;還有的學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在維護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上產生的國家主權讓渡現象日益增多,如加入區域經濟集團的主權國家讓渡部分經濟主權給集團的統一機構,以維護集團的有效運轉;同時,集團成員之間為得到更大的經濟利益,互相出租本國的領土、領海、領空的現象已經很普遍,這正是部分國家政治主權的讓渡。國家主權讓渡論與國家主權共享論有著密切的聯系,國家主權共享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面臨著許多全球性問題,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毒品問題、恐怖問題、金融危機等,這些跨國問題的出現,要求加強國際組織的作用,從而實現國家主權的部分共享。
當然,國家主權讓渡只能是經濟讓渡,是國家在處理涉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環境治理、國際犯罪等方面全球性問題上日顯無力,在此背景下帶來國家向國際經濟組織轉讓部分主權的必然。這種“讓渡”并非基于對主權的否定和弱化,相反,這正是國家處理其主權能力的體現,是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選擇,從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更好地維護和獲取國家的根本利益。就國際社會整體而言,適當地讓渡一部分主權,恰恰是一國權利的延伸,這種讓渡是建立在各國平等基礎上的,它是各個民族國家之間共同的、平等的讓渡,讓渡的真正目的在于共同享有。
可見,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眾多調整“世界性問題”的規則,是在各主權國家平等、自愿地讓渡部分主權的基礎上形成的,根據約定,各國又都平等、自愿地接受這些規則的約束,從而使國際秩序的維護得以建立在平等協商而非實力較量之上。從全國人大近年來批準簽署的有關國際公約,我們發現,滲透在其中的是契約所蘊涵的平等、合作精神。
我們以為,契約所蘊涵的平等、自由、誠信和責任理念,是“全球治理”的原則,是國際社會長治久安的憑借。如果說,全球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以全球性公共事務為中心的復合治理結構建立的過程,那么,它也是一個契約精神融入主權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和開展有效合作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