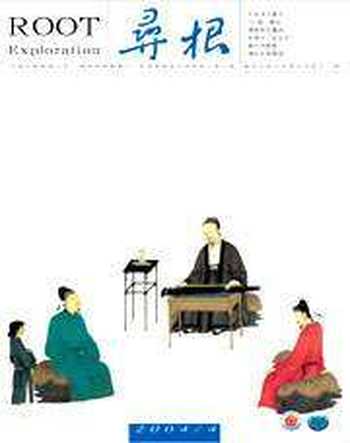墨家科學思想興衰的啟示
邢兆良
梁啟超先生曾在其《〈墨經校釋〉自序》中說:“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墨經》而已。”這個斷語,在近代科學文化日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物質、精神力量,而中國傳統文化日顯其遲滯、僵化、衰落、惰性的社會背景下,不無扼腕感嘆之意,然而把墨家科學思想興衰的歷史結合近代中國走出中世紀的里程來看,對當代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也不無啟示。
墨家是一個學者和工匠相結合的學派。墨家科學思想與近代科學精神之遙遙相符,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科學發展的早期,科學與宗教相分離的關鍵一步就是將自然的萬事萬物作為科學認識的獨立對象,既摒棄六合之外的神格的干涉,也沒有自然萬物與社會人事之間牽強附會的關聯。對自然物、象存在、變化的認識方向的確定是科學認識發生的起點,也決定了科學發展的基本方向。墨家科學思想對科學認識對象的確立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自然物、象與社會人事相分離,二是試圖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認識自然萬物的存在和變化。
孔子對自然事物亦有相當細致的觀察,但他是將自然物、象作為“觀物論喻”的“取辯之物”來論證社會的政治、倫理原則。自然物、象并不是孔子認識的獨立對象。墨家堅持從物體本身的結構來說明自然事物的存在、變化,提出了“端—體—兼”的結構層次觀念。這一思想和畢達哥拉斯數形合一的數本源說、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說在詮釋自然萬物存在的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這使得對自然物、象的認識,可以從它們本身存在的結構上一層層分析下去,而且這種分析是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性基礎上,使科學認識活動能沿著客觀、實證、分析的方向深入下去。
墨家又進一步從時空與物體運動相關聯的角度,考察、說明自然萬物的存在方式。墨家以“時空元”為基礎的宇宙結構觀和道家以“道氣”為基礎的宇宙非結構觀的區別,是前者強調萬物存在量與質的規定性,后者著眼于籠統的過程變化。作為科學理論思維的出發點,這種區別使科學活動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前者有利于以科技實踐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后者則易使理論思維停留在對表象的直覺思辨上,流于玄思冥想的神秘主義。
其二,墨家在科學活動中強調重經驗的實證精神、重邏輯分析的理性態度和重實用的科技價值觀。墨家科學思想的這一特征使墨家科學認識的發展與科學實踐密切相連,從而使墨家的科學理論認識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可檢驗性和可證偽性,不致蛻變成為一種僵化的形式框架,如陰陽五行。墨家科學思想所要求的概念的明確性、邏輯的一致性、結論的可證偽性、科學認識與技術實踐的緊密聯系性,正是近現代科學發展的基礎,也正是中國傳統科學所最缺乏而最應向之發展的方向。
墨家是能和儒學相抗衡的先秦顯學。墨家科學思想是在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社會環境中興起、發展的,至秦驟衰,幾成絕學,在以后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曾得到兩次不同程度的復興。
魏晉時期,兩漢經學陷入讖緯神學,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動亂、使儒學獨尊的思想專制瀕于解體,社會思想又一次活躍起來,墨家科學思想也得到了一次復興的機會。張湛、司馬彪都曾引《墨經》為《莊子》、《列子》作注,將《墨經》中的科學認識深入下去。魏晉時期的科學家魯勝“興微繼絕”,為“亡絕五百年”的《墨經》作注,第一次引說就經,將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單獨成書,形成了經說體例。這使得墨家的科學成果得以匯集,使墨家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科學方法、技術應用得以構成一個科學體系。魏晉時期的數學家劉徽在墨家科學思想的直接影響下,用《墨經》中的一些成果對《九章算術》重新作注。劉徽的《九章算術注》對一些重要的數學概念給出了嚴格的定義,并由此對《九章算術》中的公式和命題作出了合乎形式邏輯的推理、證明,從而構成了具有邏輯證明、推理結構的數學理論。這是對《九章算術》以數值計算為中心的非邏輯結構的數學體系的重大突破。
墨學的第二次復興是在清末民初。當時,外侵加劇,民族危機深重,封建專制王朝瀕于崩潰。這一現實促使當時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奮發圖強、變革救國的社會環境。“中體西用”便成為容易被接受的社會思潮。1896年6月,光緒帝詔定國是,將“中體西用”思想作為維新變法的政治準則宣示天下:“中外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人,齊宜發憤為雄,以圣賢之學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學之切時乎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之才。”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一批學者紛紛從《墨經》中尋求抵御近代科學文化的武器。俞樾在為孫詒讓的《墨子閑詁》作序時指出:“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倘是以安內而攘外乎?”這種看法道出了當時墨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近代中國治墨學者眾多,服膺墨子者盛極一時。他們從墨學中主要汲取的是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強烈的功利主義觀念,與近代科學本質上相類似的科學思想。當時,以儒道佛為主體的統治思想也成了社會懷疑、批判的對象。《墨經》中重實證、重分析、重邏輯的科學思想和當時傳入的近代科學文化可相互參證,從而能成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這也是墨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
墨家科學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只有兩次短暫的程度不一的復蘇。即使是在墨學作為顯學的戰國時期,墨學也是以其社會政治學說的團體組織形式為世矚目,而墨家以手工業實踐為基礎、結合在名辯思潮中發展起來的科學思想卻受到了社會的忽視。先秦諸子,除了公孫龍之外,應《墨經》者絕少。先秦諸子對墨家的評說也大都只言及其社會政治思想,而不談其科學活動。
墨家科學思想興衰的歷史對我們思考當前科教興國戰略的有效實施也是很有啟迪的。
其一,墨家科學思想的興衰與社會政治、思想環境的寬松度、自由度密切相關。科學是一種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實踐與認識活動,它強調實證,崇尚理性,倡導質疑和批判。因此,科學的健康發展需要一種百家爭鳴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氛圍。各種科學觀點、科學思想的爭鳴是以同行評議為基礎的。科學上的不同意見的爭鳴首先要以實證為基礎,同時,要有容忍異端的寬容精神。科學提倡創新,但是科學的評價是滯后的,切忌以政治權勢為支撐,利用行政命令和新聞媒介炒作等非科學手段來處理科學上的不同學派、不同觀點,壓制討論和爭鳴,用政治、行政手段支持一派、打擊一派。如果那樣,社會環境必然歸于萬馬齊喑的思想專制和沉悶狀態。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從制度上和程序上保證做到真正的百家爭鳴,行政權力和媒體應退出科學評價體系,要能在法權層面上保證容忍學術上的導端,保護少數人的意見。如何形成百家爭鳴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氛圍,這不僅僅是一個認識、觀念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實踐操作程序,即如何在法權層面上保證在科學爭鳴過程中不同觀點表達的平臺和權利,特別是如何保證少數派充分表達觀點的平臺和權利。只有這樣,科學思想才會活躍,科學人才才會輩出,科學決策才會正確,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才能有效地實施。
其二,墨家是一個學者與工匠相結合的學派,他們的科學活動是與當時的社會需求、實踐密切相關,這是墨家科學思想和科學成果能達到當時社會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在魏晉和晚清時期,墨家科學思想得到兩次程度不同的復興也顯示了這一特點。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科學創新和科學發展,一方面必須審視世界科學發展的總趨勢,另一方面又必須對本國、本地區的現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判斷。因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現實的各種條件(經濟結構、生產水平、資源,等等)決定了它對科學技術有什么樣的需求,又能提供什么樣的平臺和物質條件,科學技術轉化為具體物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是否健全、有效……等等。這些現實的社會條件往往決定了科技發展戰略的結構和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決策原則體現了科技發展戰略必須和國家、地區相結合,和現實相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發生、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所決定的。社會的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論斷對我國有效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仍具有現實和迫切的指導意義。
在當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重溫墨家科學思想及其興衰的歷史,應是不無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