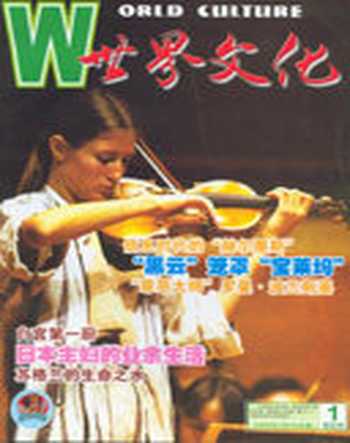不同國度的兩個女性
甄 蕾
本文要評說的不同國度的兩個女性:一個是美國浪漫主義作家納撒尼索·霍桑(1804-1864)在他的《紅字》中塑造的女主角海斯特·白蘭。一個是俄國現實主義作家伊凡·謝爾蓋維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他的《前夜》中頌揚的女主人公葉琳娜。前者是19世紀50年代生活在美國大陸上的英國貧寒移民,后者是19世紀60年代俄國土生土長的貴族小姐。地域相異出身不同,然而她們在爭取人類自由、捍衛人格的尊嚴、開拓婚姻自主的征程中,都以極致之力,顯示著自己的韌柔和剛毅。
一種感情,一旦負載上了思想和理念,就會變得更加剛烈,勇猛,一往無前。霍桑筆下的海斯特·白蘭,早先是一純靜村姑,當她意識到自己的自由選擇符合自己的理想,而這種理想又需要自己的力量來維護的時候,就變得異常的果敢和執著。她是一個“身材修長,容姿完整優美到堂皇程度”的女子。命運卻驅使她嫁給了身體畸形、虛偽冷酷的術士齊靈窩斯。白蘭沒有順從命運的這種安排。她秉承自己的意愿,與青年牧師丁梅斯代爾相愛。為了捍衛自己選擇的愛,她不求助于可能的現實的慰藉,不屈服于世俗的理性的威逼,一人獨攬通奸罪名,以驚人的勇氣忍受著世人的責罵。為了捍衛個性的自由和人格的尊嚴,她離群索居,清貧度日。她深知自己要走的這條路,坎坷曲折,艱辛無邊,但她咬緊牙關硬是堅持下去。白蘭不投靠歸來的“可接近”的齊靈窩斯,也不離開“不能接近”的情人丁梅斯代爾。她的愛,不是感情用事,不是心血來潮。她的愛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自主自定的,是堅定有力的。即使在丁梅斯代爾死去,他們的女兒珠兒已經成人定居他鄉,白蘭依然回到了她與之相知、相戀、相愛的斷魂之處,堅強地去生活。她所愛的丁梅斯代爾曾感嘆道:“女性的真心是有著驚人的力量!”不錯,白蘭的真心,鑄就了她的鋼鐵意志。她不回避身上的標志,她以她那獨有的心靈之火,點燃了胸前那象征著恥辱的A字,焚燒著她前進路上的枯枝敗葉,她在這條路上,一步一個血印地迎風前進,煎熬著自己,溫暖著別人。
霍桑用一種漸進的手法,使白蘭一步一步從無知到有知,從懦弱到堅強,慢慢地站立在讀者面前。而屠格涅夫則是把葉琳娜放在一個特殊的空間環境,通過葉琳娜對周圍的感觸、以折射的手法來升華她的品格。葉琳娜生存的小環境緊連著時代的大環境。葉琳娜的愛就是時代的愛,葉琳娜的恨就是時代的恨,葉琳娜的愿望就是時代的愿望。她痛恨封建宗法,她厭惡家長專制。少年時代,父母的不睦,使她形成了獨立獨行的個性。她的乞丐朋友小卡佳的死給她植下了一顆對窮人的憐憫心。“貧窮的、饑餓的人,害病的人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惱”。到了20歲,隨著意識的成熟,她期待著“一個能夠了解她、能夠給她的神圣感情以回聲,幫助她,教她應該怎樣做的靈魂”。可是,闖入她青春芳草園的全是一群庸俗之輩。在她看來,蘇賓嬌生慣養,懶惰窒息了才能,悔恨引起自鄙,自鄙又反轉成傲慢,能說大話不能做大事,總之是“沒有什么持久的可靠的東西”。伯爾森涅夫有些學問,但目光短淺,怯懦不前。葉琳娜向往的“是一個既有既定目標,百折不回,又能帶動別人一道去奮斗的人。”于是,她愛上了保加利亞貧苦的平民大學生英沙洛夫。父母、家人以及她所處的那個營壘的人堅決反對這門不相配的婚姻。然而世人的不可思議,正說明了葉琳娜的獨到和高瞻遠矚。她不顧封建道德觀念和家規家法的阻梗,只身一人冒風披雪奔向英沙洛夫的下榻處。聽聽他們最后的那次錚錚有聲的對話吧—英沙洛夫:“那么,你會隨著我,到任何地方?”葉琳娜:“任何地方,天邊,地極!你到那里,我葉琳娜到哪里。”……英沙洛夫:“你知道我已經獻身給那艱苦的、不望感激的事業,我……,我們不僅要經歷危險,也許還要忍受剝奪,屈辱?”葉琳娜:“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愛你!”
如果說海斯特·白蘭,在捍衛自己的摯愛中,顯示出來的是那種女性特有的外柔內剛的柔韌之力的話。那么葉琳娜,當她知道了她所愛的英沙洛夫是在從事一樁為社會鏟除邪惡的偉業的時候,當她明白了她所愛的是一名“獻身艱苦事業而不望感激”的人時候。她的愛,就變成了大洋中矗立于海面之上的一尊巖石,根底深遠,任憑風浪萬千,決不移動半分;就會變成狂風烈火,燃燒著心內身外所有敢于阻擋她追求真情摯愛的藩籬。她主動向自己追求的人表明心愿。為了真情摯愛,她秘密和英沙潔夫結婚;為了真情摯愛,她寧可失去巨額的財產繼承權、也要與一貧如洗的英沙洛夫去異國他鄉。即使后來英沙洛夫不幸死去、她的母親寫信讓她回家時,她毅然選擇留在丈夫的祖國繼續丈夫的遺業。
從古到今有多少人,一輩子都是在欺騙著自己,欺騙著別人:愛著自己不愛的人,聽著自己不愿意聽的話,干著自己不愿意干的事。百年前的海斯特·白蘭之所以被一代一代的頌揚,其主要原因是她作了另一種人。她不騙自己也不騙別人,她愛自己想愛的人,她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她開始是一個受夫權、教權、政權壓迫下的女子。殘酷的境遇使她看清了社會的真象。她用自己的直覺觀察、鑒別著周圍的一切。她忠于自己的感覺,保持自己的本真。當她在與齊靈窩斯的不和諧的婚姻中感覺不到真情的時候。她不愿裝假,不愿自欺欺人;她不玩逢場作戲,她不要同床異夢;她痛恨口是心非的生活,她厭惡沒有真愛的愛情。她認為在干枯了愛的婚姻泥沼里跋涉是對神圣愛情的褻瀆。因而她背叛,她抗爭。她用自己的良知來量度自己的行為,是罪是過她不管。她敢愛,敢恨,敢肯定“自我欲求”。她不甘心站在此岸翹望彼岸的自由,她情愿淌進那其難的征程,向著自由的彼岸進擊。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那些看著她行進的人的精神和思想,都被清教教規的枷鎖扭曲的變了形。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她在苦海掙扎卻無動于衷,她忍受著這無情的、冷酷的折磨。然而,她愛丁梅斯代爾,她恨齊靈窩斯———這是她精神的核心,也是她生活的起點和終點。為此,她自覺地進行了情感洗滌和靈魂鑄煉的痛苦磨礪,她繞過了清教徒的“懺悔爐”,直奔人生的自由之巔。她堅信自尊是維護人格的唯一武器,而人格的尊嚴使她居高臨下、無所畏懼。白蘭以自己獨有的目光,明辯著正與邪。她在為自己,也為他人清掃著往前走的路,她終于“成為一個自由人”。她的獨立的思想越來越成熟,她的自主的行動越來越明確。
有時候,人生的目標沒有達到、歷史的預想沒有實現,并不全是因為目標的不對和預想的錯誤,在很多事情上,是因追求者的韌毅之力不支所致。以往在文藝作品和在現實生活中被肯定下來的英雄,往往是以獻身捐軀之多。其實在現實中,一個人在追求一種目標而在承受那種瞬間性的痛苦時,往往是來不及體味痛苦的劇烈程度的;反倒是過后、天長日久持續延綿折磨,才是最能使人撕心裂肺的。我們通過《紅字》第23章“紅字的顯露”,可以看到一股長久的隱埋在火山底下的痛苦,是怎么樣變成了悔愛交織的滾燙炙人的巖漿,通過牧師的口噴發出來。
我們可以說,海斯特·白蘭是女性自由解放道路上的一節枕木,她默默地臥在那兒,用自己的胸膛撐起那冰涼的鐵軌,使道路一節一節的向前延伸;那么對于臥在白蘭前面的葉琳娜,我們應該說,她不僅是枕木,她還是一個指引歷史列車行進的路標。她不光為爭取女性的權利付出了艱辛,而且為女性解放乃至為人類的解放做出了貢獻。葉琳娜的年代,是俄羅斯大地風云激蕩的年代。十九世紀中葉,國家動蕩不寧,農民起義劇增,社會氣氛緊張,危機一觸即發。俄國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農權制度岌岌可危,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各派力量在相互碰撞中。貴族的革命性逐漸消失,革命的主動權逐步轉移到平民知識分子手中。美妙的向往,空洞的理論,已無法制約時局,無法導向歷史的進展。時代需要勇于行動的新人形象,而屠格涅夫在這關鍵的時刻,推出了葉琳娜與英沙洛夫作為新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