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派員駐藏到直接管理
索文清 雍繼榮

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
1720年10月,清軍驅逐準噶爾部出西藏后,在平逆將軍延信的主持下,著手進行西藏政權的體制改革。清朝決定排除蒙古諸部長期對西藏的影響,轉而啟用西藏地方上層人物執政,通過他們推行中央對西藏的施政方針。1721年2月,清朝把平準(噶爾)戰爭中立有戰功的藏族官員康濟鼐、阿爾布巴封為貝子,拉藏汗統治時期曾任孜本的隆布鼐封為輔國公,授命他們三人為噶倫,共同掌管西藏事務。到了1723年,清朝又把康濟鼐的主要助手頗羅鼐和七世達賴喇嘛的強佐扎爾鼐也升任噶倫,兼管藏區事務。清朝這次對西藏政權體制的重大改變,表明今后不再承認和碩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王位繼承,由此引發了蒙古貴族的一些人不滿,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駐守青海的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
羅卜藏丹津,固始汗之孫,襲封親王爵位,權勢顯赫,曾因護送七世達賴進藏坐床,自恃有功,早懷有“獨占西藏,遙控青海”的野心。這次清朝在西藏推行噶倫聯合掌政制度,打破了他想在西藏恢復和碩特汗王統治的迷夢,尤其清朝在獎賞平準戰爭中有功的青海蒙古諸部首領時,晉封了察罕丹津為和碩親王,額爾德尼厄爾克托克托奈為郡王,唯獨對他只賜賞銀,未予加封,這使他十分惱怒和怨恨,蓄意要與大清分庭抗禮。
1723年5月,羅卜藏丹津從拉薩返回青海,便暗地勾結新疆準噶爾部的策妄阿喇布坦,煽動當地部分寺院僧眾,公開發動了叛亂。清朝聞訊馬上派出川陜總督年羹堯、四川提督岳鐘琪領大軍進剿。雙方經過激烈交戰,羅卜藏丹津大敗,率殘部西逃。清朝為防止叛亂向西藏蔓延和羅卜藏丹津本人竄入藏地,當年10月,又派四川松潘鎮總兵周瑛統領千余兵馬馳往西藏。周瑛以45天的急行軍趕赴拉薩,會同此前被清廷派往西藏辦事的內閣學士鄂賴與眾噶倫一道,整頓西藏兵馬,合力共同御敵。
在這次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過程中,西藏官員和僧俗百姓始終與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眾噶倫聽候清朝官員調遣,積極參戰。隆布鼐曾被派往哈喇烏蘇(藏北那曲)阻截叛軍;頗羅鼐開赴青海玉樹一帶,招撫當地上層,接著領兵攻下了玉樹與康區北部;康濟鼐領兵追擊向西北逃竄的叛軍殘部。整個軍事行動,噶倫們都在忠實執行命令,奮勇殺敵,配合清軍有效地阻止了亂事的蔓延,最終迫使羅卜藏丹津不得不落荒西逃,去投奔策妄阿喇布坦。
頗羅鼐執政,設置駐藏大臣
羅卜藏丹津叛亂的迅速平定,說明清朝的平叛行動深得人心,清朝拋開蒙古汗王推行以藏族官員治藏的政策在當地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清軍與藏軍聯合平叛,換來了西藏社會的暫時安定,僧俗百姓有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清政府對西藏政局的穩定并未放心,從平逆將軍延信率部離開拉薩之日起,清政府即不間斷地派員進藏,或統領軍務,或協助監督地方辦事。派遣的官員先后有喀爾喀蒙古王公策旺諾爾布、內閣學士鄂賴、副都統宗室鄂齊和大學士班第等,這些官員們奉旨進藏,都負有安輯地方、輔佐新政權的使命,特別對噶倫內部的團結、個人權限以及他們的政治動向都十分注意。
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清廷劃定內地轄界,將藏東洛隆宗賞給七世達賴喇嘛,特遣副都統鄂齊、學士班第進藏辦理。雍正帝明確表示,今后西藏事務由康濟鼐總理,阿爾布巴協理,特“頒給敕諭,曉諭唐古特人等,盡令遵奉二人約束,庶免擾亂之患”①,但是鄂齊到藏后發現,掌權的五位噶倫這時已形成兩個派系,后藏出身的康濟鼐、頗羅鼐為一派;前藏貴族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為另一派,他們分別代表著前后藏不同地域貴族農奴主階層的利益,彼此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鄂齊向雍正帝報告,康濟鼐辦事老實,但恃功傲慢,為眾所恨;阿爾布巴賦性陰險,行動詭譎,不聽康濟鼐指揮。他與隆布鼐、扎爾鼐以及七世達賴的父親索諾木達爾扎結成一黨,玩弄權術,興風作浪,還不時挑唆噶倫與達賴之間的關系。所以鄂齊建議,應將行止妄亂的隆布鼐、扎爾鼐兩噶倫解職,“則阿爾布巴無人協助,自然勢孤,無作亂之人矣”。雍正帝決定采納鄂齊的建議,于雍正五年(1727)二月下旨,“著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喇差往達賴喇嘛處”辦事。這是清朝在西藏直接派遣常駐官員辦事的開始。
就在兩位大臣進藏途中,西藏發生了變亂。阿爾布巴搶先發難,陰謀謀殺了首席噶倫康濟鼐及其家屬,接著派兵趕往后藏追殺頗羅鼐。頗羅鼐事發后一面火速將康濟鼐被殺情形上報給清廷,一面組織集結后藏和阿里地區武裝,向撲來的阿爾布巴軍隊應戰。一場由西藏統治者內部挑起的戰爭——歷史上稱為“衛藏戰爭”,就此爆發。
衛藏戰爭爆發后,僧格、馬喇來到拉薩,這時圣城已完全控制在阿爾布巴手中,但并未阻止和妨礙兩位大臣前往布達拉見七世達賴喇嘛,他們的安全也未受到威脅。交戰雙方都向清廷奏報事變經過,相互攻訐,以求清廷支持。最初,清廷也把康濟鼐被殺、阿爾布巴發難視為噶倫內部“自相殘害之小事,不須用兵”,但開戰以后,清廷卻感到了時局嚴重,愿意看到頗羅鼐一方取勝,并按頗羅鼐“剿滅逆魁,以安西藏”的請求,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派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帶兵進藏“料理藏內軍機”,實際是保護兩位大臣在藏的安全,鎮撫地方,樹立中央權威。
衛藏雙方經過近一年的內戰,最后頗羅鼐以強大的后藏兵力分兩路夾擊,打敗了阿爾布巴的軍隊,是年七月,攻入拉薩,阿爾布巴等三噶倫被擒獲。九月,當查郎阿、邁祿率大軍抵達拉薩時,頗羅鼐已穩住政局,并以擒逆有功,“乞奏皇上,加恩賞賜”。查郎阿從軍需錢糧內支撥三萬兩銀賞給頗羅鼐,以示清廷的支持。隨后,會同僧格、馬喇和頗羅鼐本人,對阿爾布巴等進行了為期數天的審訊,最后定他們三人為“叛逆大罪”,處以極刑。凡協助阿爾布巴作亂的喇嘛人眾也都分別受到懲戒。至此,衛藏雙方內戰告終。
衛藏戰爭平息后,清廷對西藏政權進行了新的調整,承認頗羅鼐的統治地位,賜給他“貝子”銜,令他總管全藏政務。與此同時,為了加強對西藏的直接管理,在拉薩正式設立駐藏辦事大臣衙門。僧格、馬喇被任命為第一任駐藏大臣,受命中央,長駐該地。初起二大臣職銜未分正副,職掌也不明確,直至乾隆年間才漸有區分,規定任期三年。駐藏大臣是清朝中央的代表,守衛邊圉,監督管理藏務,并派有駐軍,行使國家主權管轄,這是清政府在西藏統治管理制度上的重大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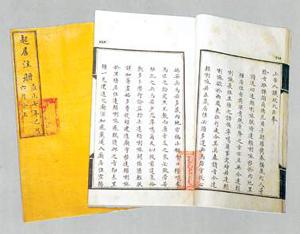
清朝還把藏區的管轄地域做了新的劃分:下令將康區之打箭爐(康定)、理塘、巴塘劃歸四川管轄,將西康南部之中甸、阿墩子(德欽)和維西劃歸云南管轄,同時又將日喀則以西直到阿里劃歸班禪管理。五世班禪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來只同意管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錯林三宗,這就相應縮小了西藏地方政權原來管轄的范圍,達到了分化和削弱西藏統治權限的目的。雍正六年(1728)年末,清政府又把七世達賴喇嘛從拉薩移往理塘,建惠遠寺駐錫,派兵守護,理由是防準噶爾來犯,實際是防止達賴干政,繼續推行“政教分離”政策,“以杜釁端”。在完成了上述這一系列的調整政策之后,將西藏大權交給頗羅鼐全權處置,他在駐藏大臣的協助下,開始著手整頓衛藏戰爭后西藏面臨的財政枯竭、民生凋敝的局面。
從雍正六年起,頗羅鼐即以出眾的智慧和才干,大力調整吏治,清除積弊,減輕民眾負擔,使社會上各種矛盾得到了緩和。由于他政績卓著,恪守臣職,又調解了布魯克巴部落之間的相互仇殺,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嘉獎。雍正九年授封他為“貝勒”,賜銀印一顆。印文用滿、漢、藏三種文字書寫。同時降詔書一道,曰:“西藏事務,妥為掌管。凡漢、藏、蒙古人等無論貴賤,如違爾法令,可依法懲處。爾后,懲辦其他任何貴族,均應向朕稟明處置之原由。”②表明雍正皇帝對他的高度信任。乾隆皇帝即位后,同樣因為他辦事“俱極得體”,對他信賴有加。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年1月),乾隆皇帝晉封頗羅鼐為郡王,從此他的政治生涯進入巔峰時期。
頗羅鼐是藏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愛國領袖,他一生忠于國家,敬信佛教,薄徭輕賦,養民生息,對西藏社會發展和弘揚藏族文化,有過突出貢獻。他的一生業績被記錄在《頗羅鼐傳》中,為后人世代傳頌。
廢除郡王制度 建立噶廈政府
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頗羅鼐去世,他的次子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受詔,襲郡王爵,繼續執政。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完全不同他的父親,是一個性情乖張、桀驁不馴的人。他剛一上臺就激化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使清朝推行的治藏措施受到威脅。他對清朝的旨令,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表面服從駐藏大臣指示,暗中卻大力培植私黨,縱咨逞威,作脫離反抗清朝的準備。乾隆十三年,他要求清廷從拉薩撤軍。清廷鑒于當時緩和西藏局勢的需要,滿足了他的要求。接著得寸進尺,又以防御準噶爾為由,大練兵丁,蓄積力量,并派人去阿里,將其兄殺害,從內部清除了隱患。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他前往薩海地方,調動部兵,搬運炮位,加緊軍事部署,還暗通準噶爾,求其舉事時發兵助戰。珠爾墨特倒行逆施的謀叛企圖已顯露無遺,當時任駐藏大臣的傅清、拉布敦兩人迫于情勢緊急,來不及請示,只有先發制人,遂于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施巧計將珠爾墨特那木扎勒誘至大臣衙門殺死,兩位大臣也在混亂中被珠爾墨特的余黨殺害。
事件發生后,七世達賴立即派官員前往大臣衙門救護,親自領導拉薩的愛國僧俗力量平叛。六世班禪聞知拉薩發生騷亂,也立即派人送糧給駐守前藏的清兵。由于這場謀叛不得人心,很快得到平息。七世達賴在采取行動制止騷亂的同時,向清廷緊急上奏詳情,表明他反對叛逆的決心和立場。乾隆皇帝接到急報,立刻頒布上諭,命四川總督策楞等人領兵赴藏,綏輯地方,搜擒余黨,并會同達賴喇嘛妥辦善后事宜。西藏的愛國僧俗上層人士,對這次二大臣翦除叛亂元兇,平息亂事,無不由衷擁護,拍手稱快。乾隆皇帝在事后總結這次叛亂教訓時說:珠爾墨特那木扎勒之所以恣行無忌,“本因向來權威太盛,專制一方”,自己加恩過重,也有縱容之弊。為此,乾隆十六年(1751)四月,他下詔給四川總督策楞會同大臣班第等人商定新的治藏章程,廢除噶倫擅權的郡王制,正式授權達賴喇嘛掌管西藏政務,由此確立了“政教合一”的管理體制。
此次清朝酌定、頒行的章程,后人把它稱為《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條》③,其主要內容是:
一、廢除郡王掌政制度,正式建立噶廈(西藏地方政府),噶廈內設噶倫四人,三俗一僧,地位平等,秉承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指示,共同處理藏政。有關西藏的重大事務及驛站緊要事件,務需事前呈請達賴喇嘛、駐藏大臣酌定辦理。
二、噶倫等重要官員,須經中央任命,以下補放宗頭目等官,眾噶倫不得任意私放,也要稟報達賴喇嘛并駐藏大臣酌定,奉鈐印文書遵行。
三、在達賴喇嘛治下,增立譯倉(秘書處),內設僧官仲譯(秘書)四人,與噶廈內的卓尼爾二人共同辦事。噶廈一切公文政令,須經譯倉審核,鈐印后才能生效。
四、各寺院堪布喇嘛,遇有缺出或調換,均應由達賴喇嘛酌辦,噶倫不得專擅辦理。遇喇嘛中有犯法者,噶倫等亦應秉公稟明達賴喇嘛,請示遵行。
五、嗣后噶倫、代本等買賣交易差遣,不得擅行私出牌票苦擾百姓,即遇公事有必需烏拉之處,也務必稟明達賴喇嘛,發給印票遵行。
六、藏北三十九族和達木蒙古八旗等地方,劃歸駐藏大臣直接管轄,照內地例置各級官職,同時恢復西藏駐兵,均依駐藏大臣調撥。等等。
章程對西藏政務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具體規定,從內容可以看出,廢除郡王制以后,西藏大權已歸于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專主,駐藏大臣享有了與達賴喇嘛共同處理西藏地方政務的平等地位和權利;做為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從此登上政治舞臺,參與政權管理,這是清朝政府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在西藏政權體制上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結束了多年實行的政教分離政策,確立由達賴喇嘛領導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權的合法性,這是西藏穩定發展的歷史要求。此后二百年間,這一“政教合一”的政體不斷鞏固和完備,駐藏大臣直接管理西藏的權限不斷擴大,西藏與清朝中央之間的政治隸屬關系走上了更加和諧的軌道。
注:
①《清世宗實錄》卷38,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
②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頗羅鼐傳》,湯池安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頁。
③原件藏文。譯文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551-55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