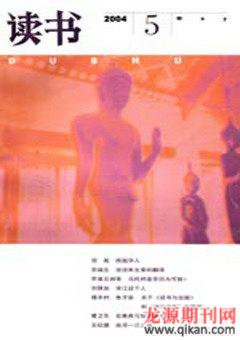跨國華人
項 飆
明年將是萬隆會議召開五十周年。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紀念它,但它的確是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會議之一。萬隆會議集中體現了當時亞非拉世界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對社會主義的向往,一個是對民族國家作為反殖民反霸權、發展本土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的信仰。這兩個思想在理論上并不完全一致,因為按馬克思的設想,民族國家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應該基本消亡。但是在五十年代,亞非拉世界面臨的最根本的實際問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在這一斗爭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幾乎是讓歐洲殖民者退出的惟一有力途徑,盡管很多地方并沒有成立像西方那樣的民族國家的成熟的歷史基礎——這一反西方殖民主義的斗爭顯然是以西方的政治理念為指導的。在此情況下,社會主義常常是為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而服務的意識形態手段。很多國家后來調整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民族國家的力量卻日益強化。在短短幾個年代里民族國家成為組織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公共生活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的概念深深滲透到各個社會角落。
周恩來和尼赫魯是萬隆會議上的重要角色。他們強調國家主權的概念,明確在國際事務中要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決策和行事單位。除了“五項基本原則”,這一思想也明顯體現在他們對僑民政策的態度上。兩國分別以憲法和條約的形式明確表示不承認雙重國籍,僑民必須在居住國和母國之間二者擇一,如果選擇成為居住國的公民,那么就應該效忠于居住國,與母國不應當再有政治關系。直至一九八六年和二○○○年斐濟的兩度排印(印度僑民)政變和一九九八年印度尼西亞的排華暴亂,中、印(度)政府都采取了謹慎關注但不干預的姿態。在意識形態上,兩國都實行社會主義,盡管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關于二者之間的“同志”、“兄弟”關系的文章在一九五○年代廣泛見于兩國。但是兩國的蜜月關系迅速面臨危機。一九六○年代有關麥克馬洪線的爭議和軍事交鋒、印度和蘇聯的聯合、中國和美國與巴基斯坦的溝通,使雙方的關系逐步惡化。在由共產黨執政的喀拉拉(Kerala)邦,左派學生高喊“塌鼻子的中國人,憑什么欺負印度”。可見,社會主義理想絲毫不能保障兩國關系,民族國家利益成為根本的決定因素——鼻子高塌(民族界限)比意識形態左右更為重要。
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這兩個大國重新出現了趨同的趨勢,都開始改革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兩國在僑務政策上開始做出調整。印度從開始不重視印僑、印人(套用“華僑、華人”的分法,前者指持母國國籍的海外居住者,后者指持非母國國籍的永久移民),到九十年代開始重視,到二○○三年和二○○四年兩度召開最高規格的“海外印度人大會”,并正式修憲,承認雙重國籍,僑務政策發生了質的變化。在中國,原來認為至關重要的“華僑”、“華人”的分界日益模糊,聯用的“華僑華人”已經在媒體、學術研究和政策語言中成為固定用語。“族群”概念不僅在學術研究中廣為使用,也進入了政策思考。“族群”基本上對應于日常所說的“中國人”的概念,海內海外、境內境外,一概包括。
如果說人類世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對社會主義的問題似乎已經形成了相對一致的新看法,那么,對于民族國家這一其實比社會主義思潮遠為根本的問題的反思才剛剛開始。二十一世紀初,印度和中國改變原來嚴格按國籍劃分群體、制定政策的做法,在僑務工作中開始采取“跨國主義”的視角,可以視為在實踐中對民族國家制度和絕對主權概念的反思的開始。
跨國行為和國際行為不一樣。“國際”指的是具有明確邊界的國和國之間的關系,而“跨國”視角則認為現實中的很多現象已經超出民族國家和國與國關系的框架,而且具有它們自身的自主性和規律,不能再被看做民族國家的派生或者是國際關系的附屬。比如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犯罪集團”,就具有嚴密的組織,它們不僅把不同國家的資源或者說犯罪機會整合在一起,而且其活動無法由任何單一一國的政府控制。比如說人口走私和販賣(人口走私通常指被走私的人知道自己是要非法跨越國界,人口販賣指運用欺騙和暴力手段將人口販運到他國或者他地),其直接的組織者分散在各國,漂移不定,但是彼此間形成嚴密的跨國合作關系,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利用不同國家之間法律、政策和行政執行能力上的差別以及漏洞來組織人口走私和販賣。比如他們利用西方國家的“政治庇護”政策為走私的人口爭取合法居留權,利用東南亞鼓勵旅游的政策把這個地區作為過渡地帶,利用東歐轉型國家在邊界管理上的松懈以進入西歐等,從而使得其行為無法由任何一國所控制。與此對應的,國際刑警組織則仍屬于“國際”組織的范疇,它是一個政府間機構,它的活動依靠各成員國政府的配合。當某一國認為某一行為和本國的法律或者利益不一致,就可以不與他國合作。現在的問題是,國際刑警組織看來不能根除跨國犯罪,因為后者在組織結構和行動能力上都比前者有更強的自主性。面對日益增多的跨國犯罪和其他許多需要規范的跨國行為,我們顯然需要突破原有的民族國家和國際框架,探索新的機制。
“跨國公司”可能是日常用語中最常見的“跨國”詞匯,可是經常被與國際化的公司混為一談。國際化的公司無非是一個公司具有多個國際分部,特別是在各國的銷售部和加工點,重大決策由公司總部形成,國際分部無非是執行機構。而嚴格意義上的跨國公司是在多個國家擁有固定資產,在經營決策上呈現多中心格局,并且在各國分公司之間有多重橫向聯系的公司。國際化的公司雖然實現了跨國界的市場擴張和生產組織,卻不能像真正的跨國公司那樣在全球范圍內對多類資源進行靈活調配。在理論上,跨國公司應當不受個別民族國家政府的左右(一些學者提出大型跨國公司應該和民族國家相提并論,成為當今世界社會組織形式上的兩類基本單位),而國際化的公司只是隸屬某一國的公司在經營空間上的擴展而已。
從跨國和國際這兩個概念的比較也可看出“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區別。“國際化”指的是在不觸及原來的民族國家制度框架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聯系的加強。現在很多文獻,把全球化和跨國性簡單視為跨越邊界的各類流動(人的、物的、信息的、觀念的等等)的增加和跨越邊界的各類聯系的加強。但是,迄今為止,世界移民不到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三,現在的遷移遠比一百年前困難。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還從沒用過電話,更不要說傳真和互聯網了。就世界貿易來看,相當一部分的貿易事實上是大型公司的內部交易(即公司從在A國的子公司賣到在B國的子公司),而大部分的海外直接投資乃是用于大型公司的兼并和資產購買。在美國注冊的公司多達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資其實來自于他們在海外賺得的、不能轉移的利潤。所以,如果認為全球化就是一個各要素在全球范圍流量加大、聯系加強的過程,那么現在的全球社會并沒有到達結構性轉變的時刻。但是,全球化和跨國性不僅是一個“流”和“線”(聯系)的問題,更意味著財富和資本積累的新的策略和方式、新的社會分化模式以及新的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的關系。所以,在全球化過程中真正重要的是一批跨國力量的崛起,包括他們對地方社會的滲透和在各地“扎根”(而不是簡單的“流動”和“聯系”)。
與此相關聯,“跨國性”是一個制度概念而不是空間概念。不少學者質問:所謂跨國性和全球化有什么新意呢?人不是在幾百年以前就有大規模的遷移嗎?以中國為例,鴉片戰爭以后,大量華人下南洋,盡管交通條件非常落后,他們仍然和家鄉保持聯系,并且念念不忘要回到家鄉。英國一八三三年廢除奴隸制后,大量印度勞工被招到全球各地的英國海外殖民地以頂替以前的奴隸。和中國早期的移民非常相似,他們也夢想著哪一天能回國。這些在殖民主義時代長距離跨地域的移動和聯系不能被認為是“跨國性”的體現。這是因為當時處于“世界帝國”的格局下,民族國家的體系尚未建立。“跨國”是對民族國家體系的反動,民族國家體系尚未確立,提“跨國性”就沒有多大意義。現在西方很多研究把任何跨越國界的聯系和活動都歸為“跨國現象”,確實造成很多混淆。嚴格意義上的跨國現象一定要是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邏輯,超越了制度意義上的國界(而不是地域上的國界)。比如美國在世界各地派兵就不屬于跨國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是完全按照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設計的;但是溫州人到東歐賣貨,同時和南歐北歐的市場建立聯系,再把外幣用民間渠道運回來,就屬于跨國行為,因為這套運作有其自主性,不是哪一國的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跨國行為不一定都屬于強大的組織。有自上而下的跨國性,也有自下而上的跨國性。
自下而上的跨國行動中(即普通人的,而不是大型公司的跨國行為),人口遷移是一個典型例子。過去人們認為,遷移就意味著移民和流出地切斷關系,進而轉變成流入地的一分子。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移民和流出地、流入地甚至流經地同時保持密切聯系,同時歸屬于多個社會。從一九九○年代初國際學術界提出運用跨國視角研究移民以來,十年間產生了大量文獻,探討移民如何形成“跨國空間”。但是和國際上傳統的關于移民的文獻一樣,其實證資料主要是關于從南美到北美、歐洲內部(如從土耳其到西歐)以及從北非到歐洲的移民。盡管華人華僑是一個不小的研究領域,但是采用較新的、寬闊的視野的新近研究尚不多見。Aihwa Ong在她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一書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和重要的理論設想。按她所舉的典型例子,一些香港的華人持多國護照,在多國擁有資產。持多國護照是為避免政治風險,在多國擁有資產是要在資本全球化的態勢下更好地追逐商業利益。他們在各國之間建立聯系,來回穿梭。他們追隨的是國際資本的運行規律,不再是某一國家傳統意義上的公民,他們所要積累的是屬于他們卻不受某個國家控制的資產。或者說,他們已經成了國際市場的公民。
新加坡國立大學劉宏博士的《戰后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明確提出了“跨國華人”的范疇。他把“跨國華人”定義為:“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地同(自己的或父輩的)出生地聯系起來,并維系起多重關系的移民群體。他們的社會場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為特征。作為跨國移民,他們講兩種或更多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擁有直系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手段”(215頁)。劉宏認為現在有三類“跨國華人”:一、“再次移民者”,即一批從傳統的華人移居地(東南亞)遷至發達國家的早期移民(其人數超過二百萬),這些移民在新舊移居地之間形成跨國網絡;二、早期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 因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而與大陸重新建立密切聯系;三、最近從大陸出來的新移民,包括技術移民、家庭團聚移民和非法移民。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啞鈴模式”(即華人在中國和海外都有事業),“太空人模式”(即在多處的事業之間來回穿梭,促進共同發展),“風箏模式”(在多個國家發展事業的同時和國內保持聯系)等等,都是“跨國華人”群體的具體行為表現。中國政府將原來針對留學生的“回國服務”的提法改為“為國服務”,并推出“春暉計劃”,支持“長江計劃”以鼓勵科技華人短期回國交流,同時又保持他們在海外的事業發展,也與“跨國華人”的邏輯相一致。劉書指出,“跨國華人”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終身“跨國”,有人到了一定階段可能回歸到“葉落歸根”和“落地生根”的模式中去,但是新的移民將不斷補充到跨國華人的隊伍中來。盡管對跨國華人的具體行為特征還需要通過更多的實證資料加深了解,并將此概念進一步理論化,但是這個范疇的提出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除了該書提出的三類“跨國華人”,我想那些身在國內,但是在跨國公司占有較高職位,有的還持有海外長期居留證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算作跨國華人?那些長期為跨國公司做代理,或者和國外公司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和國外公司互相參股的,是不是可以算作跨國華人?在研究中,我把他們歸入新興的“跨國民族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收入、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上顯然和一般的國民不同。更本質的是,他們的利益是和世界資本而不是本土資本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是全球化滲入到本土社會的關鍵媒體,但他們又有民族性的一面。我傾向于把這些“跨國民族中產階級”和“跨國華人”聯系起來看,因為“跨國主義”的概念本來就是要打破原來的研究界限,把移民研究和更廣泛的經濟社會變遷聯系起來(西方現有文獻在這方面也做得很不夠)。如果我們能跳出就移民論移民的圈子,可能會導致一些理論創新。但是“跨國民族中產階級”和“跨國華人”這兩個概念應該分別怎樣提升,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一個文化的概念又可以如何溝通,都需要進一步的工作。
劉書進一步說明了新加坡華人跨國網絡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如其副標題所示,該書對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在三個層次上做了審視:本土(新加坡)、區域(東南亞)和全球。華人初到新加坡時,沒有任何公共組織,為了在生活上互相照顧,特別是后來為促進生意上的發展,紛紛成立以地域或者宗祠為基礎的社團組織。這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核心。近來不少文獻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是一個資本追求資本、商品創造商品的過程,不僅需要國家機器對所有權制度做保障,而且是一個建立信用和交易秩序的過程。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一個階級問題,也是一個制度過程。在沒有其他公共組織的情況下,各種社團便成了當地華人商業經濟的基本制度條件。由此,華人社會形成了所謂的“幫權經濟”,即“地域/方言群體和社會/職業廣泛而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在早期,各類社團以及幫權經濟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是和僑鄉的聯系。大家對一個共同的家鄉的向往和回憶是各類華僑社團把大家團結在一起的基礎。例如,一九四七年四月新加坡豐順會館響應廣州豐順會館的捐款請求,發動馬來亞各地同胞捐款,籌集了六百萬國幣。一九四七年九月,豐順會館在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注冊為海外會員,在此后的數年,豐順縣政府呼吁捐資賑災,汕頭豐順會館也請求捐建會館大樓,這些請求大多數得到滿足。但是到了一九五○年代,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中國和華僑的關系經歷了一個歷史轉變(據估計,在戰后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大概有二千萬華僑及家屬明確變成居住國公民,宣告了“華僑時代的結束”。印度的情況也相似。中國和印度在爭取民族獨立、抵抗外侮的時候,僑民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甘地、尼赫魯、梁啟超、孫中山都是在海外的時候發展了他們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而在建國之后,很多僑民倒成了“外人”,當時不少印僑、華僑想不通),僑民社團和祖國的聯系也逐漸淡化,而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強調他們作為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但是有意思的是,新加坡華人社團在經歷本土化的同時,也開始了“區域化”和在一定意義上的“跨國化”的進程,即他們和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團加強聯系,特別是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一些社團似乎也很注意和日本華人社團的聯系。劉書把華人社會此時的區域化歸因于新加坡剛剛成立時的不安全感,小小島國上的華族感覺自己為“馬來亞人的海洋”所包圍,從而需要和其他地方的華人團體發展跨國聯系。
八十年代后期,新加坡華人社團的跨國性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李光耀時期將一切置于國家之下、限制社團的做法得以調整,第二代領導人提出要從建立國家的時代進入建立社會的時代;另一方面,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新加坡要發展為區域和世界貿易中心的戰略,推進了跨國網絡的出現,而原來和國家體系緊密聯合在一起的社會組織不具有這樣的能力,華人的跨國網絡和跨國活動由此得以發展。
縱觀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從一開始以社團為主、發揮長距離跨區域聯系的功能,到民族國家涵蓋一切統統包攬,強調絕對國家主權和國家邊界,再到國家和跨國的民間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社會和國家一直在互動。這一過程對我們關于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的研究可能也有啟發。現在看來,打破原來國家所設定的邊界的要求是社會發育中的一個重要動力。比如說,北京的“浙江村”和其他城市很多移民社區是中國較早自發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居于國家體制設計之外),這些社會系統所以能在當時發育起來,是因為它們脫離了國家體制所設定的行政邊界,并通過他們自己的遷移行為和網絡形成跨區界的聯系。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可能把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帶進一個新的場景。企業要進入國際市場,企業要解決各類貿易摩擦,主要不能靠國家政府,而要靠企業之間的關系:既包括國內相關企業的橫向聯系,也包括跨國的聯系。國家和社會關系的核心問題,將不僅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資源再分配和公共管理,而且也將聯系到不同行動范圍之間的緊張:社會是具有高度彈性的,它的一部分將必然成為“跨國”的,而國家的權力邊界則是有剛性的。如何以相對剛性甚至僵化的機構面對跨國的社會和政治行動,顯然將成為對民族國家的新挑戰。
近日,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彭軻等人的專著《跨國華人:福建移民在歐洲》。該書基于作者們在福建、英國、匈牙利、意大利的深度調查,同時運用了美國、羅馬尼亞、俄羅斯、荷蘭等國的資料,是一部非同尋常的“全球民族志”。和劉書不同,該書不是歷史回顧,而是對正在發生的流動情況的細致分析;其側重點不在社團,而在流動者個體。這本書將需要專門一篇文章來做評介,這里要提的是,它把跨國華人的概念和“中國的全球化”聯系起來。全球化不是單維的全球一體化的過程,而應該被理解為不同的文化在全球舞臺上的相互競爭。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開始和國際接軌的時候,在以西方為主體的世界舞臺上扮演相對邊緣的角色;而從一九九○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和世界空前緊密的融合,它倒采取了“以我為主”的姿態。該書認為福建人的全球性流動策略是“中國的全球化”的一個體現,同時中國對這些新移民的態度和政策也是“中國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國家和新移民形成的新型關系將使得它對資本、物品和信息的全球流動有更好的把握。所以,社會的跨國性對國家并不總是壞事,如果國家能夠及時調整其功能和手段,就可以借跨國之勢來壯大自己,以更主動的姿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
跨國性可能帶來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變化,也是由于跨國性可能帶來社會內部的新的分化。顯然,在現階段,真正能成為“跨國華人”的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他們代表著國際市場的利益,能量巨大,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新崛起的最有優勢的群體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人還是“地方”的,只能以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的形式來組織自己的公共生活。那么這兩個群體是什么關系?特別是國家應該在他們之間扮演什么角色?印度的這個問題比中國更明顯。一方面,印度原來的社會分化很嚴重,另一方面由于其殖民地的歷史和近來計算機等產業的發展,在印度國內外都出現了明顯的跨國群體。面對跨國群體的游說和壓力,特別是要犧牲下層社會的利益來滿足跨國群體的時候,應該怎么辦?隨著印度跨國群體的形成,還出現了一個很令人擔憂的情況,即狂熱印度教的復興。按照現在狂熱的印度教的思想(有人稱之為“宗教民族主義”),生在印度、長在印度的穆斯林印度公民不是印度人而是“外國人”,而信印度教的生在美國的美國公民倒應該算是印度人。這和近來在孟買和海得拉巴(Hyderabad)的宗教騷亂都有關系。
回到文章開始提到的萬隆會議,盡管現在看起來當時對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的信仰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但是其世俗公民理念看來還是應該堅持的。即,每一個人首先應該是一個世俗的具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公民,而不應按宗教、民族來劃分群體。但是如何具體來理解和調節民族國家和跨國群體、跨國群體和地方群體、政治認同(世俗的民族主義)和文化認同(宗教信仰等)之間的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
(《戰后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劉宏著,廈門大學出版社二○○三年版;Pieke, Frank, Pal Nyiri, Mette Thuno and Antonella Ceccagno.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