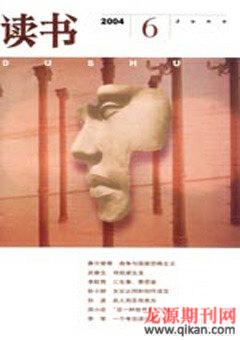品書錄
王麗麗等
反省大事件,復(fù)活小細(xì)節(jié)
王麗麗
盡管“我與胡風(fēng)”這一總題基本限定了一個(gè)切己的回憶角度,但書中的不少文章卻超出了人們對(duì)一般回憶的預(yù)想和期待,很多文章似乎有意淡化展示傷口和苦難的痕跡,而盡可能對(duì)事件展開冷靜理性的反思。由于這樣的反思立足于作者本人數(shù)十年身歷其境的切身經(jīng)驗(yàn),其達(dá)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就遠(yuǎn)不是一般的泛泛研究所能夠輕易企及。
這樣的文章以綠原先生的長(zhǎng)篇力作《我與胡風(fēng)》為代表。對(duì)于胡風(fēng)研究而言,這篇文章至少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可以提供重要啟示:提議學(xué)術(shù)界研究與胡風(fēng)事件密切相關(guān)的兩大問(wèn)題,即“胡風(fēng)集團(tuán)”集結(jié)和被剿滅的過(guò)程,以及舒蕪現(xiàn)象對(duì)中國(guó)文化界和知識(shí)分子所產(chǎn)生的教訓(xùn);澄清了人們對(duì)胡風(fēng)“高傲,強(qiáng)項(xiàng),不肯低頭認(rèn)輸”的普遍誤解,向人們?cè)敿?xì)展示了胡風(fēng)在建國(guó)初期想真誠(chéng)負(fù)責(zé)地檢討,而又始終對(duì)批判者的邏輯不得要領(lǐng),因此無(wú)從措手足的尷尬處境;綠原先生的一些直覺(jué)感受和判斷也屢屢被后來(lái)的研究證明。
此外,作為直接參與“三十萬(wàn)言”和胡風(fēng)的《我的自我批判》草擬的重要當(dāng)事人,綠原先生還提供了許多外人無(wú)從知道的歷史細(xì)節(jié),如胡風(fēng)在寫作“三十萬(wàn)言”期間,為了確保自己在理論方面的萬(wàn)無(wú)一失,曾經(jīng)多次與朋友們?cè)谔浇衷⑺目蛷d里,就林默涵、何其芳兩篇批判文章所涉及的所有理論要點(diǎn)展開過(guò)模擬答辯,他是以必勝的理論確信,而迎來(lái)上書事實(shí)上的慘敗。對(duì)于研究者而言,仔細(xì)體會(huì)這些意味深長(zhǎng)的細(xì)節(jié),一定能夠得到深刻感悟。
提供歷史證言、保存歷史細(xì)節(jié),也可以說(shuō)是《我與胡風(fēng)》一書最重要的價(jià)值之所在。在耿庸先生的回憶中,作者完整地記錄下了一段當(dāng)年胡風(fēng)先生親口對(duì)他所說(shuō)的區(qū)分宗派和正常的文學(xué)流派的一段話,胡風(fēng)在這段話中還特意對(duì)宗派主義所包含的封建性做了鞭辟入里的批判,這對(duì)澄清人們普遍存在的對(duì)胡風(fēng)集團(tuán)宗派主義的誤解是一段關(guān)鍵的證詞。與耿庸先生的證詞相呼應(yīng),羅洛先生回憶記錄的胡風(fēng)“希望朋友們每一個(gè)人獻(xiàn)一集頌詩(shī)給這個(gè)時(shí)代”,以便大家集合成“大詩(shī)人”的思想,又在另一個(gè)方面加深了人們對(duì)胡風(fēng)堅(jiān)持創(chuàng)建文學(xué)流派、經(jīng)營(yíng)文化生態(tài)良苦用心的理解。對(duì)于胡風(fēng)研究的其他重要方面,《我與胡風(fēng)》一書所提供的細(xì)節(jié)也同樣具有糾正偏見、深化認(rèn)識(shí)的作用。
相對(duì)于初版本而言,在盡可能填補(bǔ)歷史空白、彌補(bǔ)歷史縫隙方面,增補(bǔ)本《我與胡風(fēng)》達(dá)到了更深、更細(xì)的程度。新增的大部分文章似乎都有意在以前人們所忽略的方面著筆,尤其注重彰顯小事物和小角色。歐陽(yáng)莊的文章首次詳細(xì)地披露了有關(guān)《螞蟻小集》的許多饒有趣味且讓研究者不得不重視的細(xì)節(jié)。作為一九四○年代末創(chuàng)辦的眾多帶有“七月派”標(biāo)志的進(jìn)步文藝小刊之一,至今仍然保留下來(lái)的刊物本來(lái)就已非常罕見,即便有研究者費(fèi)盡周折讀到這一舊刊,又可能受到許多細(xì)節(jié)的誤導(dǎo),對(duì)之心生疑惑。如果不是當(dāng)事人自己娓娓道出,其中的任何一個(gè)疑惑,都不知要耗費(fèi)研究者多少爬梳剔抉的功夫才能夠厘清。
增補(bǔ)本還新增收錄了一組文學(xué)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物甚至是“小人物”的回憶鉤沉文章,包括自從一九三九年在“七月詩(shī)叢”中出版過(guò)第一本詩(shī)集《突圍令》以后就基本上與“七月派”斷絕了文學(xué)往來(lái)的詩(shī)人莊涌,幾無(wú)文學(xué)作品行世的原中國(guó)作協(xié)創(chuàng)聯(lián)部的普通工作人員嚴(yán)望,以及僅僅因?yàn)椤叭牧稀敝刑峒暗囊痪洹疤K州一同志”就從此“淪落坎坷”大半生的原蘇州地下黨員許君鯨。或許,對(duì)他們不幸遭遇的發(fā)掘不會(huì)對(duì)文學(xué)史或思想史的撰寫產(chǎn)生什么實(shí)質(zhì)性的改變,但編撰者因此顯現(xiàn)出來(lái)的關(guān)注孤弱的人文情懷,卻可以使人們對(duì)歷史的理解變得溫潤(rùn),讓歷史敘述不再顯得那么枯干、勢(shì)利和冰冷。
“增補(bǔ)本”還有一個(gè)編輯特點(diǎn)也頗可值得稱道。書中有多組文章明顯可以彼此照應(yīng),以便讀者對(duì)照閱讀。書中涉及胡風(fēng)和劉雪葦關(guān)系的一組文章便是例證。劉雪葦與胡風(fēng)的關(guān)系在一九五五年曾被認(rèn)為“類似饒漱石和高崗的關(guān)系”,為此劉雪葦自然“付出過(guò)高昂的代價(jià)”。《我與胡風(fēng)關(guān)系的始末》是劉雪葦在胡風(fēng)作古兩周年之際寫作的試圖澄清兩人關(guān)系真相的文章。很顯然,幾十年的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已經(jīng)教會(huì)了作者“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所以在文章中,劉雪葦著意對(duì)“雪胡關(guān)系”進(jìn)行了一番“純化”。為此,劉雪葦還無(wú)保留地表達(dá)了他對(duì)胡風(fēng)在為人處世方面的一些看法。從為文的坦率程度來(lái)看,劉雪葦所言自然沒(méi)有虛誑,但既然是“澄清”和“純化”,文章當(dāng)然也就可能忽略了兩人關(guān)系中原本屬于正常的“友誼”方面,過(guò)濾掉確實(shí)存在過(guò)的美好情感。對(duì)于劉文中的這一“矯枉過(guò)正”,梅志先生在《追憶往事——悼念雪葦同志》一文中委婉地做了補(bǔ)正,并對(duì)其中明顯的誤會(huì)做了解釋。
通過(guò)多篇文章彼此對(duì)照來(lái)彰顯相對(duì)可靠的歷史真實(shí),這一編輯特點(diǎn)不止是在展示“雪胡關(guān)系”這一個(gè)問(wèn)題上有所體現(xiàn),而是貫穿全書。從終極意義上說(shuō),這也是胡風(fēng)先生編輯遺風(fēng)的體現(xiàn)。因?yàn)楹L(fēng)先生的一個(gè)重要編輯思想就是:編輯者需要營(yíng)造的是一個(gè)公共交流的自由空間,對(duì)于這一空間中存在的各方的分歧和對(duì)立,編者不必強(qiáng)行干涉或整合,而應(yīng)該直接訴之讀者的理性判斷,給讀者和批評(píng)家留下選擇和判斷的余地。
(《我與胡風(fēng)——胡風(fēng)事件三十七人回憶》(增補(bǔ)本),張曉風(fēng)編,寧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無(wú)邊的典型”
趙勇
李衍柱先生是通過(guò)對(duì)“典型”范疇的研究走上文藝學(xué)研究之路的,因此,在《路與燈》中,我特別注意他對(duì)典型問(wèn)題的最新看法。以前,在閱讀他的那本《馬克思主義典型學(xué)說(shuō)史綱》時(shí),我一直認(rèn)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傳統(tǒng)中的產(chǎn)物,但《路與燈》中所搜集的關(guān)于典型問(wèn)題的文章讓我有了一個(gè)新的想法:除了馬克思主義文論傳統(tǒng)這一維度之外,典型問(wèn)題其實(shí)還隱含著一個(g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論傳統(tǒng)的維度。因?yàn)楸砻嫔峡矗謇淼氖俏鞣降湫蛯W(xué)說(shuō)的流變史(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但實(shí)際上,典型問(wèn)題又何嘗不是對(duì)風(fēng)行于中國(guó)大半個(gè)世紀(jì)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之路的回應(yīng)呢?然而,從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開始,現(xiàn)實(shí)主義在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擠壓下漸漸變得風(fēng)光不再,典型問(wèn)題也幾成過(guò)時(shí)的話語(yǔ)而不愿被人提起。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還有必要抓住典型不放嗎?典型問(wèn)題還是不是文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需要慎重對(duì)待的一個(gè)問(wèn)題?
作者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話來(lái)概括: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許多人的記憶中,講究典型化和塑造典型人物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套路,那是不是就意味著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然放棄了典型化的追求呢?問(wèn)題似乎沒(méi)有那么簡(jiǎn)單。隨著作者對(duì)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思潮的梳理,我們可能會(huì)吃驚地發(fā)現(xiàn),那些非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文學(xué)家和理論家(如雨果、克羅齊、韋勒克、艾略特、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納、喬伊斯、卡夫卡、托馬斯·曼、龐德、普魯斯特、馬爾克斯等)都曾不同程度地關(guān)注過(guò)典型問(wèn)題,同時(shí)也試圖在其創(chuàng)作中塑造出屬于另一文學(xué)譜系中的典型人物。當(dāng)然,作者也同時(shí)指出,雖然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程度不同地使用了典型理論,但其視角與內(nèi)涵又與現(xiàn)實(shí)主義語(yǔ)境中的典型理論大不相同。因?yàn)榍罢吒粗厍楦斜疚缓椭饔^心靈本位,而后者則更重視理性本位與生活本位。于是,表面上看,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似乎是拋棄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典型,但實(shí)際上他們開始的是向更高一輪的典型的進(jìn)軍。
應(yīng)該說(shuō),這是一個(gè)很有意思的理論課題,也是我們當(dāng)今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需要解決的一個(gè)問(wèn)題。因?yàn)槲易⒁獾椒▏?guó)“新小說(shuō)派”理論家納塔麗·薩羅特在闡述“新小說(shuō)”與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的區(qū)別時(shí)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這樣一段意味深長(zhǎng)的話:“在那全盛時(shí)代,小說(shuō)人物真是享有一切榮華富貴,得到各種各樣的供奉和無(wú)微不至的關(guān)懷。他們什么都不缺少,從短褲上的銀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脈絡(luò)暴露的肉瘤。現(xiàn)在,他逐步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從地窖一直到頂樓,塞滿了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最細(xì)小的小玩意)、他的資財(cái)與地位、衣著、身軀、容貌。特別嚴(yán)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寶貴的所有物:只屬于他一個(gè)人所特有的個(gè)性。有時(shí)甚至連他的姓名也蕩然無(wú)存了。”(《法國(guó)作家論文學(xué)》,382頁(yè))如此這般的冗繁削盡留清瘦,“新小說(shuō)”究竟想干什么呢?薩羅特一語(yǔ)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現(xiàn)在看來(lái),重要的不是繼續(xù)不斷地增加文學(xué)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現(xiàn)矛盾的感情的同時(shí)存在,并且盡可能刻畫出心理活動(dòng)的豐富性和復(fù)雜性。”(同上,389頁(yè))
如果薩羅特的這種思考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基本特征,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在二十世紀(jì)的許多現(xiàn)代派小說(shuō)中,傳統(tǒng)意義上的那種典型性確實(shí)已經(jīng)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心靈世界的矛盾性、豐富性和復(fù)雜性,而這種心靈世界的復(fù)雜含混又與外部世界的無(wú)從把握形成了一種同構(gòu)關(guān)系。這個(gè)時(shí)候,卡夫卡筆下的K可能沒(méi)有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tái)面目清晰、性格明確,但K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那種特殊的寓意恰恰表明,他雖然無(wú)法被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所接納,但他毫無(wú)疑問(wèn)又成了另一類典型隊(duì)伍中的一員。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我覺(jué)得李衍柱先生所做的工作有點(diǎn)像法國(guó)的加洛蒂。加洛蒂以“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開放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邊境線,讓包括卡夫卡在內(nèi)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進(jìn)行了一次文學(xué)移民;李衍柱同樣沒(méi)有固守典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疆界,他把喬伊斯、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等作家筆下的人物吸納到了典型的隊(duì)伍中,從而完成了一次典型的擴(kuò)充,這種典型是不是也可以稱為“無(wú)邊的典型”呢?
(《路與燈——文藝學(xué)建設(shè)問(wèn)題研究》,李衍柱著,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二○○三年版,32.00元)
文學(xué)史的難題
錢文亮
近幾年來(lái),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jìn)展,洪子誠(chéng)《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與陳思和《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的問(wèn)世,則被看作是這一學(xué)科成熟的標(biāo)志。但在另一方面,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的問(wèn)題卻因此而突出,在洪子誠(chéng)最近主編的與其《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配套的《作品選》和《史料選》中,這些問(wèn)題以更加具體的方式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
作為主編者,洪子誠(chéng)特別將自己的這套書定名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作品選》和《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史料選》,顯然是想與其他無(wú)“史”的同類選本有所區(qū)別。事實(shí)上,單看《作品選》,這套書從總體框架到具體篇目,都有一些耐人尋味的變化。例如,在大的體裁方面,報(bào)告文學(xué)一篇都沒(méi)選,八九十年代的雜文也沒(méi)有;但詩(shī)歌的篇幅有較大的增加。而最出人意料的,要算“八個(gè)樣板戲”中《紅燈記》和《沙家浜》的入選,這是前所未有的。它馬上帶出的問(wèn)題就是:面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現(xiàn)象,究竟如何確認(rèn)、取舍和處理?這自然涉及到編選者自己的文學(xué)史觀和有關(guān)“文學(xué)性”的認(rèn)知標(biāo)準(zhǔn),以及如何處理文學(xué)價(jià)值(“文學(xué)性”)與文學(xué)史價(jià)值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
通觀現(xiàn)有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選本,普遍存在的一個(gè)問(wèn)題就是,作品取舍應(yīng)該依據(jù)怎樣的標(biāo)準(zhǔn)。顯而易見,為數(shù)不少的編選者對(duì)此采取了回避的或者含混的態(tài)度,選本中看不出一種比較統(tǒng)一的、明確的尺度;而在一些明確堅(jiān)持以“文學(xué)性”為取舍標(biāo)準(zhǔn)的選本中,編選者對(duì)于“文學(xué)性”的理解又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個(gè)選本中,所謂“文學(xué)性”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際上也是不統(tǒng)一的。即以“八個(gè)樣板戲”為例,如果將“文學(xué)性”定義在藝術(shù)形式的獨(dú)立品格與價(jià)值、新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的積累與貢獻(xiàn)上,“八個(gè)樣板戲”,特別是其中的《紅燈記》和《沙家浜》,在對(duì)民族傳統(tǒng)的“折子戲”等藝術(shù)形式的繼承與革新上,在探索傳統(tǒng)形式怎么適應(yīng)現(xiàn)代生活方面,顯然積累、貢獻(xiàn)了新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在保持傳統(tǒng)的一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格局里頭,加入了很多新的東西,而又沒(méi)有使它支離破碎。包括鋼琴伴唱《紅燈記》、《沙家浜》的交響樂(lè),都做了很多嘗試。所以它們能夠膾炙人口,流傳至今。而以往的選本不選它們,所依據(jù)的恰恰是一種“政治性”標(biāo)準(zhǔn),一種對(duì)“文革”的政治判斷。實(shí)際上,在剝離了具體的政治語(yǔ)境之后,它們是否仍然具有藝術(shù)價(jià)值和魅力,這才是判斷其藝術(shù)性或“文學(xué)性”的關(guān)鍵。像曹操的詩(shī)、《三國(guó)演義》、法國(guó)的《雙城記》等,也是很政治化的。所以,僅著眼于文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這一層面,對(duì)“文學(xué)性”的理解并不全面、準(zhǔn)確。并不是說(shuō)跟政治聯(lián)系緊密的或者說(shuō)政治性強(qiáng)的,就沒(méi)有藝術(shù)性或“文學(xué)性”。“文學(xué)性”的實(shí)現(xiàn)要靠具體的文本來(lái)說(shuō)話,其中需要太多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因素的“合力”。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超功利、反功利的本質(zhì)、反對(duì)文學(xué)工具論是一回事,而能否實(shí)現(xiàn)較高的“文學(xué)性”是另一回事。
其實(shí)在一些編選者那里,問(wèn)題并不僅僅在于對(duì)“文學(xué)性”的誤解或不求甚解上。你甚至可以懷疑:他們的有關(guān)“文學(xué)性”的知識(shí)到底有多少?他們?cè)诋?dāng)代藝術(shù)形式本身問(wèn)題上的專門研究與思考到底有多少?否則,便很難理解在藝術(shù)探索方面“領(lǐng)跑”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實(shí)踐的先鋒詩(shī)歌,在文學(xué)界和諸多“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選本中所受到的冷遇。“這是不公平的”(洪子誠(chéng)語(yǔ))。這實(shí)際上又帶出了一個(gè)題外話:衡量一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者的標(biāo)準(zhǔn)與要求問(wèn)題。成熟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家,應(yīng)該有內(nèi)(內(nèi)部研究)外(外部研究)兼修、打通歷史的硬功夫。
毋庸置疑,選編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有關(guān)“文學(xué)性”標(biāo)準(zhǔn)的困惑,有時(shí)反映出的實(shí)質(zhì)上是在文學(xué)價(jià)值(“文學(xué)性”)與文學(xué)史價(jià)值這兩種標(biāo)準(zhǔn)之間的搖擺。文學(xué)史研究及其標(biāo)準(zhǔn),如果獨(dú)尊文學(xué)性,會(huì)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而要依據(jù)文學(xué)史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際上要考慮的因素就很多,包括作品之于某種文學(xué)思潮的代表性及其位置,它對(duì)當(dāng)時(shí)整個(gè)文學(xué)產(chǎn)生的影響與效果,涉及很復(fù)雜的方面。如果文學(xué)史還承擔(dān)著對(duì)文化的變遷,甚至包括藝術(shù)形式、體裁的轉(zhuǎn)換流變的考慮的話,那么作品、包括史料的選擇就會(huì)出現(xiàn)多樣化的局面。但是如果單從文學(xué)史的標(biāo)準(zhǔn)出發(fā),又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問(wèn)題:有些在文學(xué)史上轟動(dòng)一時(shí)、影響很大的作品,文學(xué)性卻不一定很高;有些代表或開啟了一定時(shí)期文學(xué)思潮的作品,在更長(zhǎng)遠(yuǎn)的歷史脈絡(luò)中,在更開闊的人文視野里,卻顯示出不可救藥的局限性和單一性。像包括“八個(gè)樣板戲”在內(nèi)的“十七年文學(xué)”與“文革”時(shí)期的作品,致命的問(wèn)題就在這里。因此可以理解陳思和提出的“潛在寫作”的良苦用心,他試圖通過(guò)突顯另一種非主流的、與當(dāng)時(shí)政治相對(duì)疏離的寫作現(xiàn)象,通過(guò)挖掘另一類具有審美現(xiàn)代性、文學(xué)價(jià)值較高(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含量較高、藝術(shù)視野較為開闊)并體現(xiàn)出文學(xué)內(nèi)在發(fā)展規(guī)律與獨(dú)立性的作品序列,來(lái)解決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中兩種標(biāo)準(zhǔn)之間的矛盾。
然而陳思和的這種意圖要實(shí)現(xiàn)起來(lái)卻是有困難的。最關(guān)鍵的問(wèn)題就在于如何確認(rèn)、對(duì)待這些作品的寫作時(shí)間的真實(shí)性。這一點(diǎn)直接影響到我們對(duì)它們的文學(xué)史意義和地位的判斷。因?yàn)檫@些作品雖然據(jù)知情者(作者)交代是寫于“十七年”或“文革”時(shí)期,但發(fā)表卻是在“文革”之后。這當(dāng)然會(huì)產(chǎn)生學(xué)術(shù)上的爭(zhēng)議。其實(shí)這個(gè)問(wèn)題在洪子誠(chéng)的這套選本中同樣存在,對(duì)這些作品的年代的處理,基本上也是按照作者標(biāo)明的寫作年代在作品選中作注。如此看來(lái),這是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者所遇到的共同的難題。
不過(guò),對(duì)此難題,洪子誠(chéng)曾透露過(guò)一種謹(jǐn)慎、折衷的處理方式,即在修訂《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時(shí)候,除了交代、提到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間還進(jìn)行寫作活動(dòng)之外,在八十年代特別地突出過(guò)去作品的挖掘問(wèn)題,對(duì)包括《傅雷家書》在內(nèi)的那些寫作在特殊時(shí)代而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發(fā)表、卻又在八十年代產(chǎn)生文學(xué)影響的私人性的東西,專辟“過(guò)去文學(xué)化石的挖掘”一節(jié),以此呈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復(fù)雜性、真實(shí)性,闡發(fā)其文學(xué)性的價(jià)值。
考證、處理作品寫作年代上的困難,實(shí)際上反映出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史料挖掘上的問(wèn)題與困難。相對(duì)而言,當(dāng)代是比較特殊的一個(gè)歷史時(shí)期。它有很多運(yùn)動(dòng),政治和文學(xué)之間有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而且,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料的問(wèn)題還帶有一種時(shí)期的特點(diǎn),什么種類的材料在什么時(shí)期具有什么樣的價(jià)值,并不是完全一樣的。
迄今為止,國(guó)內(nèi)當(dāng)代文學(xué)方面的史料編纂、整理和出版幾乎還是半空白的狀態(tài)。現(xiàn)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界開始普遍意識(shí)到了改變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學(xué)科地位,加強(qiáng)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學(xué)科建設(shè)問(wèn)題,但大家談?wù)撟疃嗟膮s是方法與視野的更新和擴(kuò)展問(wèn)題,而作為學(xué)科最基礎(chǔ)的史料工作卻被有意無(wú)意的忽視著。正是缺乏史料意識(shí),使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面貌與真相多年來(lái)在很多人那里是大同小異,當(dāng)代文學(xué)內(nèi)部與外部的很多問(wèn)題都并未得到清晰的呈現(xiàn)和解釋。而洪子誠(chéng)與陳思和等人的突破正是建立在對(duì)史料問(wèn)題的充分重視與有眼光的取舍上。但是他們的工作僅僅是一個(gè)良好開端與啟示,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在重要概念的清理上、在學(xué)科知識(shí)的建構(gòu)上、在史料的挖掘工作上,都有大量緊迫的工作要做。
(《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作品選》,《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史料選》[上下],洪子誠(chéng)主編,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二○○二年七月版,111.00元。洪子誠(chéng)著:《問(wèn)題與方法——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講稿》,三聯(lián)書店二○○二年八月版,29.00元。《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20.00元;《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陳思和主編,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35.00元)
關(guān)于“造反有理”
俞潤(rùn)生
三十多年前,發(fā)行上億冊(cè)的、用紅色塑料書套裝幀的《語(yǔ)錄》中有“造反有理”一條。這條語(yǔ)錄被譜為歌曲,身著軍裝,戴著紅袖章的人,高唱著“造反有理”,沖進(jìn)圖書館,清查“封資修”,把許許多多的圖書付之一炬;還讓許多“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掛著牌子跪在那里陪祭。這是當(dāng)年司空見慣的“造反有理”的場(chǎng)面。
真的是“造反有理”嗎?在劉平的《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huì)為視角》一書中,秦寶琦以《“造反有理”辯正(代序)》為題,說(shuō):“歷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都‘有理。”
此書運(yùn)用歷史學(xué)、民俗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綜合分析,明確提出文化層面的結(jié)論:每一次農(nóng)民叛亂都是叛亂者與當(dāng)時(shí)政治環(huán)境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有些農(nóng)民叛亂不一定是階級(jí)矛盾引發(fā)的,宗教異端、社會(huì)習(xí)慣(如宗族械斗等)、民族沖突、土匪活動(dòng)都有可能引發(fā)叛亂。農(nóng)民叛亂廣泛借用了他們所處社會(huì)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或宗教異端思想)。如果說(shu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的話,那么宗教尤其是宗教異端思想同時(shí)也是人民的興奮劑。據(jù)此,作者認(rèn)為對(duì)農(nóng)民叛亂的類型與歷史作用應(yīng)重新做評(píng)價(jià)。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里使用的是“農(nóng)民叛亂”,而不是沿襲經(jīng)典著作中的“農(nóng)民起義”的提法。作者說(shuō):“叛亂”一詞,在建國(guó)以后的國(guó)內(nèi)史學(xué)界研究農(nóng)民反抗問(wèn)題時(shí)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作者引用美國(guó)學(xué)者穆黛安(Dian Murray)的論述,分析區(qū)別了rebelliot(造反、叛亂、反抗之意)與revolt(造反、起義、反叛之意)的不同,選擇了“叛亂”這個(gè)詞,他認(rèn)為:“叛亂”不僅是有遠(yuǎn)大抱負(fù)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還包括有私欲、有野心的首領(lǐng);不僅指稱正義性的農(nóng)民起義,也包括純宗教性起義、盜匪起事、民變、地方騷亂、暴亂等性質(zhì)各異的動(dòng)亂。這就是說(shuō),作者主張對(duì)“農(nóng)民叛亂”做細(xì)致的歷史分析,改變過(guò)去那種籠統(tǒng)的歷史書寫法,改變機(jī)械邏輯的思維,還歷史以原來(lái)的面目。
作者引用馬克思關(guān)于“宗教”的論述,也不同以往。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中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一九八六年錢鍾書先生從文化史的角度,探究了馬克思這一論斷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李伐洛(Rivarol)說(shuō)宗教為法律之補(bǔ)充,又說(shuō)民不聊生,乞靈宗教,以他生稍慰此生。“后一意即費(fèi)爾巴哈所謂下地有窮民則上天有財(cái)神,上帝出于人世之缺陷怨望;亦正如馬克思所謂宗教乃人民對(duì)實(shí)際困苦之抗議,不啻為人民之鴉片。”(《管錐編》,第一冊(cè),21頁(yè))劉平則指出,“宗教尤其是宗教異端思想同時(shí)也是人民的興奮劑”。作者考察了中國(guó)農(nóng)民運(yùn)動(dòng)的歷史,沉重地指出:在中國(guó)漫長(zhǎng)的封建社會(huì),發(fā)生過(guò)無(wú)數(shù)次大大小小的農(nóng)民反抗斗爭(zhēng),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的宗教信仰有關(guān),他們所利用的“宗教”,大多為宗教異端。清代天地會(huì)首領(lǐng)洪大全就承認(rèn)“洪秀全學(xué)有妖術(shù),能與鬼說(shuō)話,……稱為天兄降凡,借此煽惑會(huì)內(nèi)之人,故此入會(huì)者固結(jié)不解”。羅爾綱先生述稱: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春,馮云山被囚,洪秀全回廣州設(shè)法營(yíng)救,拜上帝會(huì)群龍無(wú)首之時(shí),“(楊)秀清就利用當(dāng)?shù)孛孕诺慕低仔g(shù)……厲聲對(duì)眾人說(shuō):‘眾小子聽著,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楊秀清,來(lái)傳圣旨。”從此,在太平天國(guó)高層領(lǐng)導(dǎo)集團(tuán)中出現(xiàn)了兩個(gè)“神仙”化身,一個(gè)是洪秀全“天兄降凡”,一個(gè)是楊秀清“天父降托”。中國(guó)是很重視倫理道德的,天父與天兄,隸屬關(guān)系很清楚。而事實(shí)上洪秀全是領(lǐng)導(dǎo)核心。這就意味著一場(chǎng)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是客觀存在。果然,一八五六年天京內(nèi)訌,“天父”要天王洪秀全封萬(wàn)歲,被天兄降凡的“天王”洪秀全密詔韋昌輝殺死。天京城內(nèi),血流成河。天兵天將由對(duì)神靈的虔誠(chéng)轉(zhuǎn)化為興奮,進(jìn)而衍變?yōu)榀偪瘛奶教靽?guó)的歷史教訓(xùn)中,我們可以理解作者的論述。這些論述,以往是不可以說(shuō),更不可以寫成文字發(fā)表的。
正是為了還歷史以原來(lái)面目,作者以大量的史料闡述了農(nóng)民叛亂與文化的關(guān)系,如他指出:“有些農(nóng)民叛亂也不一定是由于經(jīng)濟(jì)條件和自然條件惡劣引起的”,他援引魏源《圣武記》中臺(tái)灣的情況說(shuō):“臺(tái)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chǎn)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簡(jiǎn),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nèi)賊,朱一貴、林爽文尤其著者也。”朱一貴,福建長(zhǎng)泰人,康熙末移居臺(tái)灣,因知府王珍貪酷,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夏率眾起義,以反清復(fù)明相號(hào)召,稱“大明復(fù)興元帥”,大敗清軍,人數(shù)發(fā)展到三十萬(wàn),占領(lǐng)全臺(tái),被推為中興王,年號(hào)永和。清政府從閩浙調(diào)兵渡海進(jìn)攻,起義軍戰(zhàn)敗,他被俘就義。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遷居臺(tái)灣彰化。農(nóng)民出身,后為彰化天地會(huì)領(lǐng)袖。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秋,官府鎮(zhèn)壓天地會(huì),他率眾起義,攻克彰化,被推為大盟主,年號(hào)順天。旋又克諸羅(今臺(tái)南佳里鎮(zhèn)),鳳山(今高雄),與天地會(huì)首領(lǐng)莊大田合圍臺(tái)灣府城(今臺(tái)南)。清廷派兵鎮(zhèn)壓,起義軍敗清兵于府城南,聲勢(shì)大張。清續(xù)派福康安等率援軍抵臺(tái)。林爽文兵敗逃入山中。后被俘,在北京就義。朱一貴、林爽文從反抗到建立政權(quán),應(yīng)該說(shuō),起義者的政治意圖是第一位的。所以作者主張把農(nóng)民反抗運(yùn)動(dòng)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政府行為,一類是反社會(huì)行為。要做具體分析,不能籠統(tǒng)地沿襲“造反有理”,而掩蓋或模糊了歷史的事實(shí)真相。
(《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huì)為視角》,劉平著,商務(wù)印書館二○○二年十一月版,20.00元)
構(gòu)建學(xué)術(shù)與思想之間的歷史
張仲民
《國(guó)家與學(xué)術(shù):清季民初關(guān)于“國(guó)學(xué)”的思想論爭(zhēng)》一書是羅志田自己對(duì)“清代以及近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與思想演變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從保存國(guó)粹到整理國(guó)故再到不承認(rèn)國(guó)學(xué)是‘學(xué)這一發(fā)展過(guò)程”的一個(gè)基本梳理。這個(gè)梳理“不僅需要沿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進(jìn)行梳理探索,而且應(yīng)該從思想史(有時(shí)甚至包括社會(huì)史)及思想與學(xué)術(shù)互動(dòng)的角度考察分析”、“最后也涉及從社會(huì)史角度考察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怎樣因應(yīng)西方學(xué)術(shù)的沖擊、怎樣調(diào)整和確立自身的學(xué)科認(rèn)同、‘國(guó)學(xué)怎樣為社會(huì)所認(rèn)知以及學(xué)人自身怎樣看待其研究對(duì)象等面相”(上引書,15頁(yè)),本書大概也就是羅志田教授“探索學(xué)術(shù)與思想之間的歷史”和“重寫學(xué)術(shù)史”的嘗試。
綜合起來(lái)看,從保存國(guó)粹到整理國(guó)故再到不承認(rèn)國(guó)學(xué)是“學(xué)”的這個(gè)曲折演化過(guò)程,實(shí)際上也就是“古學(xué)”(或“國(guó)學(xué)”、“國(guó)粹”)由據(jù)以安身立命、天經(jīng)地義的“知識(shí)資源”到“須改用新式機(jī)器發(fā)掘淘汰”的“最富礦藏”(嚴(yán)復(fù)語(yǔ))再到被送進(jìn)“博物院”變?yōu)椤皩W(xué)術(shù)資源”,最后又到“國(guó)學(xué)”的淡出過(guò)程,也正是新的知識(shí)傳統(tǒng)逐漸確立的過(guò)程(實(shí)在也是隨著近代中國(guó)的主要“崇拜”而轉(zhuǎn)移的過(guò)程)。羅志田認(rèn)為這一過(guò)程中最顯著的主線便是“廣義的學(xué)術(shù)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不過(guò),也正是“國(guó)學(xué)”的淡出“進(jìn)一步確立了‘中國(guó)文化這一稱謂的主流地位,此后‘學(xué)術(shù)的含義日漸收縮,昔人思考的‘學(xué)術(shù)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到今天已變?yōu)椤幕c國(guó)家的關(guān)系了”(403頁(yè))。
這本書大概是羅志田目前已出專著中最難讀的一本,初讀起來(lái)會(huì)覺(jué)得作者對(duì)這場(chǎng)清季民初關(guān)于“國(guó)學(xué)”的思想論爭(zhēng)所引的材料太多,論證甚至有點(diǎn)反復(fù)和煩瑣,讓讀者有時(shí)很難索解作者意旨究竟何在。其實(shí),這樣的寫法可能是作者借鑒了陳寅恪論著的寫作風(fēng)格,因?yàn)閺母旧现v,局限于歷史研究者自身“所遭際之時(shí)代,所居住之環(huán)境,所熏染之學(xué)說(shuō)”,以及其可依據(jù)的永遠(yuǎn)不可能被竭澤而漁的材料——“吾人今日可依據(jù)之材料,僅為當(dāng)時(shí)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cè)其全部結(jié)構(gòu)”,那當(dāng)然是不可能,這就使我們對(duì)歷史的認(rèn)知其實(shí)非常有限(當(dāng)然也可能非常過(guò)度)。作者還引用陳寅恪先生之言:“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文章或今或古,或馬或班,皆不必計(jì)也”,提示出陳寅恪先生之所以為此的一個(gè)“重要的考慮”——“即不同史家對(duì)史料的解讀可能相當(dāng)不同,若僅僅引用一二‘關(guān)鍵語(yǔ)句并據(jù)此立論,讀來(lái)更覺(jué)通暢而明晰,但無(wú)意中便使作者對(duì)史料的解讀具有‘壟斷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眾多讀者對(duì)某一具體題目的參與;若將相關(guān)史料較詳盡地排比出來(lái),雖仍有作者的剪裁、處理等傾向性在,到底可以讓讀者有據(jù)史料而判別作者立言是否偏頗的參與余地”(15—16頁(yè)),因而該書“偏重于敘述,引用史料較今日一般論著稍詳,尤其對(duì)不同見解盡量征引”(17頁(yè)),這樣或許可以有“隨人觀玩”的效果,讓讀者擁有更多的詮釋權(quán),回到歷史的“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設(shè)身處地,作者以增進(jìn)對(duì)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認(rèn)識(shí)與理解。同時(shí)也可減少由于引用者的過(guò)度解讀而造成讀者的先入之見,故此,本書的難讀也該是應(yīng)有之義了。不過(guò),也許正是作者這樣“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既重視各方觀念本身的異同,也關(guān)注不同觀念競(jìng)爭(zhēng)的過(guò)程。在處理史料時(shí)盡量平心對(duì)待爭(zhēng)論各方的言論和觀念,給各方以盡可能均等的‘發(fā)言權(quán),希望能重建出一個(gè)比較接近原狀的觀念競(jìng)爭(zhēng)進(jìn)程,以增進(jìn)對(duì)昔人心態(tài)、觀念及時(shí)代關(guān)懷的認(rèn)識(shí)和了解”(15頁(yè)),才向讀者傳達(dá)出“近代中國(guó)多歧互滲的時(shí)代特性”——這一清季民初時(shí)期表現(xiàn)最為明顯的面相。在本書里,作者又挑戰(zhàn)了以往單一的保守與革命對(duì)立的二元敘述模式,避免將歷史人物和事件線條化處理,力圖把當(dāng)初的諸多復(fù)雜面相凸顯出來(lái),使讀者在“悖論”中認(rèn)識(shí)當(dāng)時(shí)的歷史,反過(guò)來(lái),也更好地去理解歷史中的“悖論”。作者這樣的做法無(wú)疑是加強(qiáng)了歷史本就具有的豐富多彩性,“顛覆”了一些人們往常對(duì)那段歷史的清晰明白的認(rèn)知,使歷史變得更為“模糊”,真是“你不說(shuō)我倒明白,你越說(shuō)我倒越糊涂”了。其實(shí)越是清晰的歷史著作越是讓人懷疑,如果我們重建出的史實(shí)是干凈利落,恰可能正好與歷史的實(shí)相相悖,即陳寅恪先生所謂的“言論愈有條理統(tǒng)系,則去古人學(xué)說(shuō)之真相愈遠(yuǎn)”。
既然本書標(biāo)題是“國(guó)家與學(xué)術(shù)”,涉及面應(yīng)該非常之廣,但該書并沒(méi)有花太多力氣在有關(guān)文本之外進(jìn)行社會(huì)學(xué)的分析,對(duì)關(guān)于“國(guó)家與學(xué)術(shù)”的論爭(zhēng)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學(xué)術(shù)史層面展開(這與其《權(quán)勢(shì)轉(zhuǎn)移》等著作是明顯不同的),這可能會(huì)引起一些爭(zhēng)議,但“本書大致是一種介于思想史和學(xué)術(shù)史之間的探索”,作者的主觀目的是在于構(gòu)建學(xué)術(shù)與思想之間的歷史,不是在史學(xué)的大范圍內(nèi)跨越其子學(xué)科如思想史、學(xué)術(shù)史、社會(huì)史來(lái)進(jìn)行的研究。其實(shí),本書也只是作者寫作計(jì)劃中的“外篇”——“主要探討學(xué)術(shù)的思想和社會(huì)語(yǔ)境與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shuō),本書實(shí)際上是一本研究沿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來(lái)探討其演化,從而對(duì)清末民初的學(xué)術(shù)與思想演變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獲得新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學(xué)術(shù)史
(《國(guó)家與學(xué)術(shù):清季民初關(guān)于“國(guó)學(xué)”的思想論爭(zhēng)》,羅志田著,三聯(lián)書店二○○三年一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