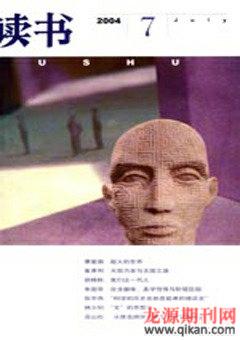大國力量與大國之道
崔勇列
讀到《大國力量的興亡》這本書時,又發現中英語言(甚或中西觀念)之間的一個差別:我無法把great powers這個詞譯成準確的中文。“偉大力量”最貼近字面含義,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超級力量”比較接近實際含義,但又不大符合其字詞定義,也太“現代化”了一點,故暫且譯作“大國力量”。這也使我想起了“霸權主義”一詞。我發現英文中其實沒有完全和其相對應的詞:hegemony或hegemonism在英文中是指一種非均衡的政治支配狀況,特別是在特定政治布局中某一國因其政治和經濟實力之優勢而具有的主導運作的局面,有點像諸國中的秦或三國中的魏。這個詞沒有貶義,更不常用。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霸權主義”大體是指某特定大國完全不顧國際法和國際政治格局現狀一味擴張自身勢力范圍,干涉他國內政,甚至進行武裝侵略和占領的行為,具有強烈的道德意涵。很多情況下,可以干脆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不必用到“霸權主義”。可能是“帝國主義”一詞的二十世紀初意識形態和道德價值色彩過于強烈,使用“霸權主義”在外交和禮儀上更溫和一些,也更現代化一些。想到這里不禁有點悲哀:反對霸權主義是中國外交的主旨之一,但英語世界對這個主旨好像沒有任何感覺,不是我們不努力宣傳,而是卡在語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知上,或者以這種感知來劃分的文化區隔上。
其實,我讀肯尼迪的這本書不是為了弄清“霸權主義”的含義,而是為了進一步探討并比較現代西方史學的方法論問題。嚴格地說,史學作為最古老的社會人文學科之一,也最缺乏明確可辨的方法論體系。歷史學作為幾乎任何現有社會科學之母,如果說還有什么方法論,那么也僅限于發掘、考證、鋪陳和時序性。現代西方史學(大概自湯因比和韋爾斯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試圖建立起一個以“文明”觀為中心,以“力量平衡或制衡”為杠桿的新史學方法論體系。這種方法論體系實際上是步經濟學的后塵,借鑒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的方法論概念。其結果(或者代價)是必須抽取歷史事件和歷史序列中任何得以產生道德結論和映現道德內容的因子,使史學分析對象呈現盡量“道德中性”或不提供道德結論空間的灰色風貌。對我們中國讀書人來說,這是一件難度極大的功課:這種方法論要求我們時時在顯而易見的道德罪惡面前抑制內心的憤怒,要求我們在色彩斑斕的歷史面前假設自己是一個文化色盲,要求我們在苦難深重和挺進凱旋的人類活動面前采取一個滿不在乎的姿態。如何是好呢?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如何是好。譬如,我們也許永遠都無法真實評價“大國”或“強國”的道德價值。“大國”或“強國”——必然地——不是和平國家,而是一個軍事強權。我們如何以這個真實標準來標定我們世世代代的道德夢想呢?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的這本書并非一本嚴格的歷史著作,卻典型地貫穿了這種現代西方史學方法論體系。“大國力量”不同于“大國”,它不僅是幅員和人口的復體。大國力量的形成、擴展、轉型、沒落和消失,都完整體現文明生長的脈絡,體現力量平衡和制衡之間歷史游戲的多變和不確定性。大國力量的形成是最有效運用文明成果的過程,是將文明成果通過社會產能最大限度物化,從而在社會生產和軍事機器規模方面大大凌駕其他國家的過程。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出現或衰落的大國力量,都直接地是軍事力量對抗的結果。但是在更深刻的含義上,它更是各自如何有效地、更建設性地將經濟和社會資源配置在軍事機器上的歷史競賽的結果。一個大國力量不必是某特定文明形態的原始者,但必須是最有效合理并最大限度運用了這個文明的成果者:希臘文明的成果最有效地造就了羅馬帝國;在意大利濫觴的文藝復興卻在法國的啟蒙運動中結出最豐碩的社會果實;在北德和尼德蘭地區萌芽的工業傳統在英倫島上匯集成蓬勃的工業革命大潮;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基地現在似乎在北美大地上;中國文明迄今為止似乎在日本導致了最豐富最精致的物質產出。一個大國力量的興起都同時伴隨著另外一個大國力量衰落。一個特定區域(或國家)在社會生產率和社會產能方面的優勢不僅抵消而且實質上削弱其他國家提高這種優勢的機會,因為一個大國力量會吸引其他地區的資金和社會財富,并以近乎掠奪性和吞噬性的姿態來爭奪稀缺的社會和自然資源,從而阻擋他國走向大國的道路。然而,一旦現有大國力量在保持和促進高度社會生產率和經濟技術增長率方面出現嚴重的歷史失誤,在維持大國地位的游戲中“自廢武功”,就會導致其大國地位的衰落。
大國力量必須在盡量長的時期內維持最根本的技術領域中具有壟斷性的優勢,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其軍事機器和他國相比具有壓倒性的實力。譬如,英國曾長時期內保持了蒸汽機制造技術方面的絕對優勢,并以此支持大噸位軍事艦只組成的強大遠洋艦隊,來維持英帝國在世界范圍內的頭號大國地位。目前美國軍事力量和其世界頭號大國地位也是依靠類似的技術優勢來維持的。一旦這些大國力量不再保持根本技術體系中的絕對優勢,其大國地位就會產生動搖。當然,大國力量地位的形成和維持不單取決于技術領域中的絕對優勢,而且也取決于以這種優勢來帶動的綜合社會生產率和產能,以及保證這二者的制度性因素。這種軍事機器和戰爭—社會生產率—社會組織改革之間鏈環作用的模式,使得一個大國力量一旦形成,就能夠在很長時期內都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這個地位。
當然,肯尼迪特別小心地指出,社會生產的配置和軍事機器之間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均衡關系,否則會大量消耗資源,從而失去維持或爭取大國地位的競爭力。德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國曾兩度試圖崛起成為世界大國,它擁有令人贊羨的制造業傳統和有效率的工藝體系。但是,德國并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它沒有足以控制世界性資源的能力,不具有某一特定關鍵技術領域中無可替代的絕對優勢,和他國相比也沒有絕對突出的社會產能,沒有創新性的社會組織和改革的風氣,令軍事機器失去資源和社會結構的支撐,導致德國兩次歷史性“叩門”的挑戰均以失敗告終。日本的情形也很類似德國。而俄國之所以能夠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崛起成為世界性大國力量,在肯尼迪看來,則是受惠于四個因素:一、在斯大林時代形成的驚人的工業產出或產量能力;二、控制了極其豐富且足以支持持久戰爭的資源;三、具有雖原始卻極其有效的社會民眾和社會資源動員系統(社會組織因素);四、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足以和美國相抗衡的技術開發能力和幾近絕對的軍事技術優勢。而俄國最終的淪落,也是因為步德國的后塵,在社會生產結構和資源配置模式根本沒有盈利和積累能力的失衡條件下,軍事機器卻過于龐大。簡而言之,缺乏武裝的和平國家和軍事壓倒一切的軍國主義國家都不可能成為大國力量。
軍事機器當然是要用于戰爭,但是在十六世紀后的歐洲政治史上,軍事機器在維持和平方面發揮的作用幾乎和它策動戰爭的作用一樣重要。軍事機器首先形成政治威懾,促成恐怖平衡和強制性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當一個大國力量完整形成后,其無可替代的實力保證他國不敢輕易發動針對大國或針對大國利益的戰爭,這樣就可以維持很長歷史時期內的國際和平。這個時期內的大多數戰爭都發生在大國和小國之間或小國之間,因此戰爭持續時間和規模烈度都不大,不致大幅改變國際政治格局。羅馬帝國時期的歐亞大陸和大英帝國時期的歐洲均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所有大規模的戰爭幾乎都發生在某個大國力量趨于衰落而另外一個或一些大國力量開始崛起的歷史交替時期。在這個交替期內大國力量壓倒性軍事優勢逐漸瓦解,維持政治恐怖平衡的能力也趨衰減,因此其他一些國家便試圖替代這個大國力量的地位。這時便會引發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和軍事沖突。羅馬帝國崩解后歐洲長期無法出現政治強權的局面,促使奧斯曼帝國向歐洲地區擴張;大英帝國趨于衰落后的二十世紀初期開始,更是爆發了兩場世界大戰,直到歐洲大陸形成冷戰時期恐怖政治平衡為止。
肯尼迪坦承,他的大國理論和十九世紀德國著名政治學家列奧波德·馮·蘭克(Loepold von Ranke)的大國理論一樣,是“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為基點的。為什么文化稟賦并不大深厚的歐洲人民能夠制造出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大國力量呢?肯尼迪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永遠都難以全面回答。經濟和技術進步方面的優勢,加上社會結構、地理位置和一些模糊的偶發因素顯然是最可能的答案。但是,在肯尼迪看來,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和其他文明相比歐洲地區特有的“政治零散化”現象。雖然出現過龐大的羅馬帝國以及后來西歐的查理曼帝國,中歐的哈布斯堡帝國(源自神圣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王室的聯姻)以及東歐的基輔俄羅斯帝國等較小的統一帝國,歐洲大陸實際上一直處于在政治上零散化的狀態,沒有經歷過諸如中國等東方帝國特有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模式。歐洲地理位置上也顯得零散且多元化:沒有尼羅河、底格里斯河、伏爾加河、長江、黃河等大型河流沖積而成的肥沃流域養成一個形態上相對統一的文明;沒有遼闊的平坦地勢供皇家騎兵無遠弗界,縱行無阻;也沒有廣大平原地帶供易于政治統制的大群農民生息繁衍。歐洲的地理氣候差異極大,被一些小型的河流,零碎的盆地平原,縱橫交錯的山嶺,犬牙交錯且殘碎不規則的海灣海峽切割成無數個自成一統的地理碎片。這種地理形態造就了歐洲大陸無數個非中央集權式的地方力量、地方王國和公國、采邑封侯區和城邦國家。這些地方自治體結構松散,并非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羅馬帝國以后的歐洲政治地圖看起來簡直像一條“百衲被”。這種政治地理特征使得歐洲一直得以保持多種文化和語言共存的局面,以及多種語言文化相互競爭、相互交融、相互吸納,也相互正視、容忍和尊重的傳統。這種局面和傳統促進了一個極其重要卻往往為人忽視的重大結果:文化機體在相互競爭和相互交融吸納中保持生機活性和創新動力,也產生文獻翻譯和交流等蓬勃的學術活動需要。在歐洲,其實任何一個重大的文化現象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僅僅局限于特定區域之內:最具有“歐洲價值”,而且被推崇為近代歐洲文明最顯著外在特征的哥特式建筑風格于十二世紀初出現于法國北部后,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內甚至沒有擴及到比利牛斯半島南部和亞平寧半島等南歐地區;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后馬丁·路德新教在一百多年內都是德國中南部地區的區域性信仰;文藝復興運動基本也沒有走出過意大利。而這些在特定文化區域內發軔的文化革新運動一旦得以和其他區域進行交流,就立刻移植成變形文化亞種:哥特式建筑風格啟發了巴洛克建筑風格并促進了歐洲的劇場藝術;路德教啟發了茲翁利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甚至英國的國教改革和清教徒運動,而且因圣經翻譯而豐富了德語和其他日耳曼語系語言,為后來德國文學勃興奠定基礎;文藝復興運動則啟發了尼德蘭和西班牙兩地的繪畫革命,以及后來以人文主義為主要訴求的法國啟蒙運動。如果歐洲一直存續著羅馬帝國式的大型中央帝國,則歐洲可能只會存在一個拉丁語,一個只能被帝國中央認可的文化標準體系即羅馬天主教,以及一個形體龐大卻毫無生氣僵硬古板的文化古店。
歐洲的地理形態和政治分理自治形態使得主要社會資源的配置不是以貢賦和其他符合中央政權意志的非商業手段,而是依靠各個地方自治體之間頻繁的平等商業貿易來達成。由于地形復雜多元,貿易形式也必須多樣化,河流貿易、海上貿易、陸海兩棲貿易、森林沿界貿易、公路貿易、轉口貿易等多種貿易形式不一而足。而且由于多樣化貿易形式的需要,貨幣支付、貨幣兌換和資本信用手段也必須多元化,從而催發現代銀行體系和貨幣兌換系統。多元化的貿易和交流關系也必須通過法律調節手段來解決,從而產生極其豐富的民法體系和普遍的法意識傳統。較大型的中央王國的財稅收入絕大多數來自地方自治體,因此必須對其加以懷柔政策,不能進行政治強制(中央政權大多通過聯姻來維系和地方自治體之間的政治關系)。這些中央王國都不是集權式的,而是被諸侯架空的弱勢政治實體。這也造成了歐洲文化極其特殊的現象,即幾乎沒有民族主義意識內容。一個弱勢的中央王國沒有足夠的政治號召力或動員力,也沒有文化強制的能力來造就一個強迫廣大地域內社會民眾接受的統一文化標識體系。羅馬教廷曾試圖做到這一點,但是被歐洲特殊政治地理風土所自然促發的社會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所瓦解。這種歐洲政治地理模式的社會運作結果是:多元化,持續不輟,由法理調節,由復雜的貨幣支付和貨幣兌換手段支持的貿易刺激空前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其中包括軍事技術的進步),大大擴充社會產能;政治分權分治保持歐洲地區長時期的政治勢力均衡;文化語言多元化也促進更廣泛的文化交流,意識競爭和意識自由,引發不間斷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革新運動,從而形成世界歷史上無出其右的強大的歐洲文明。所有這些因素之間相互結合,在某一時點上就會導致一個突破。在這些分治的地方實體中,哪一個能更多地利用貿易利益和貿易盈余來積累更多資金,更能利用貿易優勢來擴大生產規模,更能利用技術進步來加強軍事機器,更能利用文化革新和文化運動優勢來爭取他國知識界認同,它就可以崛起成為一個大國力量。
一八一五年以后的一個世紀內,世界幾乎沒有發生過大型的世界性戰爭。在這個時期內,歐洲大陸幾乎沒有一個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大國力量。歐洲長期維持了一個罕見的政治力量均衡局面,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實力來打破這個局面。未來的大國美國和俄國都忙于在各自所處的大陸中擴展版圖,沒有余力卷入現成的歐洲大國政治游戲。這個局面使英國得以長期維持了世界性大國的地位。而美俄兩國擴展版圖的歷史進程幾乎完成之后,就立刻開始卷入成為世界主導性大國的爭斗中。拿破侖法國、德國和日本的不幸在于他們在錯誤的歷史時刻,即在英國、美國和俄國試圖成為世界大國時不識時務地“出來搗亂”。一八一五年以后的一個世紀(或整個十九世紀)是西方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均衡靜止時期。西方史學家有人將其稱為“黃金時期”(不過中國史學界則對此嗤之以鼻)。所謂“黃金時期”論看來是言過其實。十九世紀只是“暴風驟雨”的前夜。這個時期里,歐洲數百年來所形成的現代西方文明正在釀制成一個前所未有的物質成果,一系列深刻文化意識革命正在促成持續不斷的革命和動亂,一系列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成就正在塑造幾個潛在的軍事巨人。正是在十九世紀,羅馬帝國以來歐洲靜止的政治社會版圖開始劇烈地震動,地方自治和政治分權讓位于能更多掌握資源的中央集權。拿破侖法國,俾斯麥普魯士,統一意大利國,奧匈帝國等中央集權政府紛紛出現。在經過十九世紀深刻的歷史釀制過程后,歐洲便進入了巨變的二十世紀。這些歐洲中央集權終于相互猛烈沖撞,歐洲地區保持了七八百年的美妙政治經濟均衡終于被打破。一般地說,世界在一個大國力量升起和存在時期最為和平也最為安全,在這個大國沒落和新大國興起時期最不和平也最充滿戰爭危險。國際和平的真正含義就是對大國力量的尊重和敬畏,以及由此形成的恐怖國際政治均衡。
最近肯尼迪撰文認為,一些大型的歐洲國家如英、德、法等國,意識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取得這種支配性的大國地位,故而必須通過合作,建造一個統一國家來分沾大國力量的歷史榮耀。在他看來,歐盟實際上是羅馬帝國夢想的現代版,也是二十世紀歐洲中央集權在歷史沖撞后相互妥協的權宜聯盟,只是這個聯盟強加了一個歐洲共同民族國家的虛幻目標。然而,這個歐洲大國夢想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其一貫的世界主義導向,對世界事務的野心遠遠沒有羅馬時期盛大,對自身世界領導地位的疑慮從一開始就深植在其大國設計方案中。歐盟是一個注定要破滅的大國夢,它無視歐洲社會深刻的政治分權、地方自治、文化語言多元化傳統,以及在經濟上以“小國開放模式”為主、貨幣支付手段和銀行信用體系多樣化的歷史特色,試圖造就一個拋卻這一切歷史要素和歷史材料而在一旁平地而起的人工帝國。歐洲社會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在十九世紀與大國升起和淪落運動相伴而生的社會主義理念在伸張人道化社會的同時,卻基本摧毀了歐洲社會最強大的一個歷史支柱,即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精神。歐洲社會已經沒有崇尚和尊奉自由競爭理念的社會風土,缺乏通過自由貿易盈余和貿易利益來積累資金的能力,缺乏資本主義工業體系高度的社會生產率和強大的產出率,缺乏植根于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之中的工藝、技術和社會組織革新的歷史動力,缺乏由強大社會產出和技術體系優勢來支撐的有效軍事機器,因此它不可能替代幾乎具備所有上述優勢的美國的世界大國地位。
美國是一個時常令人痛恨和不齒卻又不容否認的真正大國力量。它繼承了歐洲地理社會遺留的全部遺產,按照流行的說法,就是精華和糟粕都一古腦兒攬過去了。美國是歷史上最大的工業化和物量化國家,任何一個產品都必須具有驚人的“工業產量”形式才可以去參與競爭。世界上每十盒卷煙中就有一盒萬寶路煙,每十二瓶啤酒中就有一瓶百威啤酒。我曾參觀過百威啤酒廠設在堪薩斯州的一個酵酒池,長達近十五公里,而世界上大多數啤酒廠的酵酒池大多只有一個標準游泳池那么大,小一點的像一個澡池。在美國,每一個精神意識現象也都必須大物量化才能不致湮滅:一個著名歌手的碟片動輒就有數億美元的銷售額,好萊塢一部電影的市價要超過世界許多國家的年國民總產值。不管是什么東西,質量好壞精致與否先不論,這個國家就是有一個世界其他國家沒有的社會生產機制,超大量地生產,超大量地消費。最快最有效地生產出大多數人都能花費得起也扔得起的產品和勞務,這就是美國。數十萬元一頓的年夜飯,數十萬元一盆的蘭花,黃金包裝價值連城的月餅,美國大概永遠都不會有。有的只是人不分高低貴賤都可狼吞虎咽,標準工廠零件般大量生產的漢堡包。只要是“東西”,就被“生產”,而非精工細作地“打造”。法國人的揶揄,德國人的不服,日本人的不屑,其他人的指手畫腳戳脊梁骨,美國人就是改不了這個德性。可是,這就是今天真真確確的大國之道。肯尼迪認為,這種社會生產機制要求美國有一個他國不能望其項背的生產率。只要美國能保持這種社會生產率,技術革新和技術壟斷,社會自由和不斷創新改革的社會活性這三個要素,它的大國力量地位就不易被替代。
在這本書中肯尼迪也分析了中國明朝的實例。在他看來,按照外在規模,明朝是當時(約十四世紀)的世界頭號大國,無論在人口、疆域、社會生產產能和技術領先度以及文化成熟度方面均大大超過當時的歐洲。肯尼迪特別贊賞當時中國的官僚制度,官員們都受過完整的教育,經歷過政治競爭和管理社會事務的訓練。政治組織動員和配置資源方面(譬如賑濟自然災害方面)具有特別突出的功效。鄭和船隊下南洋絕非一般的貿易活動,而是一個大國力量尋求世界性定位的嘗試。但是,中國在此時卻處于類似羅馬帝國的歷史環境之中:周邊地區文化相對落后的蠻族不斷對中心文明展開圍攻,北方異族不斷侵襲中原,倭人騷擾中國沿海地帶和長江下游地區,以致中國的當務之急和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不是追求世界性地位,而是維護國家現有版圖內社會結構的穩定和安全。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版圖擴張的行動,即向安南(今越南)的擴張也被證明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得不償失。這使得明朝幾乎完全放棄了向世界開放的計劃。哥倫布船隊開啟了世界地理大發明和西方文明大擴張的時代,而時間更早,船隊更龐大,航海技術更先進的鄭和船隊只是在沿途留下了幾個供后人憑吊的碎瓷片。肯尼迪的這個觀點,是典型的“外來和尚念經”,不是念給中國人聽的,有點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如果把他搬弄皮毛的淺薄先放在一邊,僅只觀察他得出結論的方法(也是典型的西方史學方法論),還是體味到一點旁觀者清的新鮮感。在多少年以后,中國又啟動了走向世界性大國的步伐。我們躬逢其盛。但是,中國要成為的這個“大國”最終可能不是我們現在所聲稱、所設計、所設想或想要成為的樣子。我們不能在“大國力量”和“強權”之間選擇其一,做“大國力量”而拒做“強權”。這兩者本是二面一體,要么兩者皆是,要么兩者皆不是。如何做一個真正的“大國”,又做一個真正的“大國力量”呢?大國有道,何之為道?既存之道,何以避乎?現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還不晚。
二○○三年春節于舊金山北郊肯特菲爾德鎮
(《大國力量的興亡》,保羅·肯尼迪,蘭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Random House,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