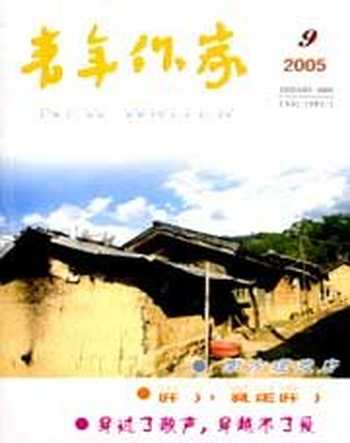我寫故我在
唐仲清
笛卡爾曾說:“我思故我在”。竊以為,笛氏所謂的思如果就只是沉思默想,在我看來意思不大。正如普列漢諾夫那句名言:“沒有用語言表達的思想,其本身也模糊的思想。”依我之見,“我寫故我在”要比“我思故我在”更有意義。正所謂:“寫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寫則殆矣”。
用我本人說事兒,我寫故我在之道理如下:
竊以為,寫作是消磨時間的最佳方式。據吾人之觀察,世上絕大多數消磨時間的樣態都沒有工作成果。麻將連打一星期,一個個牌友疲憊得變了形,稀里嘩啦,麻將收進盒子,人呢,空空而來,空空而去,例子太多,恕不詳表。唯有寫作消磨時間后還有工作成果,君不聞,某退休老干部每天只用三小時手抄《紅樓夢》,抄本已被估價為85萬元,該退休老干部堅持其抄寫行為實乃娛樂;其余時間還要打太極拳、唱京劇、下象棋;可惜,拳劇棋三項連一分錢都不值。
寫作也是一項愉悅身心的活動。鄙人對人們熱衷的一切娛樂從不染指,電子游戲麻將字牌稍稍復雜的項目都不會,只會打撲克爭上游,但也沒甚興趣;鄙人遠離娛樂活動的原因有二:拒絕學習所以不會;以為這些娛樂一點兒也不樂,竊以為,許多娛樂其實就是一套游戲規則不斷重復,正如賭博的真正樂趣并非來自游戲而是來自輸贏;寫作要有樂趣,非得創新不可。前述退休老干部如把手抄《紅樓夢》改為創作《紅樓夢》,那他享受到的愉悅決不止于85萬元手工費。對我本人而言,一切文體運動皆無,寫作便是我唯一的體力勞動;寫作讓我得到延續生命必需的最起碼的體育鍛煉。當然,寫作集體育、智育和娛樂為一體,是其他單純體育運動無法比擬的。
寫作讓我獲得守財奴的快感。巴爾扎克小說里的葛朗臺以清點財產賬目聆聽金幣響聲為樂趣;吾人則以碼字數目增長為幸福,十萬百萬千萬,寫上一億個字的人就是億萬富翁。每每夜靜更深,吾人在萬籟俱寂中用眼看用手摸歷年所寫下的“作品”,第一千次心算咱已經寫了多少萬字,自我感覺像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