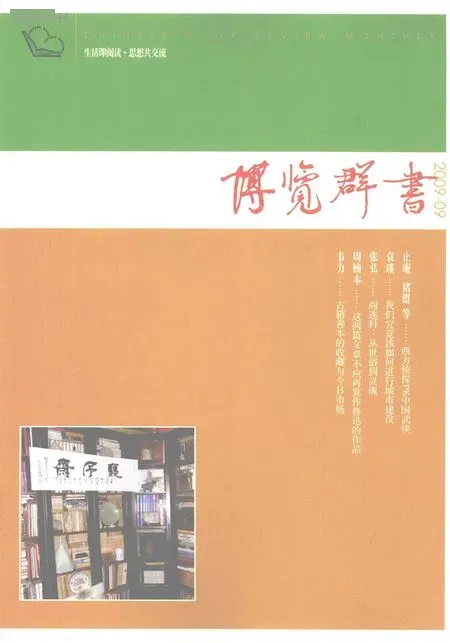理解父親
常遠志
有人雖已去世,可仍然活著。父親的人品,他誠心誠意所做的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事,一些人是永存心底的。這見諸于他們的所言所寫。我逐漸明白,自己對于父親,實在是太不了解了。
然而,隨著時光流逝,父親離去的日子愈久,他的音容反倒愈加鮮明地經常浮現在眼前;一些過去不以為然的小事,也愈讓我看到其中的價值。
我一直以為,從童年到成人,很少享受到父愛。我們見面少,說話就更少。他一年到頭值夜班,我早晨去上學時,他才睡下不久;及至放學,他又上班去了。父親對我是嚴厲的,嚴厲到使我覺得,他對子女是不公平的。我甚至下過決心,不在他跟前說話。因為,似乎在父親眼中,我開口便錯,說的話都有毛病。然而,有一次卻出乎我的意料。大概是上初一時,班主任家訪,偶然遇到了父親,用學生的話說,還是“告了狀”。后來我聽說,父親對老師說我看閑書一事發表看法,說,看幾本閑書,也沒有什么壞處。這對我的精神簡直是一次解放——大人們的意見并不都是一致的;老師也有不對之處,而父親也有贊同我的地方!此后,還有一些事情,他的態度也讓我感到,自己有某種自主選擇的自由。
我對父親的“學問”,常常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幾乎從未過問過我的學習。有時候,我也問過他一些政治名詞,他卻很少給過我明確的回答。當時,我總以為,不是我聽不懂,而是他說不出。現在,我十分感激父親,正是他的這種態度,使我很早就有了尋根究底的“毛病”,使我漸漸懂得,能出口成章的人并非都是有真知灼見的人;世上并沒有那種事事明白的人;而僅僅以所謂定義示人真理,其結果往往使人走向謬誤。
我還要感激父親的是,他給了我一種“平民精神”。父親的“官兒”,可說是不大不小吧,可是,我從小在心靈深處,就以自己雖是干部子弟,卻不以干部子弟為榮而自是。我看不慣那些坐小汽車上學的“公子”、“小姐”們。我常常愿意到大人是拉排子車、蹬三輪車的同學家玩。我覺得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比我聰明,比我知道的事兒多。記得有一次,有人說起父親不該不送我們去干部子弟學校讀書,父親又嚴厲起來,說:“我就是不讓他們上干部子弟學校。”“十年動亂”結束后,我有一次半開玩笑地提起,父親的孫兒還沒坐過小汽車呢!誰知,父親大動肝火,說:“你就死了這條心吧,我是決不會讓他坐的。”當時,我對老人急不擇言的態度覺得有些好笑,但是后來,我愈來愈明白父親的心。父親惱怒的是封建遺毒所造成的社會上種種新的不平等。父親不能容忍用這種不平等去污染孫兒純潔的心靈。如是,孫兒幾乎一次也沒有坐過爺爺的小車。我感激父親,他把平等精神留給了我和我的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爺爺雖然住在部長樓里,卻是一位普通人。
父親從未憑借他的身份幫過兒子什么忙,但為那些他認為需要幫助的人,他常常是不遺余力的。父親待人的“規矩”是,視其是否需要幫助、應該幫助,而不論高下貧富親疏遠近。
我還要感激父親的是,他給我一個榜樣:清白做人,認真做事;辦報就是要多想讀者,讓他們喜歡看。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父親是一個真正的報人。
我和父親接觸最多、講話最多的日子,是“文革”中幫父親寫過關檢查的那幾個月。“文革”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于這場“浩劫”,我們每個人都有應負之責。因為一切都是在神圣的名義下進行的;許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曾害人甚至誤國。這就是“十年浩劫”的悲劇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防止這場悲劇重演的關鍵在于使大多數人認識到自己對于造成悲劇所應負之責。
我感到,父親直到離開人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就在去世的前兩三天,父親忽然變得異常清醒和激動。在夜深人靜時,他對我說:“我是堅信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一定要實現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是四個現代化,恐怕也不是一代二代人就能實現的。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雖然犯有很多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有嚴重的錯誤……”從父親臨終前的遺言中,我看到了一個正直的、誠實的、至死追求真理的偉大的靈魂。
無可諱言,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父親是誠心誠意擁護的,他天真地希望,通過這場“革命”的烈火,真的能夠“蕩滌一切污泥濁水”,使自己變得更純粹,把中國推向前進。在父親“垮臺”前,我曾經“怨恨”過他。因為,他不曾像有的“高干”那樣,給子女以指點,或者以自己的“權勢”,使其更方便地“革命”,或者以自己的“靈通”,使其及早抽身。在父親頭腦中,確確實實沒有那些“封妻蔭子”的封建意識。正因為如此,他不可能與那些野心家、陰謀家同流合污。動亂初起,他不過真心“革命”了二三個月,便被打成了“反革命”!
無數的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無數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竟然還去承認、認識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父親至死都以此為深恥——一位當了二三十年報紙總編輯的黨的新聞工作者竟然答應我——對他的政治思想和經歷幾乎一無所知,剛剛涉世的青年為他寫“檢查”,關涉他的信仰、人格和政治生命的“檢查”。
往事不堪回首。我必須說,對于父親的“檢查”,我是有責任的。記得開始時,我僅僅是替父親抄他寫的檢查,后來,我看父親實在寫不下去,更覺得那樣檢查也實在過不了關,就想替他代筆。我自然想寫得讓他過得了關。可想而知,我所依憑的無非是“造反派”的一套。記得當我用那樣的邏輯推論他思想的來龍去脈,“幫助”他承認強加于他的種種罪名時,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沉默之后,大發雷霆,表示不再寫下去。可是,最后,父親還是“寫”下去了。我是主張父親無論如何要寫下去的,最大理由是,父親不為自己,也該為自己的兒女想想!父親是否是因此“屈服”的,我不能妄加揣測。但是,我從父親后來的態度中感知,他厭惡那種只知為家的自私,憎恨那種不能保持操守的怯懦。
我對不起父親。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我在父親最困難之際,非但沒有給他為維護自己人格尊嚴的抗爭以支持,反而以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社會進步最具破壞力的說辭給了父親致命的一擊。對于我“逼迫”他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父親至死也沒有原諒我,我更不能原諒自己給父親造成的莫大傷害。同樣,他也無法原諒自己,認為這是人格的喪失,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這件事像一座大山橫亙在我們父子的心上。父親晚年多次長時間住院,大部分夜晚,我都陪伴在旁,多少次我都有搬開這大山,重新溝通父子之情的愿望和表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但直到父親去世,我們都沒能做到。我深深地感到,父親的靈魂所受的傷害那么深重,永難愈合。這也是我心中永遠滴血的傷口,讓我永遠無法忘記這些黑暗和恥辱,而去努力爭取內心和世間的光明。
我感到,父親在“文革”之后,內心深處有一種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強烈愿望。可惜,“文革”損毀了他的身體,他無力實現自己的愿望了。在他臨終前半年,適逢舉行《晉綏日報》紀念活動,請他寫文章。父親作為《晉綏日報》的負責人,作為當年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的在場者,卻難以下筆。及至請原來報社的老同志代筆成文后,他又不同意。其原因,我問過父親,他沒有正面回答,但那意思是清楚的:不對自己的思想給以重新的反省,不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給以重新的認識,就不能對《晉綏日報》的歷史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然而,父親已經沒有精力和時間來完成他的反思了,這也是父親最痛苦的事,他就是帶著諸般痛苦遺憾離開人世的。
父親,現在我對您講:我決心做您打算做,而未能做完的事: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為中國今后的進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這就是您希望于我的。我當盡力做下去。
安息吧,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