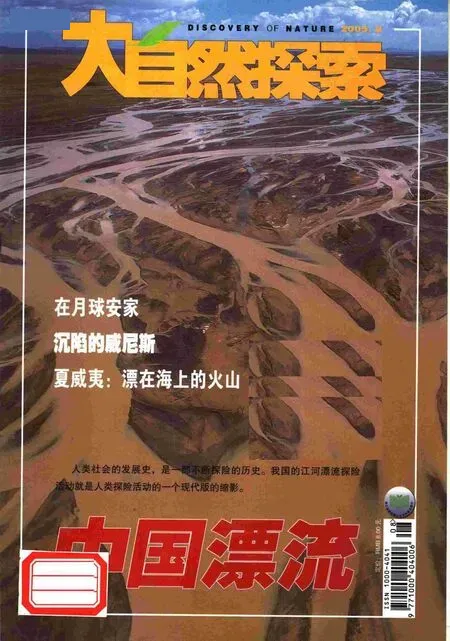寄生植物技高一籌
楊 斧
說到寄生植物,人們往往有些成見,甚至對其產生某種憎惡,從人類社會的倫理觀出發,蔑視地稱它們為不勞而獲的“吸血鬼”或用第三只手盜取他人財物的“竊賊”。但是,如果從生物演化發展的觀點看待這些高等植物中的異類,就會發現它們的許多“惡習”其實是保證自身物種生存繁衍的精彩絕招,與那些“循規蹈矩”的正常植物相比,它們的生存謀略往往更勝一籌。
世界花王——“精兵簡政”,一鳴驚人
在全世界近30萬種具有開花結果特性的被子植物中,有大約3000種靠寄生方式生活,其中最令人注目的種類,當屬有“世界花王”之稱的大王花(或稱大草花)。
1818年,英國博物學家詹姆斯·阿諾德和萊佛士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熱帶叢林中發現了這種雍容華貴、直徑達90多厘米、重達7公斤左右的巨花。自此以后,生物學家就對它的生活方式進行了長期的觀察和研究。他們驚奇地發現,這種令全世界所有有花植物自愧弗如的花王,竟然是根、莖、葉等高等植物常規的營養器官一概皆無。通常情況下,綠色植物如果沒有最引以為榮的“綠色工廠”——葉片,沒有為適應復雜多變的陸生環境而演化出的根和莖,就等于失去了自養高等植物生存的基礎。但大王花卻具有植物界中進化水平最高的類群——被子植物完善的生殖器官——花和果實,一代一代繁衍自如,體現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種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遺傳信息的保存和傳遞。
那么大王花生存所需物質又是如何獲得的呢?難道它也像動物或真菌那樣靠異養方式生活?一點不假,大王花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異養生物,它的一生中保證開花結果所需營養物質供應的器官只有一種——吸器。這種吸器兼攝取、運輸、加工食物和水分、固著花朵等數職于一身。這種精簡機構后脫穎而出的高效率的特殊器官,人們平時是見不到的。當大王花的種子在寄主植物崖爬藤接近地面的莖上一萌發,吸器就產生了,并直指寄主莖中的運輸線——維管組織,最終深入到運送水分及無機鹽的導管和運輸有機營養物質的篩管細胞中,令其中運輸的物質改道,供自己的花朵萌發所需。
在數個吸器的給養供應和支持下,從寄主身上生出的大王花花蕾終于綻開五六枚肥厚的點綴有白色斑點的紅色花瓣,開始完成傳宗接代的神圣使命。真可謂“精兵簡政”,一鳴驚人,大王花的生存技巧不能說不高。
魔王絲線——有根起家,無根發家
大王花可以說是寄生植物中最徹底的改革者。其他寄生者雖然都擁有從寄主身上竊取生活物質的特化器官——吸器,卻往往還是有些留戀以往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成為階段性的寄生者或半寄生者。它們各以其獨特的高招,成功完成了生存繁衍的歷程,表現出了生物進化中形成的生物學特性上的多樣性。
菟絲子是最具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寄生植物,早在《詩經》中就以“唐”這個名稱出了名,以后人們又根據它的特征稱其為赤網、金線草、無根藤、無根草、無娘藤等。在中藥典籍的鼻祖——《神農本草經》中,菟絲子位居上品,歷代醫家多視其種子為補肝腎、益精髓、明目的良藥。包括大詩人李白在內的不少文人則以其無根且爛漫、柔弱卻連綿而產生遐想,賦詩詠之。由此菟絲子的身上似乎也帶有了幾分仙氣。但對于寄主植物來說,菟絲子卻是一種肆虐的魔草。
菟絲子的一生雖然并不長久,卻忽忽悠悠讓人難以捉摸。春天,在萬物復蘇的田野或作物剛剛萌發、尚未進入旺盛生長期的農田中,菟絲子所特有的沒有絲毫綠葉、宛如金絲的形象蹤跡全無。盛夏時節,當持續的高溫和一場場降雨令草木蔥蘢、農田中豆類作物茁壯成長時,菟絲子就如幽靈一般突然出現了。很快,一縷縷、一團團金黃色的菟絲子莖在菊科、豆科等植物的綠色莖葉上自由自在地纏繞附著。它們沒有根基,猶如神兵天降,也似乎與大地無緣。沒有根的菟絲子,它的莖來自何方?難道它也和大王花一樣,種子直接在寄主體內或身上萌發?植物學家的觀察和研究結果否定了菟絲子終生無根而與大地絕緣的觀點。其實,“無根藤”也是在大地母親的懷抱中長大的。每當春夏之際,菟絲子的種子便在田野中萌發了。開始它也像其他正常植物一樣首先向泥土中伸出根系,以便從中得到生長所需的水分和無機鹽,然后向地面上伸出細嫩的莖,開始搜尋適于寄生的對象。此時菟絲子的行動謹慎,在沒有遇到寄主之前決不迅速生長,以免生活物質入不敷出而夭折。一旦遇到較稱心的寄主后,菟絲子的莖便迅速纏繞上去,同時莖表皮細胞開始向寄主莖的方向延伸,形成指狀突起,并逐漸穿過其表皮、皮層,直達運輸大動脈——維管組織,開始了“吸血”的寄生生活。既然已憑借新生的營養器官——吸器在寄主身上站穩腳跟,吃喝不愁,于是分布在土壤中的傳統營養器官根系便自然死去,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無根藤”。
在氣候適宜、寄主充足的條件下,菟絲子生長十分迅速,每天莖可伸長10厘米左右,而且極易分枝,用不了十天半個月,一片原本翠綠可人的草地或豆子地,就會被致密的金絲網一樣的菟絲子莖罩在下面。在菟絲子旺盛生長的同時,遭吸器掠奪的寄主植物卻日漸憔悴,盡管它們的根系拼命地從土壤中吸收水分和無機鹽,綠葉在通過光合作用不斷合成有機物質,但它們卻入不敷出,不得不忍饑挨餓,輕者生長發育不良,重者往往沒等到開花結果就死去,而菟絲子卻花豐果盛,一派繁榮。
世界上共有170余種菟絲子,都有類似的寄生生活經歷,一旦侵入農田將作物視為寄主,往往成為惡性雜草。菟絲子在北美洲尤其猖獗,被農民稱為“魔王的絲線”。而它們“有根起家,無根發家”的生存訣竅。正是其魔力所在。
森林金枝——高居樹上練絕活
桑寄生科是被子植物中最大的寄生植物家族,有大約1300個成員。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半寄生性的灌木,雖然具有能進行光合作用的綠葉和與正常植物差不多的莖,卻沒有著生于土壤中的根系,只靠吸器從寄主體內劫取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無機鹽,并附著在寄主樹木身上,終生過“空中生活”。
由于桑寄生科中有許多與人類關系頗為密切的種類,所以自古以來名氣就很大。在中國,人們很早就利用桑寄生、紅花寄生、松寄生等人藥,醫治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在歐洲,由于人們對槲樹(又俗稱橡樹、櫟樹)的崇拜和喜愛,使寄生在這類樹木上的槲寄生也身價倍增,被尊為“金枝”,認為它具有神圣的權力,可以決定圣林(由槲樹組成)守護者——“林中之王”的生死。基督教在歐洲興起后,槲寄生還被用作裝飾圣誕節的圣物,人人可以親吻站在槲寄生下的人。
在西方,菟絲子被視為“魔王的絲線”,人們對它充滿憎惡,但對于槲寄生,雖然同樣是寄生植物,人們卻奉之為神靈。其實,不論是大名鼎鼎的槲寄生。還足許多默默無聞的桑寄生科其他種類,只要開始過寄生生活就會對寄主樹木產生一定的傷害。盡管它們并非像大王花和菟絲子那樣“魚與熊掌都要”,所劫取的只是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無機鹽,但也時常令寄主難以
應付,輕者生長發育不良,重者甚至被置于死地。據統計,世界上由桑寄生科植物造成的林木和果樹損失十分巨大,例如在北美洲每年有2000萬立方米的木纖維被這類寄生者“喝”掉,在澳大利亞闊葉樹槲寄生奪走了桉樹林木材產量的一半。
可能有人會司:這類與寄主樹木相比弱小得多的灌木,是如何在高大的喬木身上爭得水分分流權的甲一些研究者認為,一棟參天的大樹所以能將根系吸收的水分輸送到包括樹冠頂部的全身各處,主要靠蒸騰作用產生的“拉力”,蒸騰速度越快,產生的拉力也越大。因此,桑寄生科植物要想從寄主身上掠奪水分,必須有更大的蒸騰速度。科學家已經證明,桑寄生科植物的蒸騰速度普遍大于寄主植物,有些種類甚至可以達到寄主的10倍。看來,面對貌似弱小卻內力十足的對手,寄主樹木丟掉控制水分流向的“權利”,是必然的結局。
槲寄生種子靠鳥類傳播,這種巧借外力為自己的種子得到安身立命場所的傳播方式,在桑寄生科中十分普遍。但有些桑寄生科植物卻可以不靠外援,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散布種子。在北美洲很常見的矮槲寄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可以通過果實炸裂時產生的推力將種子以每小時100公里的速度射出15米遠。這種射擊速度,使矮槲寄生種子當之無愧地成為植物界中飛行速度最快的“子彈”。
在北溫帶,我們見到的桑寄生科植物往往有自己個性化的葉片形態,與寄主的葉片大相徑庭。這種特性對它們的生存繁衍十分有利:既可以避開專吃寄主葉片的昆蟲的連帶襲擊,又有利于鳥類的識別,為自己的種子傳播“積分”。但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情況卻與之相反,大約有三分之的桑寄生科植物葉片形態與寄主的葉片十分相似,甚至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這些寄生者為什么要模擬寄主而隱蔽自己的形象呢寧原來,幾千萬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紀時,澳大利亞的氣候非常干燥,許多樹木都適應早生條件使葉片形態向多刺毛的硬葉方向發展。顯然這種葉片形態不適合食草動物取食,經自然選擇保留至今。那些第三紀以后形成的桑寄生科物種,葉片的形態越與上述樹木相近,對食草動物的眼睛的欺騙性也越大,不被取食的概率越高。因此,這種擬態對澳大利亞的桑寄生科植物大有裨益。
如果我們潛心觀察,還會發現桑寄生科植物更多的“絕活”。正因為如此,它們才能穩居樹上吃喝不愁,繁衍自如,成為寄生植物中的望族。
女巫雜草—一將計就計獲生機
化學生態學是近年來植物生態學家的熱門課題之一。因為自然界中的每一種植物都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形成了利用化學物質為自己的生存繁衍服務的機制,以此彌補不能夠迅速位移和沒有專門的感覺器官等“缺陷”。作為植物王國中的另類,寄生植物因簡化生活而缺失了正常植物必有的營養器官,往往更需要化學物質的幫助,因此利用和反利用“化學武器”的手段也更高明。
獨腳金是一類令熱帶許多地區的農民恨之入骨的,農田雜草,屬于玄參科,全世界共有20來種,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亞洲的熱帶地區。它們看上去并不可怕,身高不過幾十厘米,細細的莖,狹小的葉片,一串串小花……但就是這類貌似柔弱的小草,一旦侵入農田,常使農民辛辛苦苦種下的高粱、玉米、甘蔗、水稻等農作物產量大減。尤其在一些連年種植同一種作物而越來越貧。瘠的土地上,獨腳金的猖狂往往毀掉90%的莊稼,嚴重時甚至顆粒不收。它們就像傳說中的女巫一樣,既神出鬼沒,又作惡多端,因此被形象地稱為“女巫雜草”。
“女巫雜草”像桑寄生科植物那樣,是一類半寄生性的植物,它們可以通過自身的葉片進行光合作用,但卻沒有可以直接從土壤中吸收水分的根系,靠吸器寄生在寄主的根上掠奪生活所需要的水分和無機鹽。
獨腳金繁殖力驚人。據統計,一株“女巫雜草”能產生太約10萬粒直徑不過0.3毫米的種子。這些能穿過針鼻兒的微小種子,一旦離開母體便四處飄散,落到土壤中后,就靜悄悄地潛伏下來,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令人稱奇的是,在農作物沒有萌芽時,整個農田見不到“女巫”們的半點蹤影。但當莊稼的小苗吸足了水肥茁壯成長時,整個“女巫”大軍便吹響了沖鋒的號角,紛紛鉆出地面,令企盼豐收的農民不寒而栗。以往人們難于理解的是,這些沉睡的“女巫”是被誰喚醒的,或者說它們是如何得到萌發指令的。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終于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喚醒“女巫雜草”的正是深受其害的農作物本身。
許多農植物在生長過程中,根系會散發出某些特定的化學物質,以此作為抑制近旁其他植物種子萌發和生長的“化學武器”。但正所謂一物降一物,這些作物根系分泌的化學物質,對正巧睡在身旁的獨腳金種子來說,不但起不到抑制作用,反而變成了刺激其萌發的信息素。它們以此斷定近旁就有可供自己寄生的對象,于是迅速萌發,將吸器準確無誤地扎入寄主根中,開始了新的寄生生活。如果獨腳金沒有這種將計就計識別寄主的特殊本領,它那十分微小的種子一旦盲目萌發,就會因找不到寄主不能及時喝到生命之水而坐以待斃。
目前已知,在自然界中,靠感知身邊寄主植物根分泌的化學物質而促使自己種子萌發的反化學武器“專家”,還有被稱之為“沙漠人參”的肉蓯蓉,以及草蓯蓉、列當等。許多寄生在寄主根部的植物都有這種“將計就計求生存”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