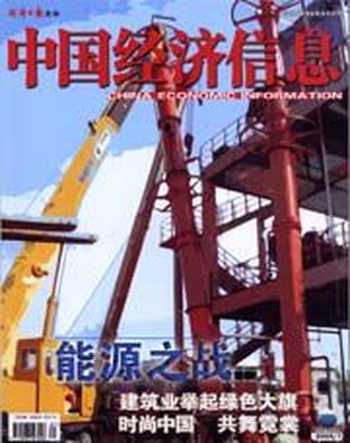心靈作畫筆 跪寫海天間
朱 琪
他生在藝術圈,又在東海中泡大;他非科班出身,卻努力在藝術的深層中體味求索。他從苦難中過來、從病癱中站起、淡泊名利、堅韌不拔地做著一件件令人感動的作品。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博導 潘公凱
真是將門虎子,潘老遺風。
——中國文人畫大師 陸儼少
蓮花洋人傳,曾癱挽狂瀾,玄機神來筆,縱橫海嶼涯。大師們對朱仁民不僅是藝術風格的評價,更是對他鍥而不舍、千錘百煉大家風范的充分肯定。
朱仁民出身在藝術大師家庭,卻在東海小島跌宕了40年。
上世紀70年代末,他獨自租個游泳池揮掃出高3米長300米的宏幅水墨巨制《大道海·天篇》。80年代初浙江畫院成立,他是第一位調回杭州作專業畫家,但卻在制作巨幅中跌下致癱,貧病間入晉陀山隱修庵長臥五年有余。
90年代初作為文化人他買下一座小島,從策劃、投資、規劃、景觀、建筑、雕塑,10年磨一劍,如此龐大的大地藝術作品尚屬罕見,全由他一個人獨立完成。
他從身無分文拄杖下山,歷盡文人難以承受的辛苦,將一筆筆畫出來的資金盡傾小島,為民眾建立一道永久免費旅游觀賞的海上藝術風景線,而他卻至今睡在工作室。
朱仁民出生在中國畫壇大家潘天壽先生家庭,自幼耳濡目染接受著傳統文化的熏陶。生活卻將他拋至天涯海角,從漲網、出漁、打鐵、教書到游泳池救生員、舞臺設計、美術干部,足跡踏遍東海,40余年天風海濤孕育了他對大海、藝術、禪學特有的靈性和堅韌不拔的秉性。
他自幼酷愛美術,10歲獲全市美展一等獎,20歲后發表了許多的連環畫插圖作品,30歲開始獲文化部、中國美協頒發的多項榮譽、獎勵和國際美術交流展大獎。
朱仁民年幼即隨父母去東海上的普陀島蟄居,在這當時還極荒蠻的小島,家喻戶曉有這么個天生背著個畫夾的人,幾十年如一日,畫下成千上萬的速寫作品。他甚至沒有感到過常人認為的那么多的刻苦過程,也不明白自己有沒有學習的停滯不前的創作磨難。很快樂地、執著地追求著繪畫和藝術。如此的狀態伴隨了他的整個童年和青年時期。
大海磨圓了多少億塊鵝卵石。若有一塊石頭尚且有棱有角直指蒼天,那定當是塊金鋼寶石,沒有天生的悟性和執著,沒有無意的追求和多于常人幾十倍的摸索,一個小島上的朱仁民怎么可能在繪畫上如此固執,如此迅速上進為一名藝術上脫穎而出的畫家?他唯一感到困惑與無奈的是極度的貧困和政治運動帶給他家庭和個人的壓抑。靠母親一個人30幾元工資養活著至死沒有工作權利的父親和3個兄弟的全部生活。為了生活,他讀初一就與哥哥瞞著母親去對面小島上打工掙飯吃,希望能減輕母親的負擔。由此開始他的足跡踏遍了群島中凡是有人居住的小島。對大海的了解和依存感,幾乎貫穿在他整個的人生藝術經歷之中。
千山萬重石,一日兩度潮,幾十年間大海哺育、澆鑄了這個大海上的孩子,給予他無盡的智慧、力量和雄闊從容的藝術氣質。正如他在題畫詩中所述:
生在海上羅漢胎,天風海濤醒醐灌。
經磨歷劫千萬變,似相非相自存在。
時添才情是非生,才做功德悉成滿。
常越業海無名礁,聊采覺浪智慧花。
1978年,他租用了自己任過救生員的游泳池,將一張張六尺宣紙拼接成3米高,用成箱成箱的墨汁倒入水桶,無法無度無功無利地整整畫了300米水墨巨作《大道·海天篇》,從混沌初開的大海到風起云涌白浪滔天,回復平靜,最后海天歸一。朱仁民潑掃得物我兩忘,盡興盡致,直至在拼接工作的腳手架上跌下致癱。這是以心和血潛入海中來表述自己對大海認知和心里由壓抑到爆發的一個過程,如同交響曲般宏大雄闊、氣吞山河。當時尚不知哪有個叫吉尼斯可以申報,也不知道沒有錢來完成裝裱,更不知有沒有如此大的展覽館來展示這一作品。直至1987年浙江電視臺為他拍攝上下集專題片“海魂”時,將六大箱作品用小卡車運到杭州海軍療養院室內球場,雇了一群民工,將整個球場圍了一圈還不到作品的一半。那飛濺的墨色,斑斕的白光,通過這如篆大毫,將朱仁民的心境,徹底地潑向大海,因為沒有任何功利目的,抖露的才是真正的自我。傳統的技法自古缺乏對大海表述的系統表達,大寫意的水墨畫家沒有在大海上生活過,朱仁民在探尋與自然的流露中選用了將游泳池作畫桌,經加工的掃把作筆,300米×3米的宣紙作畫面,這樣才使他得以酣暢、淋漓、自由自在地心情潑瀉。此時他曾有意識地回避傳統的技法,在宏闊中難免摻雜入粗率,噴發中難免夾帶狂野。
由此,他倒下了。1980年底,他那強有力的手和筆無可奈何地垂下,他沒有想到倒下的滋味竟會是這樣的殘酷和無助。沒有錢治病,沒條件養息,連起碼的住房都沒有。他徹底地絕望了。對死的渴望竟會遠遠超過對求生的追尋,盡管他也竭盡全力的企圖抗爭,不斷地請人幫他播放命運交響曲、英雄交響曲,滿屋子貼上“天生我才必有用”“苦難是成功的墊腳石”,希望以此激發出對命運的抗爭力,可是總無濟于事,他失去了人起碼的自理能力。
人生就是如此地具有戲劇性,因為無錢租房,房東們也怕將房租給一個長癱的病人,其母親的學生介紹他去普陀山一座山頂上的荒蕪破廟隱修庵養病,那里不要房租。此時的隱修庵,荒涼破落,斷壁殘垣,只有老鼠、松鼠和一條大蛇伴他整整度過五載。
上世紀80年代浙江畫院成立,調他回杭州任專業畫家,他卻在繪制巨幅作品時跌下致癱。貧病間入普陀山荒蕪的隱修庵長臥五年有余。無助中入悟道法師門下,靜研于藝術禪學間,數年后奇跡般下床,拄杖下山。
——潘公凱《蓮花洋人》序
當他有力量翻下床,在庵中破地板上練習爬行,直至能蹲,朱仁民激動了。他沒有錢買拐杖,取了根拖把柄和一位老農民贈給他的一根桃木拐杖,撐起了自己孱弱的身軀,他拍撣了一身的塵埃下山而去。此時正當畫界水墨運動席卷全國,他回觀自己過去的300米巨作感慨萬千。是對巨幅作品的粗率不滿,還是病癱后心理、體力的收歸,隱修庵中擠壓出他對藝術表達方式的困惑和對入定的強烈尋求。這階段他的作品開始趨向細膩、精湛。
他將西方的光感、層次隨機自然地揉合在傳統的筆墨語言之中,也將對大海、生活、藝術的感悟,嚴嚴實實地凝制在如詩如夢的禪境里面。他的書法詩詞,情感抒放,無拘無束,灑灑洋洋地奔瀉出他的生活經歷、藝術氣質和對入定的尋求來。
——潘公凱《蓮花洋人》序
1987年朱仁民帶了作品拜見陸儼少先生,陸先生竟然為他的作品氣勢所動情,“真是潘老遺風,將門虎子。”“作品的氣勢了不起,我沒有你那么樣的氣勢,真的沒有,我不會象有些人那樣沒有會說有。”并破例叫朱仁民幫他取下櫥上的整張四尺宣,斗書題贈他“潘老遺風”。
90年代初,經歷了多少年浪谷峰顛、跌宕騰挪的朱仁民,坐在海邊,玄覽靜思,開始一長段時間的反思,他回想:80年跌下病癱前,他創作的中國畫《在公海上團聚》在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獲銅獎,浙江省銀獎,他說,先擱下;1984年他以獨特風格的連環畫《青春日記》入選全國六屆美展;又以黑白疏密極考究的裝飾性線條連環畫《奔月》獲全國首屆風俗畫優秀獎,美協的領導告知他這種風格很獨特、完整,你再畫一套,奠定你的風格,朱仁民一驚,又趕緊擱下。他又以漫畫《大師考文憑》獲全國職工美展銀獎,漫畫《嚴重警告》獲全國七屆美展銅獎,漫畫協會約他參加活動,他又擱下,旋即又以民間版畫《擒龍王》入選首屆中國藝術節優秀作品展,直至他在日、中美術交流展獲大獎后,他才最后喘了口氣:行了!試遍了!他以各種技法、各種方式一口氣在國內在眾多高層次的畫展中,天真地檢閱了一遍自己多方位的藝術素質與才氣,回島上如同布道般地全身心地投入了免費的海島兒童畫、海島漁民畫的教育工作。此刻朱仁民分析了自己所有的能耐,他無論如何擺脫不了“藝術家”3個字對自己的嘲笑,很認真地將自己的藝術軌跡鎖定在一個具有嫻熟技巧和敏銳度的高級畫匠。
他不愿意做個自說自話的大師,更蔑視那些吃著民眾的俸祿,戴著各種耀眼桂冠、混混噩噩的“藝術大師”們。
這個時代聰敏的畫匠太多了,技巧到了淋漓盡致的飽和點。而缺少的是精神,一種奉獻的精神,藝術家不管在從事“陽春白雪”或“下里巴人”,在俗與雅、藝與德都不能忘記自己的責任和良知,在目前這種物欲橫流的時代正需要獨立寒秋、中流砥柱式的藝術家。
他認為自己具備當代文人、藝術家所不具備的某些精神,他在幾十年海內外生存中所獲得的廣博的知識,包括對哲學對禪宗的理解;對社會對人學的洞察;對策劃、營造的精確與敏感;對弱勢與苦難的體驗;對文化、藝術的總體認識與把握,以及堅韌不拔的吃苦精神。
他立志以冷峻而理性的文化良知、藝術潛質,志向社會,抖露出自己的畢生與全部。
他開始注視病癱時天天凝視著的一座小島,一座生在普陀山海面上,酷似海上臥觀音的天工之作——蓮花山。冀希著有一天如同圣西門,傅立葉一般在懸水的領地上,實施自己的人生、藝術主張。
他想以自己的藝術實踐來證實自己對新世紀藝術的認知,將人為的禪宗演變為對自然的崇尚,人格的崇尚以及它們之間天衣無縫的合一。同時也在這一件作品中抖露出他對建筑、規劃、景觀、雕塑、繪畫、室內全方位的藝術把握性和心與物、形與神、人與自然天衣無縫的合一。
終于,朱仁民10年磨一劍,經歷了文人難以承受的扭曲與辛酸,在小島上用自己的智慧和雙手螞蟻啃骨頭般地矗立起一座座向著民眾樂于接受的大自然圖像,并將自己不斷摸索的繪畫作品相擁在這爿小島之上。這里已經分不出建筑與雕塑,藝術與禪宗,大海與人生的界定,全在一身汗水和海風刮出的咸淚之中。
至真至摯、堅定不移的人生軌跡鑄就著蓮花洋人朱仁民獨特的人格魅力和價值豐碑,正如他的人生寫照詮釋的精典之語:當我跨越艱辛,站在人生的高地上回望,我有資格微笑,屬于那種勇敢純粹的人類!
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室內設計師學會會員朱仁民曾獲文化部、中國美協頒發的大獎有: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銅獎、第七屆全國美展銅獎、全國職工美展銀獎、首屆中國藝術節優秀獎、日中國際美術交流展大獎;被文化部授予全國兒童文化先進工作者,全國民間繪畫優秀輔導員。并入編《世界名人錄》《東方之子》書畫卷、《中國世紀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物辭典》《世界優秀華人藝術家名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創業功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