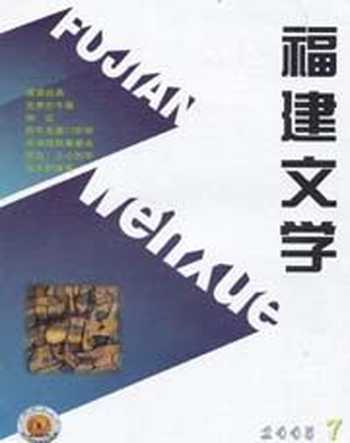免費的午餐
曹明霞
我和表妹時常要湊在一起聊天,就像有些單位的定時例會。因為我們都是離婚的女人。離婚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稀奇了,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問題是我們現在又都面臨著離婚,再次的離婚。
早上,表妹電話都沒打,就直接來摁我家的門鈴。聽是她,我撳開對講門,說上來吧。她說表姐你要下來一下,幫我拿點東西。
我趴窗向下一望,呀,表妹的自行車載滿了鼓鼓的包裹,像三輪車一樣寬大。車梁上連個空兒都沒有,她是怎么駕馭來的,騎在哪了呢?
我下去幫助表妹手提肩扛,把東西拿上來了,還好,都不重,只是體積大。表妹說這都是宋江單位的,有的是發的,有的是他偷的。新被子,新毛毯,還沒用過呢,都挺值錢的。表妹為自己先下手為強的戰果而自喜。
“你提前倒騰東西,他知道了怎么辦?”
“東西多,他不一定都記得。再說了,昨天他還拿走了我的手鏈呢。”
天呀,已經到了搶東西的地步,這日子確實不好過了。
表妹把包裹一層層打開,淘寶一樣淘出了一個小盒子,紅絲絨的,我以為是首飾,她說紀念幣。晃了晃,“純金的,足金”。表妹臉上很安慰地說。
那天表妹沒有多坐,她簡單歸置了一下,就走了。說還有事。看著表妹健步的背影,我的心里突然云開一樣晴朗。原以為她會很憔悴,很悲傷,因為就在前天晚上,她半夜打響我家的電話,說她正在樓下的草坪坐著。不用問,她是被打出來的。我看了一眼墻上的石英鐘,已經兩點多了,“要不你來我家?”“不,不去。”表妹回答得很堅決,雖然她的聲音里是抑制不住的哽咽,但我知道我勸說不了她。表妹不愿意見我們家的老吳,她對老吳的反感就像我對宋江的憎惡。表妹說表姐沒事兒,我主要是胸悶,出來透透氣。給你打電話,主要是告訴你,如果宋江打電話找我,你就說不知道,沒來。
“不知道,沒來。”這是表妹每次和宋江吵架離家后,都要給我的叮囑,似乎是想讓宋江找不到她,沒處找她。而在我看來,她這份閑心操得純屬多余,因為宋扛從來就沒有找過她,無論是她離家了一夜,還是幾日。有一次老吳出差,表妹在我家住了半個月。那時只要電話鈴響,表妹都一馬當先,搶著去接電話,結果當然是無功而返。在她失望落寞地把玩手機時,我看到在她翻看的短信信箱里,還有宋江一年前發給她的信息,信息很像網頁上那些變態狂的留言,讓人看了惡心,起雞皮,可是表妹卻在回味,欣賞。
“宋江有病,還病得不輕。”我說。
表妹不置可否地笑了。
我認為宋江不但有病,他還是個騙子,一個很高級的騙子。最簡單的例子是他能把表妹這樣一個大學本科,又讀了碩士研究生的女人給騙蒙了,騙傻了,相信他很愛她,會在她受傷出走后,因為找不到她而焦急,而備受折磨——這不是一廂情愿的妄想嗎?宋江如果愛她,有那么一絲絲的愛,會在她出門的剎那,又是半夜三更,而對她聽之任之、無動于衷嗎?一個要在樓下的草坪上過夜的女人,有家不能回,還打電話告誡我別告訴宋江她的去處,我看表妹真是傻透了。
可是表妹卻不這樣看,相反,她覺得自己非常精明,腦子很夠用。她不止一次竊喜著對我說,知道嗎,當初不是我堅持,一忍再忍,供他吃供他喝,騙他,他不會跟我結婚的。早滾回到老婆孩子身邊去了。
你不知道,為了登那個記,扯上結婚證,我費了多大的勁兒。表妹又說。
扯了證現在不是照樣要離嗎,倒麻煩。
那可不一樣。怎么說也是跟我結過婚了。不然,得被那個女人笑死。
人在曹營心在漢,結了婚又有什么用。
用處可大了,起碼他人要在這個家,錢也要往這個家花吧。
你又不是沒有工作,養活不了自己。我真不知你圖什么。
表姐,這還不明白呀。要是一人過好,你又結的什么婚呢。
咱們不一樣,我得讓孩子有個家呀。
關于結婚離婚,我和表妹方向上是一致的,原由卻大不相同。表妹時常勸我,說表姐我要是你,已經有兒子了,這輩子也不孤單,就不再成家了。況且老吳還是那樣個男人。你看你家老吳還像男人嗎,陰得臉上能下雨,一天都不說一句話,完全像個太監。
看來是一家不知一家苦啊,她羨慕的,正是我的難題。我就是因為有兒子,才千萬百計地想成家。我兒子沒爸,我不能讓他一輩子沒爸啊。
表妹又說,不過老吳這樣的也有好處,有錢有車,又不亂搞,你要知道,現在的有錢人,能不養二養三兒,不天天給你戴綠帽子,那是多大的福呢。
我可想讓他出去搞,可是老吳這人,除了愛他自己,誰都不愛。
表姐你也不要要求那么高了,我們都不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了,還是再婚,有日子過就不錯了。
日子?什么是日子?實話告訴你,結婚一年多,我一直睡在保姆屋里。
表妹理解地點頭,再點頭。也是,老吳這一點是夠嗆。他和宋江勻乎勻乎就好了。
表妹你不知道,為了讓老吳對我有點感情,我家保姆都不雇,我天天在家,侍候上侍候下,可是老吳照樣頭不抬眼不睜。昨天做了一條魚,小火鈍了半天兒,六個小時,你說耗了我多大的功夫。老吳吃的時候,眼皮沒撩一下,一直是吃,直到把那條魚吃剩一根兒刺,森森白骨。從始至終,他沒說過讓我吃一口。你說,這像夫妻嗎?
像周樸園和魯媽。
我要是有工作,有學歷,還像你一樣沒孩子,一個人走遍天下無牽掛,我就不再結婚,一輩子就一人兒過了。多爽。
表妹說女人沒有孩子,你不知道多孤單呢。
可是,我就是因為有了孩子,生活才一再地亂七八糟呀。“沒兒沒女活菩薩。”這是母親活著時常說的一句話。我覺得沒有文化的母親,這句話說得真是太精辟了,非常的準確。養大一個孩子可是太難了,我有幾次都覺得活不下去了。而母親,她當年也一定領教了太多的苦,因為她一個人,養了我們八個,還沒有父親相助。有一次看電影,片名是《一個和八個》,我說媽你和我們就是一個和八個的故事。
不,不止是一個和八個。當時痛恨母親生了一堆孩子的大哥冷酷地說。
母親瞬間就低下了頭,什么都沒說。她本來聽完我的話是要笑的。
一個和八個。我和兒子,也不只是一個和一個,再婚的旅途上,我問了一家又一家。人家首先問:有孩子嗎?
有。
是男是女?
男孩。
是男孩人家馬上就搖頭了。帶孩子的女人本來就降了等,孩子再是男的,長大上學結婚娶媳買房等等等等,危害性太大了。對方幾乎是無一例外地說,男孩我們就不找了。
男孩和繼父是天敵呢。介紹人都有這樣的覺悟。
后來,我就自覺地降低條件,一降再降,比如男人的年齡不限,相貌不限,工作不限職業不限。老吳大我二十多歲,只因不能生育,年輕時女人走掉了。進老吳家門的那天,我原以為他會色迷迷地看著我,歡迎我,可惜我錯了,老吳像電影上那些老派的老爺一
樣,穿得挺好,家境也不錯,表情威嚴中透著冷漠,他說嗯,你來了,洗洗,去收拾吧。
我就去收拾了。
在表妹準備離婚的日子里,我告訴她,我們也要分開了。雖然離開老吳,我將再次面臨流離失所,可流浪也比困獸好活。我說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受不了老吳的冷酷。你說他都有那么多錢了,又沒孩子,他還掙錢干什么呢?可他就是天天跟錢拼了命。沒有一天是半夜十二點以前回來的。還有一樣,就是酒。你知道,錢和酒,是老吳這一生的大房和二房了。我呢,丫環都算不上。在他眼里,沒有女色。他找了我,是雇了個免費的保姆呢。
表妹說唉,老天捏男人時怎么那么漫不經心呢,宋江和老吳正好搞反了。
確實,宋江對女人已經到了變態的地步,這也是我一再鼓勵表妹離婚的原由。我認為宋江已經豬狗不如,就是古代的皇帝,也基本限于宮院內的女人,而宋江,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幾乎都不分老少了。而且還同時保持著多家的關系。宋江并沒有什么權,有錢也是舍不得花死摳那道號的,可因為他是司機,公車私用為他提供了拉女人的便利。他經常開著那輛奧迪車,老黑魚一樣游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東家人西家,有的有丈夫,有的沒丈夫。對這些宋江一概忽略不計。
也是因為有車,為表妹的跟蹤偵察提供了相當大的難度。打的追蹤,表妹是打不起的。
“我現在不抓他了,抓也沒用。這回我和他是肯定離了。”表妹說。
看我目無表情,像不相信的樣子,表妹說,這回真的,“這次要是再不離,我都不再是你表妹。”表妹發誓。
離吧,看著表妹眼角的烏青,我說不離也沒好。這樣打下去,你是打不過他的,什么時候失手,他把你眼睛打壞了,后悔都來不及。
表妹用手摸了下眼角,說這不是他打的,是昨晚電話磕的,我打電話報警,他搶,電話搶到了我的眼眶上。
他要是拿刀劃了你,你也不怨他,而是把這筆賬記在刀子上嗎?我恨鐵不成鋼。
表妹不吭聲了,她知道我對她家宋江有仇恨,宋江這個色魔,有一次借酒遮臉,對我這個表姐動手動腳。后來我告訴表妹,表妹說真恨不得把他拉到驢圈騸了!
我一直不明白,以表妹的條件,為什么她跟宋江成了一家人。表妹在上大學時,她有著辛德瑞拉一樣的善良和美貌,按理,她應該相遇一位白馬王子,有份幸福的婚姻。可是偏偏不,表妹的第一次婚姻,連洞房花車都沒有,她就稀里糊涂地頂上了離婚女人的帽子。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同居一詞可是鬼混的別名啊,不是正經人,好人是沒有那么干的。和宋江,表妹也依然沒有當上新娘,她沒有婚紗,更沒有婚禮,她像搶婚一樣,是死乞白賴地跟宋江把婚結了。所謂結婚也就是到民政局拿回了兩個小本本。每當問起這些,表妹都嘆口氣說,姐,這都是命啊。沒辦法。
我可不信命,雖然我和表妹什么都比不了,我沒有學歷,沒有工作,但是我有一雙能快速奔跑的長腿,在我路邊擺攤兒的時候,每當看到城管的人一露頭,我能在剎那間夾起兒子,卷起地上的包裹,轉眼就飛奔得無影無蹤。而那些跑得慢的,因行動遲緩,不但被踢翻了鍋灶,還抄走了她們的桌椅,服裝,幾乎是全部家當。躲在暗處,看著遠去的車隊,我很同情她們,也慶幸自己,是我鶴一樣的長腿,使我一次次化險為夷,絕處逢生,也使那些匪兵一樣的城管人員,對我難望其項背。但是,到了夜晚,我的長腿又顯出了短處,因為我和兒子是租住在一處不足兩平米的吊鋪上,睡眠成了我最發愁的時刻,我真恨不能把兩只腿折疊一下,或者卸下來另放地上。后來,兒子的個子也長高了,他的腿也和我一樣,面臨著同一難題。就是白天擺攤兒,我也無法一下子夾起他就跑了。我跟命運拼命,可是明顯地,越來越不好拼了。
這時,我又想到了活下去的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嫁人。只要找個有房子的男人,我和兒子馬上就會有家了。
我去了婚介所,我以為到那兒就會有現成的,像上貨一樣,盡管挑。可是我想錯了,女老板很厲害,她描濃眉,畫紅唇,頭上還插著一個金鏈兒簪,很像舊電影上妓院的老鴇。說話也又奸又橫,她幾乎是冷笑著問我:你想什么都不費,到這就找,中介不成了免費拉皮條?現如今就是看個破房子,也要先交點跑腿費吧,何況是要看大活人!
看房子那套我懂,多年來我一直在租房。中介們本來沒房子,可她愣能說出幾處你要找的房子,只要去看,就必先交上看房費。最后沒看成,費也不退了。這些把戲我見多了。我說你這看大活人,該不是也像房子一樣,是假托兒吧?
我的話讓女老板雙眼一亮,并真心地笑了:她說原來你也干這個。
看也看懂了。
要不,這樣吧,咱們明人不說暗話,我看你呢,長得也不錯,你就在我這先干一段,注冊費呢,也不用交了,干一段后用工資頂,無本的買賣,等于空手套白狼,怎么樣?干這個當然好,一不被城管的到處抓,二還近水樓臺。
老鴇好像一下子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說別打什么歪主意,真槍實彈不成。咱們運行,最忌的就是吃窩邊草,你呢,安下心來在我這好好干上半年一載,多創點效益,自己的腰包鼓起來,即使找不上合適的,日子不也好起來了嗎?
我沒有文化,更沒有學歷。我實話實說。
這個呀,不用學歷。你今天就說自己是小學老師,男人死了,死男人的對方愿意找,踏實。呆會兒就有個姓吳的老板要見面。你的主要任務就是帶他去咖啡屋,喝冷飲,喝完冷飲能再去酒店,更好。出了酒店如果還能帶去商場,那算你有本事。每一環節都有提成,就看你讓他消費多少。說著,老鴇交給了我一張小紙片,上面有指定的茶樓酒店和商場地址。
正說著,前門有客人說話聲,老鴇慌忙把我推到后面,迎出去說來了,我們正等著您呢。然后我聽到一個老年人力求洪亮的嗓音,老鴇回頭把我叫出來,沒什么過渡,介紹了一下我的年齡,身份,包括名字,都是她瞎編的。然后就讓我們出去自己談吧。
我們出了門,馬路上肯定是不能談的,老人家走路都有些喘了,不能像年輕小伙子那樣邊踩馬路牙子,邊跟女人調笑。接下來,我猜他會說咱們找個地方坐坐?如果那樣,我就順水推舟,請他去“無人島”。
可是老人家面沉似水,他說小陳(小陳是我剛剛才有的姓),你也不要拐我去什么無人島有人島了,說實話,我對你還中意,如果你不是托兒,確實沒有家庭,就跟我到我家去坐坐。咱們可以打出租走,費用我出。
天吶,這可是新同志遇到了新問題,我一下子犯起了難,事先老鴇可沒告訴我出現了這種情況怎么辦:怎么處理。
老人家看出了我的為難:他說要不,你先回去請示一下?
我站著沒動。請示什么呢,去他家消費,我一分提成都拿不到,還可能被扣工資。
老人家說,大太陽底下的,咱們這么站著也不是個事兒。這樣吧,這是我家的地址和電話,我叫吳用,今年六十歲了,沒兒沒
女,有家自己的公司。如果你還有興趣了解其他,有時間可以去我家里坐。今天就不去什么商場酒店了。好吧。
我拿著手上的小紙片,傻愣了半天,太陽下紙上的字像一團團小蒼蠅,嗡嗡地飛。我很沮喪,一分錢也沒讓人家消費掉,回去不知怎么跟老鴇交差。沒想到老鴇很寬厚地原諒了我,她說老狐貍成精了,不上咱這個當,看來他是有經驗了,知道不見兔子不撒鷹呢。他這個人也就這樣了,再來電話我就告訴他,人家姑娘嫌你太摳,連個商場都不敢去,還想找什么媳婦兒!讓他涼快去吧。
后來,老吳再來沒來過電話我不知道,我又一連出任了幾次中學教師,銀行職員,還有政府公務員什么的,收獲都不大。那些人好像都明白我是托兒,堅決不上當。只有一個鄉下來的包工頭,破產了,說要找富婆,我當天的身份就是富婆。他花了一些大頭錢,目的是舍金套玉。那天結束,我覺得太惡心太骯臟了,包工頭不但醉得口腔一遍遍管涌,他還大著舌頭表示,愿意當場脫下褲子,一顯身手,讓我見見他真正二爺的厲害。
我幾乎是踉蹌著跑回去找老鴇,我說我不干了,說什么也不干了。找愛情找婚姻,臭垃圾吧。這么長時間了我有多少工錢,你給我結一下。
老鴇還算善良,她沒有像舊社會的老鴇那樣死拉硬逼,她說不干就不干吧,不過實話告訴你,這個世界上,哪碗飯都不好吃,就沒有好吃的飯!說著,她給了我五百塊錢,這可比擺地攤多多了。我心下感激,眼淚就下來了。老鴇說,看見沒有,找對象,找什么對象,都是想把自己的困難扛到別人肩上,女學生想傍大款,農村小伙想靠富婆,都把婚姻當成了免費的午餐吶。可是誰傻呀,不好找。還說什么愛情,有愛情我能不找哇,守著攤兒這么近,我還能把好的留給別人。嘁。你也來這么長時間了,你見著愛情了嗎?愛情也像那免費的午餐一樣,不好找。人吶,這輩子,活來活去就是顧個兩頭兒,多數人能顧上一頭就不錯了,有飯吃,有日子過,這一輩子,也就行了,什么愛情不愛情的。
老鴇的話語重心長,出了中介的門,我就直奔老吳的住處。
我過起了良家婦女的生活,能做得一手好飯,灑掃庭除。雖然老吳有錢,可是過日子上我極其勤儉。衛生間的水龍頭下,永遠在滴著一滴水,慢慢地滴,不走水表。每個月交費,我家只交一噸水的價錢。電也是,即使在黑暗的傍晚,我做飯時也只開陽臺上一盞小燈,兒子放學回來,還以為家里沒有人呢。他發現我正用那滴來的水淘米,說媽,我真不明白,你這是圖什么呢。家里又不缺錢。
兒子是不能明白,他還小,他怎么能明白日子是什么呢。
就連我和表妹,已經在日子里走進走出的人,不也依然糊里糊涂嗎?
這一次表妹提前往外搬東西,看得出她的決心是下得很徹底了。從前她頂多是出門躲幾天,宋江不找她,她就又像出差了一樣自己提著包回家。這一次,她先下手為強,提前轉移家財細軟,這說明她確實不打算跟宋江過了。
我問她,這一次為什么力度如此之大,真能不過了嗎?
表妹說肯定,這一回我要是再說話不算數,我就不是你妹妹了。說著,她眼里盈滿了淚,表妹不是演員,她那大顆的淚不能含在眼里隱而不落,她的淚水像滂沱的雨,下得稀里嘩啦,聲音也是真哭,一個婦人的真哭,沒有一點美感。她的鼻子是囊的,面巾紙瞬間被她用了滿地,她滔滔的淚水和悲痛的敘述互相碰撞,我斷續地聽明白了,宋江不但偷偷在外面買了一處幾十萬的公寓,公寓里已經有了懷身孕的女人。這個消息是另一個爭風吃醋的女人用信息發給表妹的,還附了照片。表妹說完了,我沒有孩子,這日子就像黑洞,沒頭啊。我不耗了,算了,抗不過,想開點。離!
一個臭司機,卻妻妾成群,過著封建老爺的日子!呸。
我當初就是被他的外表迷住了!表妹蒼茫地仰臉看著天。
宋江確實長得挺好,中年男人了,頭頂不禿,身子不胖,走起路來還小伙子一樣噌噌噌的。宋江還喜歡打球,唱歌,經常在高級酒店里吃吃飯,上島館喝喝咖啡。如果不了解宋江的,還以為他是個教養好,生活健康有規律的知識分子,只有表妹知道,他是個東奔西走,在夜晚花天酒地的嫖客。
表妹走后,我為她的認清形勢而高興。不過我也擔心,她能不能像往次那樣,離了一通最后又不離了。不管怎樣,她已經發誓了,宋江又撤走了她腳下的梯子,想必這次她不會再不了了之了吧。當天晚上,我和老吳談了我們離婚的問題,我說這樣的日子,我就像被人揪著頭發在半空飛,并不好受。
老吳看了看我,他說我明白,能理解。
不過——他又說,你帶你兒子出門去玩一趟吧,現在正好暑期。費用我出。如果你回來后還堅持原來的意見,我不會勉強。
夏天快過去的時候,我和兒子從拉薩回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游走了大半個中國。我們沒有跟隨旅游團,那種一輛大巴一只大喇叭,人人舉著小旗聽召喚的形式,我認為那不是旅游,那不過是貨物一樣被不停地裝、卸,裝、卸。我喜歡自由地行走,我和兒子安步當車,實現了真正的游山玩水,是老吳的一張金卡幫助我們如此充分地熱愛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回來的路上,我和兒子心情舒暢了許多,甚至是從沒有過的暢快。
回來的第二天,表妹就來我家取東西了。我以為她找到了房子,問她手續辦了嗎?表妹沒回答,一副行色匆匆的樣子。我問她房子在哪兒?要不要我幫你?
表妹說不用。這時,我向窗下看了一眼,發現樓下正停著宋江的車。宋江來搬東西?我看著掀起的車后蓋,和坐在車里悠閑吸著煙的宋江,心里明白了,表妹是在往家搬。
我的火兒騰地就上來了,我說我真不明白,宋江都那樣兒了,你怎么忘性這么大。
表妹不吭聲,小心地檢查著那枚紀念幣。
宋江到底哪兒好,他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這樣離不開他!
表妹理虧不爭辯的樣子,依然低頭忙活。
我就不明白了,你又不靠他吃,又不靠他喝,一個爛貨,你到底圖他個什么呢!
——你今天不說清楚,我不讓你走!我氣得坐到她的大包兒上了。
“姐,這不明擺著嘛。”表妹沒抬眼皮兒,把我從包上挪開,“他好歹不陽痿呀。”
——表妹把那個大包用力往肩上一聳,下樓了。
責任編輯: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