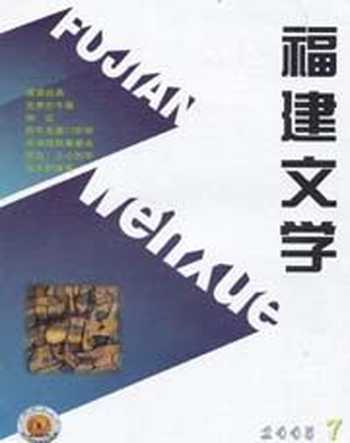戲子
章 浩
很多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戲子。我早晨起床的時候,對著鏡子,梳理我的發,整理我的衣,擦擦皮鞋,像一個要登場的戲子一樣,我收拾著自己的行頭。上班的路上,會發生很多的事情,比如必須經過的樓下的花園,我看著那些曾經綠色茵茵的草,現在開始變黃了,還有花木,枝頭一樣淡了紅。天有的時候會陰沉著臉,風冷了些,我感覺它們開始侵入身體。我的情緒隨之也發生了轉換,如此敏感的個性,使我對路遇的第一個人開始微笑起,就挺失敗。接著我的戲開場,瑣碎的事務,吵鬧的人聲,越來越多類似的壓迫,使我的演技也越來越差,我盼望著夜的來臨,那樣我會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我知道,被動作為一個戲子,我必定是失敗的,生活很多的無奈也是如此,我投入的激情越來越少,我竟然封閉了自己,封閉的是我的敏感的心,對于世界,這個世界上的滾滾的人群,它們和我隔離,我喜歡這種隔離。
但我是有演戲的遺傳基因的。母親唱過戲,在她還沒有出嫁的時候。我想象那個時候她一定美麗,現在她老了,發都白了。她年輕的時候,穿著紅綠的戲袍,臉上擦著濃重的油彩,折折回回,衣袖飛舞,啟朱唇,裂玉帛,唱戲文,“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她沉浸在她的戲中,這成了她一生回憶不盡的溫馨。可是,后來,她出嫁了,做了人婦,別了舞臺,閉了嗓音,回到了現實中,“千般裊娜,萬般旖旎”,蛻變成了柴米油鹽,孩子的哭聲掩了笙管余音裊裊和鑼鼓的鏗鏘喧囂。我常常想起母親,想起我的童年。母親肯定是懷念青春作為戲子年華的,雖然她從來不提演過戲的經歷,她還有很多封建的觀點,認為戲子是下賤的,是不上臺面的職業,但她會靜靜地待在人家的窗口前,很長時間。我有些時候問她,她竟然會羞澀地紅紅臉,然后說,聽見了屋里傳出來的戲文,真好聽。我就遺憾,她沒有將戲演下去,我又慶幸,她沒有將戲演下去。
母親出嫁后,再也沒有唱過戲。作為一個戲子,只有回憶留在她的腦海中。她能干,越發使父親的無能顯現。父親只是一個清苦的教師,他愿意沉迷在他自己的象棋世界中。我的童年于是孤獨,我的孤獨使我沉迷在家里僅有的幾本書里面。院子里有一棵槐樹,鴿子從槐樹上飛過,太陽的影子在槐樹下悄無聲息地走,我在屋檐下,滿眼里、滿世界都是書的世界。我從書的世界中出來,就癱軟了,看著天空,明晃晃,云彩橫溢出天邊,思緒飛,旋轉著,舞蹈著,聳立,橫跨,沉思中的我就變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神創造著人,指揮著人,安排著人,毀滅著人。一種快感在那個時候就襲擊我,我在成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類似一種發泄的感官享受。后來,就有了一條鐵軌,向遠方伸展,我坐在鐵軌上,離開了家鄉,跟隨著風走,然后,我就看到了更多的書,什么書都有。有詭秘的,有晦澀的,有發笑的,有苦澀的,更有慘烈的。書對于我是一個世界,作者對于我是一個戲子,他們粉墨登場,引吭高歌,婉約吟唱,臉上擦盡了人間的油彩,身段扮盡了世上的光帚。
我有一天突然發現這個事實,嚇了一跳,我發現寫作者很多的時候是一個戲子,像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樣,臉上涂油彩,嘴里唱戲文。
我愛上了戲子。
我用鋼筆,方格紙,后來就用鍵盤和鼠標。我用方格紙的時候,有綠的,有紅的,我還喜歡用彩色的筆來涂抹紙,花花綠綠的文字在稿紙上飛舞,我沉迷在稿紙中不能自拔。鼠標和鍵盤更給我了演戲的資本,粗的,細的,斜的,正的,黑的,紅的,藍的,所有的,都使那些方塊字在屏幕上飛奔。我反叛的時候,我會戴上耳機,我聽到“情欲在尖叫”;我有淡淡憂愁的時候,我聽那首聽了千遍的“想過去的好時光/想我們年輕的時候/想生活真愚蠢……”當然我還聽呂劇,我還聽快板,我還聽那首《女人花》,我聽著聽著就會滴下淚水來,想起一些女人,想起一些愛惜。
可是,這樣的戲子的人生同樣失敗,我很多的時候沒有觀眾,我在唱獨角戲。
時空再回到童年的屋檐下,回到書的世界中,我突然發現我過去的認識有錯誤的地方,書里的作者在我現在看來不是戲子,他們是戲子的主人,也可以稱呼他們為導演。
卡夫卡將自己安排成了一個蟑螂,然后還是從生活中消逝了,蟑螂的命運很像我從現實中消逝,盡管如此,他還是一個戲子的主人。博爾赫斯從南美洲開始演,演到了印度,演到了中國,他的舞臺背影竟然有長城,還有青島。他就是一個瞎眼的說書者,時空對于他毫無作用,他蹲在路邊,瞎著眼,敲著鼓點,自言自語開始說書。但他也是一個戲子的主人。
我做不了主人,像做不了生活中的主人一樣。我從寫作者的戲子又開始逃離了,年齡越大,我發現,我越來傾向于就是做一個純粹的戲子。我經常微笑,很勤奮地工作,回家逗逗老婆,盡一個丈夫的本能,輔導孩子學習。我還會做飯,洗碗,我看見妻子孩子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也不多說話,我雖然很幸福,但我慢慢地開始焦慮,不安,我一直偷偷看他們,我知道,我的戲癮犯了,很難受,我期待我的舞臺。終于,隔壁傳來妻子和孩子的輕輕的鼾睡聲時,我就開了一臺叫做計算機的東西,關燈,屏幕上飛起來星光,那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屏保,像我飛濺開來的隱秘的內心,熱血沸騰。我戴上耳機的時候,會看看窗外,幾個窗,還有微弱的燈光,花園里黑黑的,漆黑,像我的眼睛一樣黑。周圍靜極了。往往是開一個叫做記事本的程序,有的時候是Word,將標題居中,我閉上了眼,靜默了一會兒,我其實已經想了一天了。演戲對于我沉迷久了,我必須承認,我分不清楚戲里戲外了,我抽著煙,在辦公室里冥想,然后在夜里,我進入了戲里,開始給臉涂抹上油彩,將白天想起的戲文記錄下來。我、你、他,甲三、乙四,丙五,那其實都是我自己,戲子的領導可以分配角色,可以布置背景,我將所有的角色都分配給我自己。我喜歡用“我”,我甚至將“他”置換成“我”,我的戲里都是“我”,我笑,我哭,我憤怒,我憂郁,我將這些演的戲,保存起來。我喘了一口氣,戲演完了,毫無意義,我去睡了。
做一個毫無意義的純粹的戲子有一種快感。
中學的時候,我就有一個女同學,她漂亮,她還反叛,和我一樣。我們就斗嘴,我們還吵架,吵來吵去,我們就吵出了感情。大年初一,她就來拜年,我記得,靠近家的小火車站的候車室,我們一起笑來笑去。可是,后來,她就消逝了,因為什么或者什么理由,我都沒有記憶。我成為了一個戲子,我就想起了她,我想起她的時候,我就成了一個戲子,我看著她從高樓上飛越而下,在大雪紛飛的季節里,血,綻開在白色的雪地上,同樣我也飛越了下去,象征了我逝去的青春和我留戀的情人,這場戲演來意味無窮,很讓我懷念,我起了一個名字,叫,雪。可是,現在這個“雪”還是躺在我的計算機里面,沒有人發現,沒有人賞識,從我想做一個純粹的戲子的時候開始,我作為一個戲子的悲劇也開始
但我還是繼續演下去。
我很多的時候是斷橋河畔的許仙,心情
是紫色的。斷橋邊,各式的葉子悠然飄落,西湖里的水流很清,還有浮萍,投影水里的是流云,深情的眼眸閃現淡紫色的心,就像我。我輕喚,怕驚了千年的寧靜,我的輕柔的聲音還是蕩漾成了波紋,波紋圈圈擴展出去,娘子啊,你可安好?我是許仙,我從波浪洶涌的海邊,來到了這西湖邊,西湖的水映照著我瘦弱的身軀,你可看見我淺淺的笑容,還有我略羞澀的面容?我可知道,我們兩人也還有一個故事,故事延續了千年,我帶著濃濃的愛意,我帶著滿腔的熱情,我是許仙,我在西湖邊飄起衣袖,旋轉歌舞。然后我就看見了娘子的笑容,秋的楓葉掩不住她緋紅的笑臉,娘子像一抹云彩搖搖蕩蕩走了過來,霞光滿天,遮不住你露出的一段潔白胳膊,我笑了,在我的丈字中,我在文字中演的戲中,我體會到了作為一個戲子的純情。
我還會是《霸王別姬》中的蝶衣,“勸君在飲酒聽虞歌,解君憂悶舞婆娑。贏秦無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子戈。自古常言不欺我,成敗興亡一剎那。寬心飲酒寶帳坐,再聽軍情報如何。”我輕嘆一聲,“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我聽見了楚霸王“咬牙切齒罵韓信,拿住胯夫碎尸分”的恨聲,聲聲讓我滴淚。可是,我是戲子,我就會演來演去,我就演成了蝶衣駕鶴西去,她的旁邊還有一只鶴,那只鶴上橫跨著楚霸王,淡在天際云深處。
我還演現代戲,我穿得很少,我脫了上衣,脫了褲子,我裸露了身體,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開始了解剖自己,我手里拿著刀子,很鋒利,我扎下去,從我的胸膛開始,肉白花花地翻開,沒有血涌出來,我看見了自己的心在跳動,心在顫抖,但這不夠,我用刀子一點點剔開動脈,剔開靜脈,心一片片成了碎片,我用手沾著動脈里流淌著的血液,品嘗這心的滋味,有的時候,很濃,很騷,有股性器官的味道;有的時候很淡,淡到我不相信,這是自己的心,甚至這根本不是我的心,是狗的心,是豬的心,是羊的心。我演啊演啊,演來演去,我就體驗了童年的屋檐下的快感出來,我變得很純粹,很快樂。
但有一點,我始終褪不掉我的內褲,那是我最后的堡壘,作為戲子,這是何等悲哀啊,我到底做不了一個徹底的,徹頭徹尾的戲子,這都源自我的相信,我如何演來,也是獨角戲,我甚至不相信那臺叫計算機的東西,它或許有一天都會出賣我,這是我作為一個戲子的悲劇補充。
關掉計算機,我會靜默一會兒,常常想起母親,想起我的童年的時候。父親沒有在家里,父親早就奔殺向他的象棋的世界里去了,母親端坐在床上,然后輕輕地哼唱了起來,“金釵銀鳳頭上插/五色絨花十幾朵/菱花鏡照著芙蓉面/好似玉女把鳳下……”
我承認,母親的嗓子很好,清亮,婉轉。我坐在計算機旁邊,經歷了一場演戲的過程后,演過的戲已經存放在硬盤中,我也會清唱兩句,“走了一崗又一崗/叢林茂密遮日光!”我比母親幸運,母親比我幸運,母親后來沒有演戲,盡管她常常回憶,那種回憶盡管溫馨,母親不演戲,她活得很好,而像我一樣的戲子,不僅僅有快感,還有慘烈,這些我都不再愿意說出來。我孤獨地演戲,我是一個孤獨的戲子,當然,我睡覺,做愛,起床,大陽出來,我上班,嬉笑,打鬧,我在生活中繼續拙劣著我的演技,但我盼望夜的來臨,夜里作為一個戲子的人生,對于我是一個悲劇,就是一個悲劇,我還喜歡,對比母親的幸運,我也幸運,無怨無悔。現在,我將燈熄滅了,開啟計算機,一片星光散漫開來,戲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