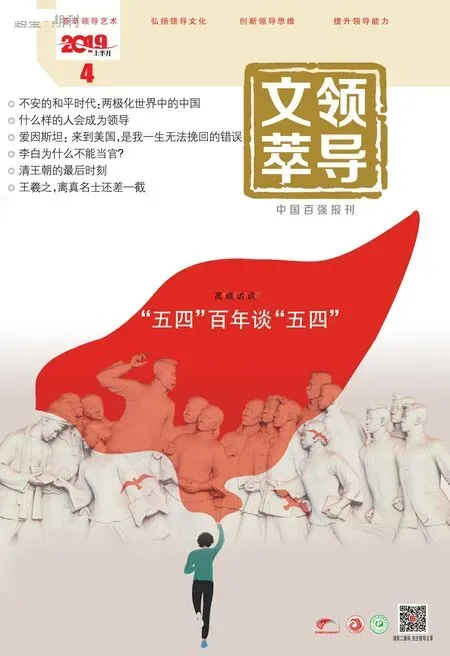教育部長周濟的“段子”
沙 楚 熊金超
“公”“私”分明——這種信息披露上的“雙重標準”,使周濟給外界留下的印象只限定于“校長周濟”、“市長周濟”、“部長周濟”,或者是“院士周濟”。而“生
活中的周濟”,卻少為人知。
“公開的”與“不公開的”
用“Google”搜索“周濟”,查閱者會得到18.9萬條的相關新聞,而在“百度”上,這個數字是34.1萬。這組數據給人最直觀的印象是,作為教育部的部長,周濟的“信息”并不匱乏。但是,仔細閱讀這些相關新聞,相信所有查閱者很快就會發現:如果撇除了以學術身份和官方身份出現的周的信息,他們對周一無所知——有關周的私人資料幾乎是空白,除了個人簡歷。
很多采訪過周的記者都曾嘗試了解他的“另一面”,但往往鮮有收獲。
“他的話題興奮點幾乎繞不開他心愛的科技。”三年前,一位新華社記者在采訪中,“努力探訪他的業余生活以及個人愛好”。但周的回應是“三緘其口”,“認為自己平時除了堅持跑跑步外,幾乎沒有什么業余愛好。”
周在“個人問題”上的回避,并不意味著他憚于接觸媒體。事實上,任職教育部長后,周曾力推教育部的對外宣傳工作,并多次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媒體見面會上。
周是“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國的留學生。1980年,在考入華中理工大學(后并入華中科技大學)機械系研讀碩士研究生后兩年,通過考試,周被選送至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學習機械制造。
“拼命三郎”加“好為人師”
盡管有著“海歸”身份,但大多數與周接觸過的人,給周的評價卻是“樸實”。
在華中科技大學,有一個關于周濟的“段子”廣為流傳。說周從國外回來后,為爭取科研課題,頻繁來往于北京與武漢之間。有時走得急了,連跟家里打個招呼都顧不上,常常是買張站臺票就“混”上了車。有一次上車后太累了,周和衣躺在別人座位下面就睡著了。結果乘警檢查車廂,很快把他給揪了出來,以為他是為了逃票。周解釋了半天,乘警愣是不相信,這位躺在座位下睡覺的會是位大學教授。
“周濟是個生活上大大咧咧,很不計較的一個人。但是他勤奮、敬業。”周的一位同學如此評價。
早在留學時,周的勤奮好學就有口皆碑。有一年美國大雪,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所在布法羅交通中斷,周的室友發現,周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回宿舍。第四天,擔心周出了意外的室友,急匆匆四處尋找,最后在實驗室發現“失蹤”的周。當時,周正趴在計算機臺上呼呼大睡,而電腦顯示屏上依然閃現著一串串數據……
有熟悉內情的人透露:美國留學期間,周在實驗室儲備了大量的方便面、罐頭和生活用具,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實驗室度過。正因為如此,周僅用了3年半時間,就先后獲得了在美國通常要用6年至7年才能取得的工學碩士和工學博士學位。而且16門課程成績全為“A”(優秀)。
“即便在學校的時候,他做研究也是非常能吃苦。”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的一位老師接受采訪時說,“老師們私下聊天,也談起過周部長。對他,大家依然非常尊敬。”周1984年回國后,執教于華中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歷任機械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在華中科技大學前后待了16年。
據說,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時候,周的同事私下里稱他為“拼命三郎”。周常對自己的博士和碩士們說:“我每周工作70個小時,就要求你們干60個小時。”而且,周經常忙得忘了吃飯,手下人也不好意思提醒,結果害得大家一起陪著挨餓。也因如此,周的妻子經常會在晚上7時左右,給單位來個電話:“周濟今天出差了嗎?如果沒出差,請提醒他回來吃晚飯。”
在私下的場合,周有一次開玩笑說,除了工作,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興趣就是“好為人師”。周說,從1972年走上大學教師崗位以來,即使當了院士、當了校長,自己始終沒有離開過教師崗位,“已經習慣了和學生交流。”
即便是后來當了武漢市的市長,只要回家早,仍住在大學里的周依然習慣把一些科研課題負責人叫到家里,和他們探討學術問題。一些業已取得成就的學生,也愛有事沒事到他家串串,向他請教科研難題。
演講不咋地,做事有眼光
1997年擔任華中理工大學校長后,周經常需要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做報告。一位已經畢業的研究生回憶周在這種場合的表現時,“坦白說,很平常!”這種評價來源于周與周的前任演講風格的對比。
“前任校長是學人文出身,經常出席各種講座,演講時能把握聽眾情緒,極有感染力;而周校長的風格則是平實低調。”
“但在私下交流,你會發現,他思路非常清晰,邏輯也很嚴密。”他說,“而且非常有眼光。”
研究生舉了個周創辦CAD實驗室的例子,為自己的觀點作佐證。他說,周留學回國時,別的沒帶,而是用自己所有的積蓄換回來3臺單板機、1臺蘋果個人電腦和30公斤的學術資料。“他把這些設備和資料全部捐給學校。無論從硬件還是軟件上看,這都是當時非常先進的。”
有了這些電腦和學術資料,華中理工大學很快創立了自己的CAD(計算機輔助設計)實驗室。事實上,周自己也常說一句話: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就是計劃與準備。在現代高科技的時代,你看不準,沒有做準備工作,就無法在競爭中取勝。”
在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位老師的印象中,周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有眼光,在人才培養上也是如此。“記得是1998年時,周校長當時就要求,所有的博士都要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當時很多人對他這個主意感到很郁悶,因為以前沒這個要求,現在多了這個硬杠杠,讀博的難度一下就高了許多。
“大家明著不好反對,于是以圖書館資料不夠為借口。周校長聽了,二話不說,加強圖書館的建設,保證大家想看到的國外學術期刊,在圖書館都能找到。結果,有怨言的人也沒轍了。”這位老師說,“幾年下來,結果是,當時的高要求,最終行成了一個雙贏的局面——圖書館資料豐富,博士生的水平也水漲船高。”
一位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的記者,從新聞從業人員的眼光分析了周幾年中的舉措后,得出的結論是,“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能提出一些獨特的思路。”
“他當校長時搞的高校后勤化改革,當湖北省科技廳長抓的中國光谷,以及當市長時提出的‘綠色武漢概念,應該說,這些在當時都比較領先的。”
一位熱心的班長
周濟是“文革”之前考入清華大學的,就讀精密儀器系。
“他當時是我們的班長,憨厚但有威信,特別能團結人。”一位大學同學如此描述印象中的周,“剛上大學,大家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相比之下,周濟的組織能力是相當出色的。”
盡管一年后“文革”的到來,讓這幫“剛聞到清華的味道”的學生們的正常學習生活受到極大沖擊,但在此之前所發生的事情,卻讓這位大學同學對周的號召力,有了深刻印象。
“我們剛入學后不久就碰上了‘換班風波。”他回憶說,清華精密儀器系那一年一共有五個班,排名是“機零零一”到“機零零五”,當時國家有意教育改革,嘗試“半工半讀”。于是精密儀器系在這五個班中,內定了兩個班為“半工半讀”班,學習機械制造,其余則屬于光學專業。消息出來后,原先分配進‘半工半讀班的學生們不樂意了,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看來,光學專業比機械制造更吃香。
由于學生意見很大,最后學校不得不重新分班,同時號召學生主動報名去學機械制造。“我和周濟當時是被分進光學專業的。重新分班時,周濟就動員大家響應學校號召,主動報名機械制造專業。”他說,“從這一點上,能看出周濟社會工作能力是比較強的。因為后來,我們那個班幾乎全部報名轉成了機械制造。”
憶往事,這位同學的判斷是,周之所以能夠在同學中很快開展工作,這應該得益于高中時期的鍛煉。“他在高中的時候就是學校的團委副書記,后來進了大學,也是我們班的班長。”他說,“在我們那個年代,高中生能當上團委副書記的,鳳毛麟角。”
新疆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的肖舉森副教授也是周的大學同學,在他的印象中,念書的時候,周濟的信件是班上最多的。肖說,當時有個特殊的歷史背景,高中生在高考之后,錄取通知書下來之前,大多會主動填寫志愿書,承諾一旦高考落榜,就響應國家號召,支援邊疆。
“周濟是從武漢讀書出來的,他們那一撥填的是去新疆。后來周濟考上了清華,但也有不少高中同學去了新疆。周進大學后,一直和這些同學有書信往來,交流思想,相互鼓勵。后來周大學畢業后,主動報名去新疆,可能也是有這個因素。”
“應該說,對同學而言,周濟是很熱心的一個人,”肖說,“不僅是當學生的時候,他當了部長后也一樣。”
“他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他會關心你所關心的事。”肖有如此感觸是因為2004年與周的一次碰面,而此前,他們接觸并不多。
2004年,周出訪回國,路經新疆。因為周曾在新疆工學院工作過七年,周邀請老同學和老同事聚聚。“和他在大學是同學的,除了我,還有另外一位同學。”肖說,席間,周來祝酒,“他問候那位同學的第一句話是,‘你女兒在北京已經工作了吧?!問候我的第一句則是,‘你母親還好吧?!”
“別人感受不出這種問候的含義,但我們知道,他所問的恰恰是我們最關心的人。”肖說,“就這一點,我們的感覺是,老同學他沒變。”
(江河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