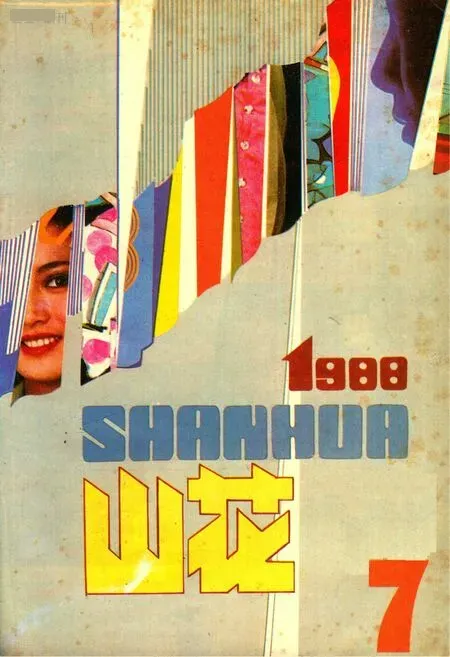網絡詩歌對人文精神的解構
任 毅 蔣登科
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點,詩歌總能較其它的文學門類率先嗅到時代環境瞬息萬變的氣息,及時作出反應,并對自身的發展方式作出矯正。網絡詩歌應運而生。它依賴網絡技術而存在,和其他的技術媒介的發展一樣,離不開人文的動機和目的,必然地負載著一定的人文價值和人性底蘊。從十多年我國大陸網絡詩歌的發展來看,相對于平媒詩歌,它卻更多地體現了對傳統人文精神的解構。
國際互聯網1994年落戶中國大陸,1995年大陸即有了文學網站。網絡文學和作為網絡文學重要一翼的網絡詩歌在網羅天下的Internet上很快演出了人間的千姿百態。2000年至2001年,是網路詩歌成長最為迅速的一年,大約近二十種詩歌站點和論壇開通,各種綜合網站和專門的詩歌網站搭乘“信息高速公路”遍地開花。“詩生活”、“詩江湖”、“揚子鱷”、“靈石島”、“界限”、“終點”、“守望者”、“蒲公英”、“鋒刃”論壇逐步成長為影響較大的純濤歌網站,而以綜合欄目出現的著名的有“北大在線·文學大講堂”、“榕樹下”、“橄欖樹”、“橡皮”等。它們—般都由一個或幾個著名詩人牽頭,以自身的特色和個性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網絡世界中,網站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網站互相鏈結,攜手言歡,資源共享,人員流動,網絡寫手 (又稱“土著”詩人)可以在這充滿聲光電色、透明而敞亮的虛擬時空中像銀魚般自由穿行,不受拘束,悠悠乎詩哉!網絡的這個快樂時空很快也引來“境外”傳統詩人的頻頻光顧。現在,出沒于各種大小網站的詩人正日益增多,網絡詩歌在一個多元的文化時空中展開,隱約已經對主流詩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些優秀電子刊物儼然有與傳統詩歌刊物分庭抗禮之勢。但是,總體來說,目前的詩歌網站除了少數運作規范、質量較高的以外,整體水平還并不太好,一些網站更像人來客往、搬貨卸貨的詩歌“轉運站”或人聲鼎沸、招帖揮舞的詩歌“茶座”。
詩人楊曉民以敏銳的理論前瞻,率先將“網絡詩歌”這一命題推到了大陸文學評論的前沿。他提出“網絡世界的普及,特別是網絡的開放性、游戲性、參與性、交互性,又為詩歌徹底打通走向大眾之路開辟了一個新的視野——為現行詩歌的轉換提供了可能,為大眾閱讀、寫作、批評詩歌開辟了無限的前景。”電子媒介的出現,是人類文化傳播史上正在經歷的一次空前的革命,詩人清醒地認識到,它不僅會極大地改變詩歌傳統的書寫和傳播方式,而且直接或間接地改變詩歌自身的形態。楊曉民又將網絡上即將出現的詩歌樣式稱為“超文本詩歌”,并且清晰、縝密地發掘出它的革命性意義:“網絡詩歌”修復了詩歌與現實的關聯,拆除了詩歌通向大眾的屏障;巨大的交互性,取消了詩人和大眾的界限;語言游戲的狂歡慶典;語言的平面化和公共性;平等原則,確立了詩歌新的游戲規則。對網絡詩歌的發展前景,詩人也難以抹去心頭的隱憂,“網絡詩歌的崛起……最終意味著現行詩歌的全軍覆沒還是泛詩化時代的到來,預示著詩歌的死亡還是全面復興?”大眾傳播的全球化形式的確深刻地改變了詩人和讀者的書寫、閱讀方式,認知結構及審美心理,然而,把詩歌的復興僅僅寄希望于創作媒介的崛起和轉換,而不是創作主體精神上的復興,恐怕也是不可靠的。
1995年,美國加州大學學者、詩人杜國清提出:“由于最近開始席卷全球的國際網絡(internet)勢將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可能產生出一種新的國際網路詩學。”在中國詩史主題變遷和表現技巧“通變”的詩史發展規律中,考察詩的藝術創造、意象生成、審美想象和象征這些詩學中重要的命題和國際網路的本質、構成之間的關系,尋找兩者之間的結合點,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網絡詩學的框架。他為我們勾勒了未來詩人“在線”創作的圖景:“利用電腦掌握天下資料,再進而運思謀篇,將是今后詩人寫詩的創造方式。”“……詩人的想象操作與電腦回應的雙向互動中,產生出各種繁復多樣的藝術造境,而使電腦網路的創作發揮象征表現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同時也使創作成為詩人與電腦對話互動,而在自由自在的電腦操作發揮最大限度的想象力。”網絡世界固然可以讓詩人享受到言論自由的最大快感和聲光無窮變幻的樂趣,可是“極盡聲色的耳愉目悅”并不能和“神與物游”、“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藝術運思的美妙等量齊觀。即使網絡像佛教的“因陀羅網”一樣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天下大同、資源共享的“極樂世界”,能夠鼠標所向“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但是“信息”不等于藝術創作的才情、知識、想象力和良好的藝術直覺,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技術的進步,信息資源的占有,并不能保證現代人能創作出比前代人更優秀的詩。電腦網絡對詩創造的影響是要通過詩人、詩歌發表的場域——詩網站等諸多中間環節達成。夸大網絡對藝術靈感的激發、拓展藝術想象力空間的作用,構筑藝術疆域里新的“技術神話”使我們隱約聞到了一絲技術文明崇拜和迷戀的氣息。
由于詩歌本身的特性和詩歌網站制作者水平或現有網絡技術條件的限制,在網絡詩歌中表現得并不充分,上面提到的詩歌網站,以多媒體技術和超級鏈接方式制作詩歌作品的并不多見,在人們理想中充滿聲光變幻,融音樂性、繪畫性和高度藝術性為一體的網絡詩并沒有出現,楊曉民預言的“具有互文性質的、典型的后現代主義文本——超詩歌文本”更鮮有面世,現在人們看到最多的還只是一個平媒詩歌的網絡化形態。《互聯網時代的中文詩歌》(桑克:《詩探索》 2001年第1--2輯)、《魚戲蓮葉間》(馬策:《詩生活月刊》 2001年第3期)、《透視網絡詩歌》(小引:《界限》詩月刊第3期)、《網絡詩歌的虛假繁榮(一))》(尚冰雪:《詩江湖》月刊2002年第1期)、《需要在黑暗中呆多久》(朵漁:《詩江湖》月刊2002年第1期)、《向虛擬空間綻放的“詩之花”——“網絡詩歌”理論研究現狀的考察和芻議》湖慧翼:《界限》詩月刊第8期)等,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評述“網絡詩歌”文學現象的隨筆和理論文章,大多是網界同人的“現身說法”,不成系統,難成陣勢,整體上缺乏對于網絡詩歌的自覺的理論建構。
“網絡詩歌”并不意味著它相對傳統的平媒詩歌有著獨立的寫作方式、審美趣味和評判標準,網絡詩歌不是獨立于原有的文本詩歌存在的,無論是在“網上”還是“網下”,詩歌的最為內在的本質未變,它只是融入全球化大眾傳媒背景之中的新的傳播方式和詩歌樣式。換句話說,網絡詩歌是運用網絡這個新的媒介和載體,來創作、傳播、存儲和閱讀的新的詩歌樣式,它不僅指運用網絡的多媒體技術和超文本鏈接手段創作的詩歌,而且也包括文本詩歌的網絡化形態,也就是在網上傳播的平媒詩歌。如果用“網絡詩歌”挑戰已有的傳統詩歌的價值標準,甚至干脆拒絕“詩歌”的、“藝術”的批評,像某些前衛的網絡“土著”詩人做得那樣,就會悖離“網絡詩歌”本身的精神要旨。
當然,網絡又絕不是僅僅構成了當代詩歌和詩人寫作的一個外部環境,促成了一個新的詩壇地貌的形成,也不能把它與傳統文本詩歌的區別圈定在詩歌生存環境的好壞,發表的難易,受眾的多寡,傳播速度快慢等等表象上。“網絡”不是加在“詩歌”頭銜前面的簡單的附加值。當代西方傳播學大師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了二十世紀文化傳播學上一個劃時代的命題——“媒介即是訊息”。習慣的思維認為媒介僅僅是形式,僅僅是信息、知識、內容的載體,它是空洞的、消極的、靜態的,可是麥氏卻洞察到媒介對信息、知識、內容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積極、能動地對訊息產生重大的影響。“媒介是人的延伸”,麥氏認為媒介對人的感知有強烈的作用,并且區分了兩種媒介和人的感知結構、思維方式之間的關系:書面媒介影響視覺,使人的感知呈線狀結構;視聽媒介影響觸覺,使人的感知呈三維結構。機械媒介優其是線性結構的印刷品)是“分裂切割、線性思維、偏重視覺、強調專門化的”,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認識世界,在過去機械時代里,人成為分割肢解、殘缺不全的畸形人。“電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到整體思維的前印刷時代”,網絡時代的人是感知整合的人,是能整體思維、整體把握世界的人,“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全面發展的人”。由此,網絡媒介對詩歌創作也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和能動作用。實際上,人類歷史上哪一次書寫和閱讀方式的改變,不同時又是一次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價值標準的一次(或大或小的)重新選擇呢?用不同媒介手段閱讀和創作的人都有著相同的感受:物質的性質會直接影響到所表現的內容。電子媒介可以能動地“參與”詩歌的書寫、傳播,并且深刻影響著詩人的主體精神結構和感知、審美心理。
可是,與傳統平媒詩歌相比,網絡詩歌卻更多地表現出對傳統人文精神的解構。
網絡詩歌的匿名創作放棄了詩人對創作主體角色的承擔。網絡詩歌的寫作往往是匿名的,網絡詩人處于一種“三無”狀態,即無身份、無性別、無年齡。所有網民在同一個平臺上自由嬉戲,相互交流卻又各自獨立,這使得網絡寫作可以擺脫物欲功利的誘惑,實現藝術創作的心靈自由;又可以褪去濤歌以外的因素強加給詩歌的負載,保持詩歌的獨立品格。隨著作者虛擬和主體性缺位,詩歌寫作的責任和良知、詩人的使命感和作品的意義鏈也就無根無依或無足輕重,詩歌的價值依憑和審美承擔成了被遺忘的理念或不合時宜的信念。
法國當代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曾經從“知識與權力”的轉換機制上研究創作主體的地位和功能問題,他說:“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個社會中某些話語的存在、傳播和運作的特征。話語是一種社會權力,詩人對話語的介入,不在于如何將意義賦予詩歌文本以及詩人如何從內部調動話語的規則來完成構思,而是在話語中詩人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形式出現?它遵循一些什么規則?表現出什么功能?網絡詩歌寫作對主體承擔的卸落,正是在人文本體的意義上,用主觀代替了藝術主體,又用主觀化的客觀代替了藝術客體,最終它放棄的不僅是主體承擔,還有承擔背后的藝術責任和社會權力。
網絡詩歌顛覆了傳統平媒詩中的人文價值觀。網絡詩歌大多是從聊天室起家的,“灌水區”里的眾聲喧嘩,圖的就是言說自由和消愁解悶。人網者多是懷著好奇、休閑、交友、打發無聊、派遣孤獨等游戲性的心情發育的,這種“亞健康”精神狀態擺脫了名利等社會束縛,撕開了虛與逶迤、道貌岸然的生存面具,回避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控制。上網者只需按虛擬牡區的游戲規則扮演好自己的網絡角色,而無須承擔其他責任。以這樣一種心理定勢進入網絡詩歌創作,便是以類似巴赫金的“狂歡化”方式規避傳統觀念,鄙視主流文化,清除本質主義,直至嘲諷或顛覆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而采用非正統的、前衛的、后現代的價值觀看待世界、社會、生命和生活。如《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從網上紅到網下,說到底是在用一種土得掉渣的言辭將生活的酸楚化作一縷無奈的笑談和稀松,“翠花,上酸菜”一時間膾炙人口的背后,是對典雅、高貴、仰慕等價值觀的生動拋棄。對于網絡詩人來說煙消云散的還有傳統的價值觀念、人文傳統、道德范式和主流的意識形態,還有自身的文化身份和體現意義深度的歷史記憶。網絡詩歌創作不設防地任由顛覆的價值觀對傳統實施矯枉過正,以之充塞藝術的精神,其實是把自己的主體立場不負責任地交給了反叛和前衛姿態,從而以一種自蹈幻覺的方式滿足那已被架空了的詩歌價值選擇。
網絡詩歌的讀屏模式消解了平媒詩歌閱讀時的詩性體驗。網絡詩歌提供給人們的是屏顯電子詩歌文本,而不是紙介印刷的作品,以“讀屏”替代了“讀書”,“閱讀”變成了“觀看”,“想象”變成了“直觀”,印刷文化演變為視覺文化,是網絡帶來的詩歌媒介革命,也是后現代社會“視覺消費”對讀者詩性體驗的拆解。
讀者從互聯網上讀到的詩歌作品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屏幕上顯示的文字符號,即把傳統的平媒詩歌經過電子化處理后送進網絡供網民點擊和瀏覽,或者繞開紙質傳媒直接在計算機上完成創作,然后發送到某一網站首發,我們稱這樣的作品為“網絡原創詩歌”。另一類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絡詩歌,即利用多媒體技術把文字、聲音、圖片、圖象動畫,乃至影視剪輯等融合起來組成的網絡詩歌作品,這類網絡詩歌沒法轉換為紙介質作品,離開了計算機網絡就不能存在。不過這兩種網絡詩歌都會造成對詩性精神的漠視、對詩歌審美體驗的淡化。就文字讀屏模式來說,為迅速吸引網民眼球,一般網絡原創詩歌都要設法“讓文字動起來”。網絡詩人全憑興致,顧不上精細打磨,甚至壓根兒就不具備精細打磨的藝術素養和耐心。網上充斥著的“口水詩”和“平面化寫作”就是明證。網民在欣賞時則由于節省時間和上網費的需要,一般都是快速瀏覽,甚至一目十行,來不及細細體味,領悟不了詩歌語言內部的蘊味(假如作品中有韻味的話)。這對于以表意為主的漢語詩歌來說,是審美閱讀的大忌。語言的審美在于一個“審”字,即離不開對語言文字的仔細端詳、把玩和品評。詩歌藝術的詩性魅力是間接的、漸進的和想象的,要通過對語言形象的經驗還原、想象填充和韻味品咂才能把握其美感和意蘊,即所謂“辨于味而后可以育詩”(司空圖)。鐘嶸評價詩歌時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論及詩之意境時說:“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蘊藉深厚的詩歌煮象往往迷離恍惚,超出語表,寄于言外,其味外之味、韻外之致常常是空靈深婉、超乎象外,要靠讀者在“收視反聽”、“絕慮凝神”中心領神會,達成“神遇而跡化”、“目擊而道存”。然而,網上閱讀追求的是暢神和逸趣、自適而快心,往往是走馬觀花,大都省略了詩性體驗、審美品味和藝術感悟等重要環節,任由文字和影像從眼前飄過,卻不容去作悠悠的品咂和舒展開藝術想象的翅膀,更談不上追求藝術的精神內核和形式之美。的確,上網讀屏少有韻味,只有影像;沒有體驗,只有速度。詩歌內在的詩性被速度蒸發了,“字立紙上”的詩化平臺被聲光電屏有效地拆解了。
黑格爾說過,藝術像科學一樣也表達著理智透過現象對對象本質的認識,藝術品總要通過精神的浸潤而后進行感性的直觀,他說:“藝術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把真實的東西,按照它在精神里的樣子,按照它的整體,拿來和客觀感性事物調和(統一)起來,以供感性觀照。”網絡藝術作為人的一種認知實在的感性直觀,自然會有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應是人類精神的一種自我理解方式,詩歌歸根到底是高度個人化的創新性勞動,媒介技術手段的更新,對詩歌寫作者審美心理結構、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不能代替詩人融入深邃,隋感的智性思考,和詩人深入生命本體和藝術本體的靈魂跋涉。思想家克羅齊曾指出:藝術是一種心靈的活動,不是一種物理的事實,真正的藝術僅存在于藝術家的心靈之中,而物質形式只是真正藝術品的摹本。網絡為詩人俯仰天地、放眼古今、精神解放、張揚個性提供了一個平臺,卻不是力挽詩歌“頹勢”狂瀾的靈丹妙藥。網絡上紅旗招展、山頭林立、人多勢眾并不一定會產生大作家、大作品。詩歌進步,述需從蕩滌詩人和“詩壇”自身開始,偉大的作品的產生,最終還是要植根詩人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依賴主體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偉大人格的建構。在這一過程中重塑網絡詩歌的人文關懷、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導駕馭網絡這匹野馬,使它朝向復興新詩、朝向人的價值全面實現的精神指向上發展。電子媒體的崛起,把詩歌置于全球大眾文化傳播的背景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中國新詩應該可以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和契機,實現它在藝術領域的再次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