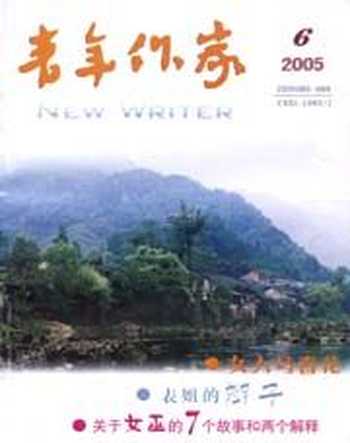平凡的日子(外二篇)
馬 夫
六點半,兒子上學,有時是鬧鐘鬧醒的,有時是我或他媽媽喊醒的。起床前,他總要伸個懶腰,仿佛要把渾身掙不脫的疲倦扯直似的。在督促的剎那,我禁不住打個呵欠。一天就這樣在懶腰和呵欠之間開始了。
過完早,我去趕交通車,妻子遞過公文包,順手把我腦后一撮翹著的頭發壓幾下。心情好的時候,我會折身接點自來水在頭上抹一抹,扭頭在菱花鏡前照一照;心情不好的時候,一句“算了”就溜出門。下樓后,還聽見妻子問中午回不回來吃飯?說不準的事兒我也懶得吱聲。
妻子原來是一家電影公司的小職員,后來安排到基層影院推銷電影票,電影業不景氣,她時常為勞無所獲犯愁。慢慢地,她也“安居樂業”,索性呆在家里燒火做飯,每天變換幾個菜給我和兒子嘗鮮,成了她最大的慰藉。要是有人喊她打麻將,她總得限個時辰,以便在我和兒子回家之前收手下廚。“三缺一”時,人家只得依她。
隨著城市的擴張,大多單位已在古城之外搶占寬綽之地。上班的車流東奔西走,瞬間就完成了士大夫到公務員的角色轉換。同事們都是熟面孔,抬頭笑笑或點點頭就算打了招呼,然后各人進各人的辦公室,掃地、換茶、擦桌椅,再把該做的事擺到桌面子上來。稍有閑暇也翻翻報紙,串個門兒聊聊天。機關資料室原來訂有《人民文學》、《詩刊》、《散文》之類的雜志,時下刪減得干干凈凈,就像荊南路兩邊的梧桐樹,一到冬季就鋸得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杈。每天大摞大摞的黨報政刊,載著同樣的內容,瀏覽了一個版本,其它的就可以擱在了一邊。稍活一點的報紙,隔三岔五的也有體育版、文學版,要看還得找半天。有時挑來挑去,挑出一張套紅的周末版來,你傳我,我傳你,也不知傳到誰的手里去了。
新修的辦公樓裂了縫,過道上的天花板也有掉下來的時候,反正現在的建筑和裝璜都這個樣子,沒人管這種閑事,上樓或下樓的步子照樣吱吱有聲。上訪的人群吵吵嚷嚷,熱心的人湊過去好話安慰一番,甚至舉自己的例子,說得與對方一樣落魄無奈;插不上嘴的或自知人微言輕者,就去忙自己的,也很泰然。重大節日,工會和政工科照樣出墻報,組織文體活動,其存在的價值沒誰小看。也唯有這種群體活動,大家才能聚攏來,下下棋,跳跳舞,嗑嗑瓜子,樂得就忘了自己生活在世紀末端。熱鬧場合,我總是坐在最角落或不顯眼處,靜靜地,像看戲,高潮還沒到,就想到了曲終人散。
這種愁緒不是沒有道理。這么多人擠在“大觀園”,好景不會太長。機構改革后,該做點什么?是辦公司,做買賣,還是到南方去謀生?聽說南方的錢也不好掙,便更加謹小慎微。我思忖:萬一下了崗,就閑下心來寫點兒作品,也算是“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吧!妻子不放心,她舉了好多文人落魄的例子,結論無非是讓我死抱著手中的飯碗。我想,她也許是在家里呆著,寂寞怕了。不然,她不會每天倚著門聽我下班的腳步聲,并從步子的輕重來判斷我的心情。
星期六照例做些形式大于內容的表面文章,或者到會議室學習,或者到大街上去掃地,也不知環衛工人到哪里去了。說不準某張金口一開,還要幫著建筑工人去砌墻,幫著紡織工人去織布呢。兒子扯著要陪他到公園玩,被妻子一把推開,我怕傷了兒子的童心,趕緊補充一句:“爸爸去掙錢供你讀書。”兒子又問什么時候搬家,我說快了快了。新樓一茬茬的,別人都搬進去了,我再找不到話來搪塞。兒子看我口氣火火的,喉嚨卻是噎噎的,似乎也明白了許多事理,就不再追問了。
傍晚,兒子要做永遠做不完的家庭作業,我只好把僅有的八平方米的書房讓給他,自己斜靠在客廳的沙發上打個盹兒。妻子或織毛衣,或洗衣服,有時也打開電視,讓我搜索能夠逗起興致的節目。從這些零零碎碎的細節中,我覺得她對生活的感受比我還深,也就孩子般地聽她擺布。
偶爾停電的時候,妻子就點根蠟燭,坐到我的身邊,慢條斯理地談著股市跌了多少,打牌輸了多少,水電費交了多少……然后淡淡一笑,一切自然又自然。那種笑,是平常人家的一種安慰,是枯菜葉兒浸水之后充盈起來的一種感覺。
重復的日子就這么一天又一天,氣候的變幻仿佛永遠被關在了門外。待上床時,才發現被子厚了些,被子上面又加了一床毛毯。我問妻子是不是該下雪了?妻子模棱兩可:“保不準兒,你看呢?”
說完,她把我的被角掖了掖,又進兒子的房間去拉窗簾……
嘎 公
王家巷稱爺爺叫爹爹,爹爹的長輩沒個正式稱呼。好在吃五谷雜糧,少有五代同堂。
嘎公姓什名誰也記不清楚了,也不那么重要,一聲嘎公就能叫出輩分。他是一個歷經幾個朝代的老人,吃的鹽比我們吃的飯還多。
嘎公是村里的五保戶。戴紅領巾的時候,我和春伢子、山羊子都爭著做好事,經常幫嘎公挑水劈柴。嘎公說伢們小,不讓干重活,經常把我們逗在一起猜謎語講故事。好多故事都淡忘了,但關于蟒蛇的傳說記憶猶新,且觸目驚心。他說從前一條蛇有馬路那么寬那么長,好多汽車在它身上跑,蟒蛇搖一下尾巴,就把汽車全打翻。一個士兵用槍也沒能把蟒蛇打死,一個管水的農夫卻用鐵鍬把它斬斷了。一直以來,我常這么想,連槍都打不死的東西,怎么能用鐵鍬斬斷呢?怕是中國幾千年來對鐵鍬的依賴在嘎公心目中留下的信念吧?一個封建王朝推翻另一個封建王朝,莫非就像布衣年復一年地用鐵鍬翻挖泥土那么簡單?這樣看來,鐵鍬的能耐不可低估。
嘎公為人慈善。每到他家,不是分給我們糖果,就是捧一瓢瓜子。有幾天我“打擺子”沒到他家,嘎公聽說后拄著拐棍來看我,送了兩個煮雞蛋。我感激嘎公黑燈瞎火的來看我,嘎公說自己反正是個瞎子,分不清白天黑夜。難怪俗話說“眼不見為凈”,我再不為嘎公辨不出黑白而擔心。
我印象最深的要數推薦上“共大”。本來名單上有我,可革委會查明我的爺爺當過保長便把我刷了下來,貧農出身的母親不依了,非得評理,并要嘎公出面否定爺爺當過保長這一事實。嘎公到革委會去了,但他那一句權威性的證詞竟把我的母親氣得半死。他說:福兒的爺爺是當過保長,可當保長那么多年,村里沒有餓死一個人……
直至恢復高考,我總算離開了鄉村,成了家,有了兒子。還經常重復地把蟒蛇的故事講給兒子聽。以至于兒子長大了扮鬼臉時,還雙手比劃著說:“好粗好粗的一條蛇,有馬路那么寬那么長……”
世界真小,夏天的傍晚上天橋納涼,竟會遇到少時的春伢子。談及老人來,他說嘎公剛過世。春伢子正跑一趟棉花生意,無暇參加葬禮。我沒心事問他生意做得如何,他也沒問及我在城里混得怎樣,彼此心中都有一種失落感。
回到家里,我悶悶不樂。妻子認為是菜炒淡了,又加了一勺鹽,邊攪和邊要我嘗嘗還淡不?我搖搖頭說嘎公過世了。兒子問是不是那個講蟒蛇的老頭?我點頭說想請假回家看看。可又一琢磨:人死一堆土,又不是親祖宗,用不著盡這份孝心。再說請幾天假,月獎金就沒了,城里的錢也不好掙,連我寫文章的煙錢也不知打哪來,不能不顧及這點蠅頭小利。
夏天,兒子放了暑假,吵著要回老家玩。正好有公差,便公私兼顧,抽身回到王家巷,打探嘎公的墳地。
土墳在黃土崗,墳地坐南朝北,四周空蕩蕩的。幾個放牛娃坐在遠處的牛背上朝我張望。這是我的出生地嗎,這么陌生?這是嘎公的墳頭嗎,這么冷清?沒有一絲青草,也沒有一個花圈!看來再長的人生,結局都是一個樣。幾個兒時的朋友認出了我,上前跟他們握手時,他們也伸出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恍然悟出來,鄉下沒有握手的習俗。我只得同時把雙手搭在了他們肩上。
王家巷靜悄悄的。靜悄悄的王家巷就這么多了一座土墳,少了一個歷史老人。
遠去的老鎮
雙河地處大洪山末端,在南方的最北部,典型的一個丘陵小鎮。由于沒有顯赫的標志,只能退求其次,以縱貫境內的兩條小溪命名。歲月就像河水中的魚尾,搖擺著一路滑行,拐彎抹角后,找到了寬闊的漢水,也找到了東方的出路。
雙河是個老鎮,當年稱區,后來改鄉,再后來改鎮。改來改去,也沒有改變酸性土壤及其河水的流向。就像我,先有乳名,后有學名,再有筆名。改來改去,也沒能改變個性。
想起老鎮,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這種滋味與生俱來,與生共有,與生同享,與生共存。就像老鎮與老屋,秋天與秋水,眼睛與眼淚。夜深了,城市的車流依舊,道路被汽笛聲壓得彎彎的,扁扁的,惟有月光細細的,柔柔的,悄無聲息地從窗口針尖似地穿透進來,灑落在枕頭上,趕也趕不走,拂也拂不去。依稀小時候躺在老家的榆木床上,看月光從亮瓦里斜映床頭的情景。記得老家的門背后,總是橫七豎八地斜放著楊叉、木锨和鐵鍬,堂屋里一張方桌四平八穩,還有篾制的篩子和簸箕……媽媽就是用這些篾制的東西篩去雜質,讓生活盡可能地潔凈一些,再潔凈一些。那屋檐下的木犁是千百年就有的,引得我往更深處想。想來想去,頂多想出一兩個側面來。謀生的人是沒有哲學概念的,比如挑在肩上的扁擔,只能被擔子壓彎,或者被不屑一顧的目光看扁。
每每回到老鎮,我就要先在老街轉轉。老鎮是由一條三五米寬的老街冰糖葫蘆般串起來的,街巷清寂,街面和人家都干干凈凈,呈現出南方獨有的素描來,順著青石板,漸次就步入了一種古樸的意境。農忙時節,趕集的人不多;即便農閑趕熱集的時候,買的東西也不多。每個店鋪里,都有一兩個主人,閑散地織著毛衣,或者做點針線活兒。見我進了店子,關切地問一句:“回家看老人的吧?”便自作主張地為我張羅開來。
老街的背后是河。河水潺潺地,一副老奶奶或者老爺爺拄著拐杖從遠古顫悠悠地走來的態勢,并順著水往低處流的道理,謙卑地流淌著。河水的兩岸開墾了許多田地,種植著水綠的顏色。看到闊葉所掩映的長長的黃瓜,我又想起小時候趁著夜幕,光著身子趟至對岸偷嘗鮮嫩的事兒。“偷”字總是與“羞”字聯系在一起,所以我沒有勇氣在人們面前提及那段往事,甚至一想起來,就羞至耳根。其實,偷字是與人密不可分的,是人的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比那欺世盜名要膚淺得多。單就母親背著我“偷偷”地流淚,惟恐辛酸的情緒感染了孩子和左鄰右舍而言,還是一種美德。
老街到了盡頭,就是一排楊柳。柳枝垂著頭,把人們帶進比老鎮還要老的村落。村落里的梯田錯落有致,數間散文化的灰瓦屋也錯落有致。高低之間,看不出一點兒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也沒有貴賤之分。如果趕到花季,桃紅梨白的樹枝,便伸出幾片俏麗。有的花落了,有的花結出了果實。盡管如此,也不能簡單地用幸運和不幸來概括。仔細思忖,花朵掛果與凋零,同樣深刻。
老鎮走的是一條老路。驀然回首,漸次有了一去不歸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