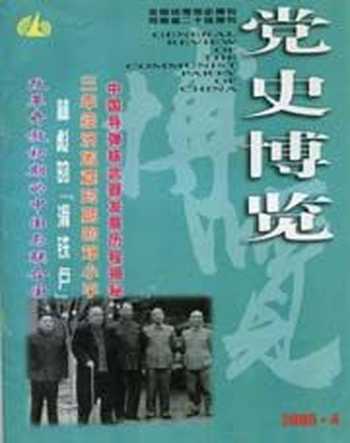張仲瀚情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陳伍國
奏響屯墾戍邊序曲
1949年秋,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十九兩個兵團進行了西北戰場上最后兩個戰役——扶眉戰役和蘭州戰役,從而基本結束了大規模的解放戰爭。
這時,各縱隊已經改編為軍的編制,一軍、二軍和七軍編為西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王震任司令員兼政委。六旅編為六師,屬二軍建制,張仲瀚任師長,熊晃任政委。9月下旬,張仲瀚隨一兵團從古城西安直取青海,翻越白雪皚皚的祁連山進擊河西走廊,挺進張掖,解放酒泉,兵臨玉門關下,直叩新疆大門。
1949年9月25日、26日,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分別通電起義,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10月1日,部隊在酒泉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會。10月上旬的一天,在西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的軍用地圖前,張仲瀚懷著興奮的心情接受王震司令員交給自己的任務。、王震把手指停在南疆北疆分界處的天山咽喉焉耆、庫爾勒一帶,鄭重地對張仲瀚說:“你迅速組織一支包括領導干部和農林、水利技術骨干在內的先頭部隊,先行到達這些地區進行踏勘布點,做好一場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新戰役——屯墾戍邊、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的準備。我已經和陶峙岳將軍通了電話,請他派一批熟悉新疆情況的技術人員先行到焉耆等候,與你的先頭部隊會合。”
10月13日,張仲瀚帶著40多名有關人員,分乘1輛吉普車和3輛大卡車,風馳電掣般地向目的地進軍。
在南疆小鎮庫米什,他們遇到持有陶峙岳親筆信的新疆省水利局局長王鶴亭、地質所所長王恒升和一些農、林、牧、水利技術人員。張仲瀚如虎添翼,更加增強了圓滿完成任務的信心。
踏勘近一個星期,張仲瀚談笑風生,了無倦意。出現在牧民獵人中間的這位氣度不凡的將軍,有時很像一個風水先生。不少人第一次從他那里聽說,開都河還曾有過通天河的美名。
到了和靖,張仲瀚還拜訪了蒙古王爺。王爺聽說來人是解放軍的師長,立即大禮相迎。和靖、和碩是蒙古人的聚集地,他們過著“天不管我我管天”的游牧生活。告辭后,張仲瀚對隨行人員說:“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中特有建樹的兄弟民族,但游牧生活終不能使他們擺脫落后與貧困。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必將刷新各族人民的歷史。”
經和碩到達焉耆后的第二天上午,起義的一二八旅旅長陳俊送帖子來請他們吃飯。然而,張仲瀚已于清晨帶著這支先頭部隊進入了茫茫草原,到開都河南岸的鐵門關踏勘去了。
1949年12月5日,毛澤東發出《關于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執行勤務者外,應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
為了響應中央的號召,加速屯墾戍邊的進程,1950年早春,張仲瀚、陶峙岳跟隨王震,帶著水利、土壤專家等隨員,踏著冰雪大地,冒著刺骨寒風,向準噶爾盆地邊沿進發。
當時,工兵團正搶修瑪納斯大橋,車不能通行,他們就挽手徒步履冰過河,沿古驛道西行,一路勘察了石河子、烏拉烏蘇、三道河子等。次日,他們繼續西行,經老沙灣縣城、奎屯、車排子、炮臺等地,接著又轉回石河子向北至老鴉窩一帶。所到之處,滿目是叢生的紅柳、梧桐和駱駝刺等,低洼處則蘆葦茂密,遮天蔽日。他們披荊斬棘,穿行其間。
此行歷時5天,行程千余公里,取得了有關新疆地理、水源、土壤等的第一手資料。經反復研究,北疆首先開展以炮臺和石河子為中心的兩大墾區。張仲瀚率領九軍二十五師、二十六師受命在這兩個墾區“作戰”。
戰火中走出的部隊指戰員們,放下武器,掄起鐵鎬和坎土曼,拉著土制犁,在亙古沉睡的戈壁荒原上,奏響了屯墾戍邊大生產運動的序曲。
千古荒原上的“戈壁明珠”
剛到墾區,指戰員們既無住房,又無帳篷,就挖地窩子以棲身。瑪納斯河水漲,道路翻漿,運輸中斷,糧食供應困難,他們就挖葦根填腹。張仲瀚風趣地說:“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以‘小米加步槍起家、發展而取得勝利的話,那么新疆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赤手加坎土曼去取得打開局面、奠定基礎的勝利的。”
張仲瀚和陶峙岳經常帶著干部下連隊參加勞動,與戰士同吃同住。張仲瀚高卷起衣袖,和大家一起挖地窩子。他說:“干這個我是內行。你們沒有趕上去南泥灣挖窯洞,今天趕上了天山腳下挖地窩子。明天的高樓大廈,就從地窩子開始吧!”
第一年,他們就做到了蔬菜、肉類和糧食的自給或部分自給。準噶爾的戈壁荒灘上,呈現出片片綠洲。
1950年夏,新疆軍區黨委決定:在瑪納斯河西岸、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建設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作為生產部隊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的指揮中心。
12月,石河子建城工程處成立,二十二兵團副司令員趙錫光兼任處長,張仲瀚兼政委。
建城工程處的首要任務是做好規劃,拿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方案來。“怎樣才是切合實際呢?這個城市應當建成什么樣呢?”幾個不同意見的方案擺在了張仲瀚的辦公桌上。為了做好這個規劃,他翻閱了不少城市建設書籍,經常向建筑工程學者、專家請教,并把自己的想法與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交換。
張仲瀚說:“所謂切合實際,并不是指僅局限于目前的經濟起點與實力,而是要著眼于適應新疆經濟發展和屯墾戍邊事業發展的需要和要求。用這個觀點看,把石河子規劃為1萬人的農業城市是不適應將來的發展要求的。糧食、油料、皮毛的加工,機械的維修和制造,有許多不是農業自身所能解決的。……我們正在進行的農業生產僅僅是極微小的開端,我們兵團的農業將是現代化的、大規模的。發展農業的結果,必然要發展工業。有工業,才有城市,城市是發展工業的結果,是為工業(同時也是為農業)服務的。”“城市能容多少人,不是地面能住下多少人口,而是城市的經濟能力能養活多少人口。”
為此,張仲瀚親自設計了一個方案i為使這個新城市具有民族氣息和中國氣派,將整個形狀規劃為長方形、棋盤式和開放型的,可以擴展,可容15萬至20萬人口。增加了工廠、學校,城市中心規劃為行政區,四周為文教、工業、商業發展區,林帶花園環抱著一個個居民區。
1952年,在石河子城規劃區的中央,第一座行政辦公大樓拔地而起。次年,小禮堂落成。
隨后,張仲瀚又用了5個年頭,在實踐中對這個方案進行修改和完善,并于1958年正式形成了石河子新城的規劃,使石河子發展成為現在享譽中外的一顆璀璨的“戈壁明珠”。
邊疆處處賽江南
1954年10月7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由陶峙岳任兵團司令員,王恩茂兼任兵團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張仲瀚任兵團副政委、黨委第二書記。
剛開始,有不少戰士甚至領導干部對此不理解,議論紛紛:“新疆軍區分兩支部隊,一支打仗,一支生產,這不是很好嗎?為什么要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呢?”“軍不軍,民不民,二轉子,還不如解甲歸田,回老家去!”“‘莊稼兵沒干頭,干脆打報告到現役部隊去。”
針對這些思想,張仲瀚用心研究了歷代守備邊疆、屯田以定西域的大略方針,聯系南泥灣大生產的經驗,逢會必講,逢人便說,宣傳毛澤東寓兵于農的思想:“我們兵團是一個特殊兵種,又是軍又是民,‘兩個護,一個團結,左手擁政愛民,右手擁軍優屬。中心是在新疆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領導下,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繁榮富強的新新疆。自古以來,當兵吃糧餉天經地義,而我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則不吃軍糧,不拿軍餉,不穿軍衣,平時創造物質財富,戰時消滅敵人。試想:我們現有10萬轉業軍隊,將來還要發展到幾十萬、幾百萬人,一年將會為國家創造多少財富,節約多少軍費啊!”
講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性質時,張仲瀚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既不是現役的、正規的人民解放軍,也不是一般的國營農、牧場或企業,中央要它保持解放軍的光榮稱號和組織形式,正是為了讓它繼續發揮人民解放軍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和工作隊的作用,擔負起屯墾戍邊的重任。這就是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在新疆這種社會、地理、歷史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運用和發展,是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結合。歷史終將證明,這是我黨屯墾戍邊的一個歷史創舉……”
后來他把這種思想抱負凝練成一首七言詩:
雄師十萬到天山,且守邊疆且屯田;
塞上江南一樣好,何須爭入玉門關。
每有干部來找張仲瀚提出調動或返內地時,他就把這首詩拿出來“請教”,往往使對方愁眉緊鎖而來,眉開眼笑而去。
兵團成立后,張仲瀚敏銳地提出“積極發展,慎重穩進”的方針,每年以增加5萬至10萬人的速度擴展,掀起了建設正規化國營農、牧場的高潮。
與此同時,一股“只能進行農業,不能進行多種經營”的冷風,阻礙著兵團事業發展的步伐。面對這股冷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部的一些干部也產生了糊涂認識和消極情緒,提出要“重新考慮兵團的組織形式”和“雙重領導關系問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由國家農墾部和新疆自治區雙重領導,以自治區為主),“把兵團交給地方”;認為“兵團發展速度太快了,工業辦得太多了”,“兵團發展生產越快,對民族團結越不利”。
在國家農墾部部長王震,以及新疆自治區黨委的支持下,張仲瀚等兵團領導堅決抵制了以上屯墾戍邊事業發展的阻力,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得到了大發展,迎來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事業的昌盛時期。建立“邊境農場帶”,鑄祖國鋼鐵長城
“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斗的武器,捍衛祖國的安全與領土完整。”
張仲瀚牢記毛澤東1952年對解放軍一部分整編轉為生產部隊時的教導,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之日起,他就堅定不移地按毛澤東“三個隊”(生產隊、工作隊、戰斗隊)的建軍思想建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行以農為主,工農兵學商并舉,勞武結合的方針。
張仲瀚多次強調:“屯墾戍邊,不能只抓坎土曼丟了槍桿子。我們處在祖國的西大門,面對著綿延萬里的邊境線,毛主席叫我們保持人民解放軍的組織形式,正是要我們繼續執行‘三個隊的任務。對此決不能打折扣。隨著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們兵團‘三個隊的任務次序、側重可有不同。現在我們把‘生產隊擺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隊和‘戰斗隊。重點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但‘三個隊必須并存,必須結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缺一不可。”
1962年4月,新疆伊犁、塔城地區部分邊民在外部勢力的策動和誘騙下外逃。當時,張仲瀚剛從北京開會回到蘭州。一天晚上,他剛躺下休息,就接到周恩來辦公室的電話:“張政委,明天派專機到蘭州接你返京,總理有事安排。”
次日,張仲瀚一回到北京就火速趕到王震家,才得知新疆邊境發生的情況。晚上6點半鐘,他隨王震來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分析了伊、塔邊境事件的形勢,講了黨中央處理此事的方針和政策,用深沉的語調對張仲瀚說:“你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處理比較合適。這可以說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吧。”隨后,周恩來向他明確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民兵在邊境斗爭中的任務、方針、政策和策略,要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對邊民逃出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工作實行“代耕、代牧、代管”。
張仲瀚向周恩來堅決表示:“我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定全力以赴,落實周總理的部署。”
次日,張仲瀚火速趕回新疆,向自治區黨委匯報了周恩來的指示,并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會上作了緊急安排。在此嚴峻時刻,張仲瀚主動協助自治區黨委指揮,勸阻邊民外逃和制止事態發展,火速調集、組編一定數量的民兵值班連,沿中蘇邊境布防。同時,警衛地州黨政辦公機關,維護了社會治安。
這年夏秋之交,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到新疆檢查工作。張仲瀚總結匯報了執行“三代”任務的經驗,并正式提出建議:在“三代”的基礎上,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沿邊境建立“邊境農場帶”以鞏固邊防;同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不脫產的民兵形式,建立在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上相當于正規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值班部隊”,完全生產自給,不支用國家軍費,只由國家裝備武器。以“民兵”為形式,可以隱蔽力量。這個建議由雷英夫轉報中央軍委后,很快就獲得批準并電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于1963年組建一批如上標準的值班部隊。到1965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在中蘇、中蒙1300余公里的邊境線上,建成了一條包括幾十個農場、縱深寬達幾十公里的邊境農場帶,筑起一道堅強的屏障。
1965年7月,周恩來到新疆視察工作時,檢查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建設。他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現在已經有一部分主力,但還不夠,還要進一步建立第一線部隊,既生產,又工作,又能戰斗。
身在北京,心在天山
從踏上新疆這塊寶地屯墾戍邊的第一天起,張仲瀚就非常注重鉆研生產科學知識,提倡科學種田,科學管理,按科學辦事,并經常虛心向教授、學者、專家、勞動模范請教。
張仲瀚每到農場、連隊檢查工作時,對縱橫交織的排水渠道總感到心情沉重不安。他面帶難色地說:“我們這是在干既挨打又受罰的傻事,挖了排水渠就等于給地判了無期徒刑。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兵團的農業就會在鹽堿面前打敗仗,當逃兵。馴服水土是決一死戰。”他狠狠抓住這一關鍵,廣泛聽取專家、技術人員和干部群眾的意見,親自召集農、林、牧、水利等各專業干部座談。同時,組織干部到連隊蹲點搞試驗,探索對土壤變化發生作用的諸因素及其活動規律。終于總結出一套綜合土壤改良的措施:平整土地,渠道防滲,重新規劃,改造條田;牧草合理輪作;農牧結合,種植林帶和培植林區并舉,避免用挖排水渠的方法。
20世紀60年代初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事業蓬勃發展,充分展示了它在新疆的戰略作用和地位,黨中央決定在西北五省區推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經驗,大力發展生產建設兵團事業。
為此,周恩來在京兩次召見張仲瀚,傳達中央意圖:決定組建一個西北農業建設兵團和一個西北林業建設兵團,并明確指示,兩個西北兵團都讓張仲瀚來管。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中央西北局成立一個領導兩個兵團的領導小組,你參加這個領導小組,具體抓這一工作。”
張仲瀚堅決、迅速地執行周恩來的指示,兩年內選調了從師到團的管理、業務、技術干部,支援成立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團(后改稱西北林業建設兵團)。之后,他又按周恩來的指示,選調干部和戰士成建制組成了一個2000多人的農業建設團去西藏支援建設。
正在張仲瀚為西北生產建設的宏偉藍圖而歡欣鼓舞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兵團的某些領導人利用傳達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機會,公然宜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全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典型,存在著激烈、嚴重的階級斗爭,有些單位的領導權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人掌握,做了許多壞事,要把他們徹底打垮,一個也不能放過……”
面對一連串非難和打擊,張仲瀚想不通;“一個月前,《人民日報》還決定用8個版面的篇幅連續宣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就和經驗,稱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偉大的創舉。而一個月后的今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怎么成了全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典型呢?”“周總理要推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經驗,要我把新建的兩個西北兵團都管起來的話音還未落,怎么一夜之間連我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呢?”“毛主席歷來肯定新疆和平起義有功,為什么現在陶峙岳卻成了‘假起義、真潛伏的罪人呢?我黨一向肯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造起義部隊是成功之舉,為什么現在又被戴上‘階級投降,國民黨改造了共產黨的罪名呢?”
8月25日,新疆自治區黨委三級干部會議在昆侖賓館召開,兵團某位領導人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的小組會上宣布,“揪出了以張仲瀚為主帥、賀振新為副帥的反黨集團”,號召大家起來揭發批判。
眼看紅紅火火的兵團事業要毀于一旦,張仲瀚著急、憤懣,又無可奈何,最后終于病倒了。但他仍竭力安慰和鼓勵來醫院看望自己的同志:“在任何壓力面前,堅持實事求是就是最好的斗爭。必須堅信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方向是正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7年的巨大成就就是不容抹殺的客觀存在,歷史的發展定會做出公正的結論。”
1967年1月,江青公開點名批評張仲瀚:“張仲瀚是王震的一個打手,是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張仲瀚終于被扣上“歷史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了。3月,他在北京被強行投進了監獄。
在8年零3個月的漫長監獄歲月中,張仲瀚多次上書周恩來、葉劍英和韋國清,陳述自己的觀點,希望中央對這場斗爭作出公正的結論。
1975年春,經周恩來精心安排,排除阻力,將此事交鄧小平操辦,向毛澤東遞交了關于盡快落實政策、釋放張仲瀚的報告。毛澤東親自批示:“張仲瀚原是部隊的人,還叫他回部隊去。”這年5月15日,張仲瀚終于被解除監護,住進了總政招待所。,
1979年12月17日,經中央軍委審查批準,總政治部作出了《關于張仲瀚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為張仲瀚恢復名譽,平反昭雪。
由于張仲瀚的身體備受“四人幫”嚴重摧殘,加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已被撤銷,葉劍英勸他留在北京,“住院治療,盡快恢復健康”。同時,中央軍委任命張仲瀚為解放軍炮兵顧問。
在這段時間里,張仲瀚身在北京,心在天山,無時無刻不想念著新疆,想念著被林彪、“四人幫”橫加破壞的西北屯墾戍邊事業:“如果說我一生中有過最傷心的事,那就是被迫離開了新疆。我只要一閉上眼睛,就恍惚回到了新疆,看到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看到了那里勞武結合、改天換地的軍墾戰士。”
1980年3月9日,張仲瀚在北京逝世,永遠離開了他魂牽夢繞的生產建設兵團和那些勤勤懇懇的軍墾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