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告別人生舞臺
黃秀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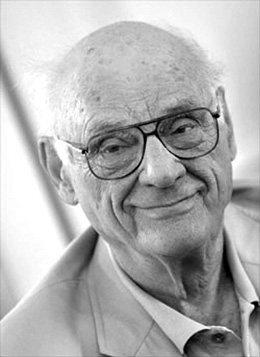
1956年7月1日,劇作家阿瑟·米勒和好萊塢性感影星瑪麗蓮·夢露結(jié)婚,輿論嘩然,用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的話說,他們的婚姻把“偉大的美國大腦”和“偉大的美國肉體”結(jié)合在了一起。米靳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和人們茶余飯后談?wù)摰脑掝},其所帶來的知名度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他的作品獲得的無數(shù)獎項。半個世紀(jì)后,當(dāng)享年89歲高齡的劇壇泰斗由于心力衰竭生命消逝時,再一次被媒體與夢露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炒得沸沸揚揚,仿佛,只有借助美人的名聲,劇作家的地位才能永遠(yuǎn)光輝燦爛。
在蜚聲美國劇壇之前,阿瑟·米勒曾飽嘗了生活的艱辛和貧困的滋味。米勒1915年出生于一個沒落的猶太商人之家,中學(xué)畢業(yè)后,因交不起學(xué)費輟學(xué),做些零工賺錢,點滴積累起來的錢使他得以到密執(zhí)安大學(xué)新聞系讀書,后轉(zhuǎn)入英文系,開始創(chuàng)作劇本,但一直默默無聞,直到1947年,其社會道德劇本《全是我的兒子》一舉獲得成功,初步奠定了他在美國戲劇界的地位。真正使他在美國劇壇持久立足的是1949年首次搬上舞臺的《推銷員之死》。這一“現(xiàn)代美國悲劇”轟動了美國戲劇界,創(chuàng)下了連演742場的記錄,奠定了他在美國戲劇界的大師地位,并為他一舉贏得了三項大獎:“普利策戲劇獎”、“紐約戲劇評論界獎”和美國舞臺成就最高獎項“托尼戲劇音樂獎”。
主人公威利·洛曼做了一輩子的推銷員。兢兢業(yè)業(yè)的他雖然盡心竭力地做著本職工作,卻由于工作不利遭到老板解雇,“成功”的夢想破滅了,事業(yè)已經(jīng)山窮水盡,威利步入了人生的低谷。他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兒子們卻讓他傷心透頂。大兒子比夫曾是他的驕傲。中學(xué)時,比夫是校橄欖球隊的隊長,倍受同齡人崇拜,在紐約最著名的球場參加過全市錦標(biāo)賽,有三家大學(xué)爭著讓他到自己學(xué)校,但是,比夫卻因為數(shù)學(xué)不及格連中學(xué)都沒畢業(yè)。自此,他破罐子破摔,自甘墮落,到處游蕩,至今無一份固定工作。二兒子哈利則四處拈花惹草,吹牛混世。一家人只有妻子林達(dá)理解、關(guān)心和體貼他,時時給他一絲活下去的勇氣。工作和生活的雙層重壓使他身心疲憊、精神恍惚,眼前時常出現(xiàn)幻覺,仿佛十年前故去的富翁哥哥就在他身邊,時時和他對話,他的精神總是處于不正常的亢奮狀態(tài)。父親對兒子的失望和兒子對父親反常舉止的指責(zé)使父子開始激烈爭吵,林達(dá)在極度痛苦中不得不告訴兒子們:威利每月都向朋友借錢假裝工資拿回家里;他幾次故意把車開向河里企圖自殺,還在煤氣灶下另接一根橡皮管。受到震撼的兒子們良心發(fā)現(xiàn),試圖振作起來安慰父親。第二天,威利去找老板,企圖用自己一輩子對公司的奉獻(xiàn)精神打動老板給自己一份固定工作和薪金,老板斷然拒絕了他每個星期40美元的最低請求。比夫去找過去的老板借錢出無功而返。哈利在請父親吃飯時又勾引一個女人,拋下了父親。回家后,父親和兒子幾乎大打出手,盛怒之下,比夫拿出橡皮管揭穿父親,自己卻情不自禁痛哭流涕。猛然間,威利欣喜若狂地意識到兒子依然愛著自己,他義無反顧地斷然將自己醞釀已久的計劃付諸了實施:制造一起撞車事故,給兒子留下大筆保險金。事態(tài)炎涼,他生前的商界朋友沒有一人參加他的葬禮,他沒能像生前希望的那樣永遠(yuǎn)活在朋友心中,最后一個夢想也破滅了。

故事僅僅發(fā)生在24小時之內(nèi),米勒卻運用倒敘的手法展示了威利的一生事業(yè)生涯。在生命的最后的一天,他時刻在尋找著自身和兒子失敗的答案,思索中,他總是把哥哥本作為衡量自身成就和行為的標(biāo)準(zhǔn)。本是美國西進(jìn)運動的先驅(qū),17歲邁進(jìn)西部的原始森林、21歲即成為大富翁,他是實現(xiàn)美國夢的原型,集先驅(qū)者的冒險精神和勇敢、堅毅于一身。而威利與本截相反,他夢想“成功”,卻又又不愿冒險。當(dāng)年,本曾邀他一起去西部,他卻舉棋不定。恍惚中,他仍然感覺到本在勸說自己到西部發(fā)展,林達(dá)卻一直設(shè)法阻止他,最后,林達(dá)戰(zhàn)勝了本,威利決定留在東部城市,但他又不安于過平淡的生活,“成功”的夢想一直在遙遠(yuǎn)的地方頻頻向他招手。他涉世之初之所以選擇做推銷員,是因為他認(rèn)為這一職業(yè)能給他帶來巨大的成功感,像他的一個前輩,在80歲高齡還能去二、三十個城市,死時幾百人都來參加他的葬禮,“一連好幾個月火車上都是一片傷心景象。”工作并非如他所愿,“成功”遲遲沒有到來,而且,由于上了年紀(jì),推銷不利,又遭到了解聘的下場,“夢”破滅了。希望寄托到了兒子身上,比夫中學(xué)沒能畢業(yè)的事實給了他致命的打擊。事實上,“比夫夢”破滅的癥結(jié)卻在自己身上。在波士頓一家旅館,比夫撞見父親和別的女人在一起,一度屬于母親的絲襪套在了其他女人腿上,父親在自己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轟然倒地,比夫自此失去了對未來的幻想,并自甘墮落。威利承受著雙重夢想破滅的雙重痛苦,他恍惚、夢囈,生活在幻覺世界中,清醒帶來的只是失敗感。
劇作中,米勒精心地將現(xiàn)實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手法結(jié)合起來。舞臺上,時空界限被徹底打破,燈光的切換表現(xiàn)著時空的轉(zhuǎn)移,甚至不同的時空同時出現(xiàn),整個舞臺夢幻般變換不定。米勒取消了假想中的墻壁,“現(xiàn)實”場景里的人循規(guī)蹈矩,“過去”場景里的人物則穿越墻壁自由行動。威利潛意識中的哥哥本隨時隨地在舞臺上出現(xiàn),打斷“現(xiàn)實”人物的對話,牽引他們的思路,這樣,威利不停地以內(nèi)心獨白和自言自語的方式與代表著自己分裂意識的本進(jìn)行交流,宣泄著內(nèi)心的苦悶與壓抑。通過這種表現(xiàn)主義手法,威利頭腦中的活動成功地展現(xiàn)在舞臺上,觀眾了解到人物的過去、現(xiàn)在和夢的開始、破滅,意識到了主人公在家庭和事業(yè)中的尷尬處境。
繼《推銷員之死》之后,1953年在百老匯上演的米勒另一力作《煉獄》,進(jìn)一步鞏固了他在美國劇壇的地位。該劇作取材于1692年清教統(tǒng)治時期發(fā)生在馬薩諸塞州的驅(qū)巫案,影射和諷刺了20世紀(jì)50年代麥卡錫主義在反共狂潮中的興風(fēng)作浪及其所造成的血雨腥風(fēng)和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
阿瑟·米勒的畢生努力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成就,成為與尤金·奧尼爾和田納西·威廉其齊名美國劇壇并獲得世界認(rèn)可的著名劇作家,米勒被人稱為“美國的易卜生”。此外,他還是美國戰(zhàn)后歷史中較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與批評者,被人們稱為“美國的良心”。看來,不需要借助瑪麗蓮·夢露的名聲,阿瑟·米勒照樣能夠名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