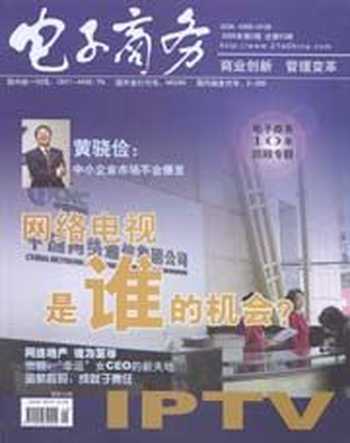軟件產業:印度的天堂
曲玲年

印度是我們的鄰邦,但在我的印象中,印度卻是神秘而遙遠的國度。很久以前的記憶是曾經發生過的中印邊境戰爭、吹笛的舞蛇人,再有就是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唐僧取經了。去年10月去印度考察軟件產業,才有機會第一次踏上印度的國土。
我們的航班由北京始發,經停上海到德里再轉機去印度的軟件之都——班加羅爾。在上海,一大批印度錫克族人由加拿大經上海回印度,搭乘我們的航班,他們像搬家一樣帶了大量的行李,使得飛機不堪重負,不得不在重慶降落加油,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飛機到達德里時已經整整晚點6個小時。這時離去班加羅爾的航班起飛只有不足40分鐘了,德里分別有飛國內和國際航線的兩個機場,機場間還有40分鐘車程,幸好旅行社的接待導游提前為我們換出登機牌,我們緊趕慢趕,還是讓航班等了我們30分鐘。轉移機場的路上有幸一睹德里的風采,真是不敢恭維。沿途豪華住宅與貧民窩棚穿插其間,轎車、大客車、機動三輪和悠閑的老牛在道路上占據著各自的空間,擠在一起,路上很難分出有幾條行車線。老實講,印度這時給我的印象急轉直下,我很難將印象中的軟件外包王國與眼前的景象連接起來。我的頭腦中開始產生疑問,如此環境能生產出高質量的軟件嗎?
我們的訪問團,是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托,由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團,赴印度考察軟件產業,并肩負著促成印度企業與中國企業合作的任務。印度方面十分重視我們的訪問,我們先后拜訪了印度最大的四家軟件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會見了十幾家中小軟件公司。在印度排前四位的軟件公司都由副總裁級別的高級管理人員親自接待,迎接的規格也高過我們的預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中國軟件產業的了解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十幾天的印度之行結束時,印度軟件產業給我們每一個團組成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軟件產業的起步還應從上世紀70年代算起。當時由于外匯管制和限制外資占企業股權比例等原因,大型跨國計算機企業先后離開印度。印度政府只能靠自力更生來建立自己的計算機工業部門,印度的軟件是伴隨國家計算機工業戰略而發展起來的。而正是這被逼無奈情況下所積累的經驗,成就了印度軟件產業今天的大發展。
介紹印度的軟件產業,我更愿意從軟件園說起。以前我在IBM和NEC都工作過,參觀過IBM在美國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研發基地和NEC在東京附近的開發中心。作為國家軟件產業基地的評審專家,我到過中國11個國家級軟件產業基地中的多數軟件園。平心而論,僅從軟件園區的比較,也可以看出我們與印度軟件業之間的差距。班加羅爾的軟件園,不再是物理園區,而是以國際衛星通信和高速寬帶網絡為基礎形成的虛擬軟件園區。印度的大、中型企業都在虛擬園區的平臺上建設各自的物理園區。一些知名公司如TCS、Infosys、Wipro和 Satyam,不但都有自己頗具規模的軟件園,而且還不止一個,是兩三個甚至更多。以Infosys為例,不但有幾個軟件開發生產園區,還有專門用于培訓的,具有萬人培訓能力的培訓園區。

訪問Infosys在班加羅爾的園區時,園區正在建設編號39和40的開發大廈,據說這個園區每年都有新的一批建筑落成,公司在快速成長,新樓在不斷落成。訪問團三年前來過這個園區的人說:今天的規模已經是三前年的三倍多了。Infosys公司2000-2001年財政年度軟件出口銷售收入為2億美元,2003-2004年度突破10億美元大關,預計2004-2005年度達到15億美元。
以前我總以為印度的軟件企業只是給美國和歐洲的企業打下手,簡單講就是做數據錄入、代碼轉換、簡單測試等底層工作,沒有技術只是勞務,賺的是辛苦錢。此次訪問印度進入軟件園,立刻發現我的理解錯了。因為如果是我以上的理解,Infosys不可能建設如此規模和如此漂亮的軟件園。
在印度城區內,不管是德里還是班加羅爾,給我的印象有點像我們上世紀70-80年代城市的感覺,但衛生條件與我們當時比卻差得很多。市區主要干道上隨處可見成堆的垃圾,老牛和烏鴉在垃圾中尋找食物,多數人衣衫不整,汽車一停,立即就有乞丐上前操難懂的英語向你乞討。
印度的軟件園,一般坐落在靠近市區的近郊,園內與園外反差之大,給人以跨越時空的感覺。所以當我們進入軟件園以后,不禁要問這是在印度嗎?國際水準裝修的現代建筑,錯落有致地散落在花草樹木之間。整個園區綠樹成蔭、大片的草坪配合點綴其間的水面和小橋以及各式噴泉,整個園區就像一幅美麗的圖畫。尤其是Infosys在遠郊的培訓中心,更加美不勝收,淺紅色的別墅散落在大片的綠地上,大型熱帶植物環繞在建筑四周。建筑內的起居條件遠遠超過我們在班加羅爾住的五星級賓館,許多被征用了土地的農民被雇來澆灌和照料這里的一草一木,園區讓人留連忘返。在園區內工作的人群,無論是精神狀態還是衣著服裝都與園區外有著天壤之別,使人無法聯系在一起想象。所以有人講:在印度,通過勤奮學習而進入IT產業工作,就像從人間一步跨入天堂。我們在園區里找到了印度IT產業界人士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理由。
經過深入交流后我們才知道,印度的軟件產業早已今非昔比,正如我們常講的,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印度的軟件產業就像中國的城市建設一樣,幾乎每一年都發生不小的變化。如Infosys公司,2004年已有三萬多名員工,而且還在以每月一千人以上的速度在發展。最值得自豪的是在三萬多名員工中,有兩千七百名具有用戶經驗的咨詢團隊、公司有一批年齡在45~55歲之間有經驗的銀發族,他們是公司的脊梁。Infosys公司在10個應用領域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軟件包。今天許多印度公司在海外建立了到岸支援的分支機構,有實力與所在國(尤其在北美市場)的一流企業一爭高下。
按照國際上一般的水準,經營有效且具有規模的軟件外包企業,其利潤率一般在30%上下。我們國內規模較大的外包企業也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水平。但與印度企業相比,我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差距。以北京達到30%利潤率的企業看,是在經營者以有效手段,嚴格控制預算支出的情況下獲得的經營業績。而印度企業要維持如此豪華的軟件園區和員工培訓所需的大量投入時,卻仍能保持30%的利潤水平,說明他們取得的外包單價遠高過我們,進一步講他們的市場價值超過我們。據他們自己講:在美國取得的合同價格,已經與當地公司不相上下。這進一步證明,他們的技術實力和品質得到了市場的認可,其市場地位正在由卓越向不可替代轉化。
我國的制造業已經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被譽為“中國制造”。我們的軟件與服務業,正在走向世界。以我國現有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基礎,我們是印度最可能的競爭者。我在微軟和Gartner的朋友都曾講過:中國的軟件產業要走向國際,印度是最好的老師。本次的印度考察之行可謂是通過身體力行,驗證了朋友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