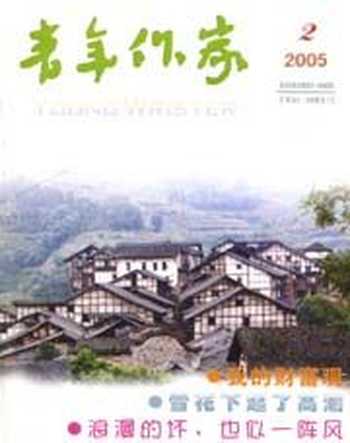生命倫理的詩性闡釋
楊傳珍 杜紫微
當寫夠了那些閃閃發光的思想隨筆之后,摩羅的文學生涯才真正開始。他的第一部小說就寫成了思想、信仰、學養與詩的結晶體。
杜紫微:我是摩羅思想隨筆的忠實讀者,反復研讀過他的《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隨筆、評論集。我一直認為,摩羅能把思想隨筆寫到這個高度,就此封筆,在文學史上也會擁有不朽的地位了。沒想到,他又拿出了這部名叫《六道悲傷》的長篇小說,在浮華的中國文壇上立起了一座青銅般的不朽豐碑。
楊傳珍:《六道悲傷》的問世,說它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重大事件,可能為時尚早,但一點都不為過。我可以作個比喻,如果我們把中國新文學的先驅魯迅先生比作俄國的果戈里,那么摩羅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六道悲傷》與老陀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相比(我堅信,有朝一日,摩羅會寫出他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無論是藝術高度、思想深度、信仰亮度還是作品之于作家的意義、對民族文學的貢獻,前者都不比后者遜色。
杜紫微:在閱讀這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時,我完全沉浸在作品所營造的藝術氛圍之中:她有著厚重深沉的血土氣息,也有著清涼淙淙的憐溪水的氣息,有著大鳴山神秘哭聲的悲涼氣息,也有著每天清晨濃郁而溫暖的煙火氣息。作者帶領我們走進的是一個既特別又普通的南方村落,她坐落在鄱陽湖邊上,幾經興衰,曾經被突如其來的蛇陣、虎陣滅絕,也曾被戰火洗劫一空。故事就發生在這么一個名叫張家灣的村落里,那看似靜謐的氛圍之下正孕育著一場空前的浩劫。因為讀第一遍時,完全被作品的內在力量所征服,我不得不讀第二遍,以便站在一個適當的距離來欣賞評析。
楊傳珍:你認為《六道悲傷》所表達的核心是什么?
杜紫微:核心是對所有生命的敬畏,是對一切尊嚴的肯定,對人類、對自然界的一切生靈、對社會、對文化、對善惡、對信仰、對生存、對宇宙、對過去現在未來,以及這些疇區之間的交叉關系的深層思考,并把這些思考提升到生命倫理的高度進一步審視,用存在論(而不是辯證論)的美學觀作藝術本體意義上的闡釋。《六道悲傷》是一部思想者、信仰者、學者的作品,也是一部詩人的作品。它的深度、高度、厚度、密度自不必說,僅作品所具有的詩性,就使得《六道悲傷》成為一部長篇小說經典。而且,它的詩性不僅表現在語言上,更表現在結構布局、人物塑造、環境描寫、氛圍營造上。當然,說它具詩性,并不是說它的思想性低于藝術性。
楊傳珍:摩羅是以思想者的身份在中國文壇出現的。他已經發表的超過百萬字的思想隨筆,多是以理性態度對社會政治倫理某些方面的置疑,而不僅僅是對某些社會丑惡現象的批判。所以,摩羅在思想文化界剛一亮相,就和那些風云知識分子有著明顯的區別,他體現出的是一個責任倫理主義者的高貴品格。而且,他早期的思想隨筆,就隱含著由文化到哲學,由思想到信仰,由關注社會到關注生命本身的質素。到了創作《六道悲傷》時,這些潛在的質素走到了前臺。我們不妨說,摩羅的隨筆,雖然是漢語寫作難得的精品,卻是《六道悲傷》的鋪墊和預演,是為了打造出這部大書而進行的創作心態和心力的準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人在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之前先去處理的零碎事物。當寫夠了那些在思想文化界閃閃發光的隨筆之后,摩羅的文學生涯才真正開始。所以,對摩羅的小說,我們不必擔心其思想性,只怕思想的深刻與密集影響了詩性。可他畢竟是一個詩性化的思想者,第一部小說就寫成了思想、信仰、學養與詩的結晶體。
人,喜鵲,蛤蟆,雞,豬,狗,泥鰍,山,水,樹,石,這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著活潑潑的靈性。
杜紫微:中國的文學,沉寂了半個多世紀。在魯迅、沈從文之后,長篇小說創作一直是乏善可陳。再不出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五四新文學所倡導的精神就要脫氣、斷檔了。
楊傳珍:摩羅的出現,不僅續上了魯迅、沈從文等文學大師的血脈,而且使得這一文學傳統有了新的生長點。
杜紫微:什么生長點?
楊傳珍:魯迅是思想大家、美學大家、小說大家,勇于面對黑暗、承擔痛苦,是心靈黑暗的在場者。他勇于把荒誕的存在還原為荒誕,從而徹底擊碎了瞞、騙、躲的傳統,穿透了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也穿透了中國美學。可是,魯迅用陰、冷、黑、沉、尖、辣、烈的心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他那里,溫煦和悲憫的比例太小,占主流的東西是敵意、荒寒、冷漠。究其原因,是魯迅在面對丑惡時,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策略。他企圖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控制,結果反被他所憎恨的傳統文化所傷。他的精神深處,缺少信仰之維、愛之維。而摩羅就沒有這種局限,在他的作品里,那敘述者的聲音雖然同樣是大地荒寒在場者的聲音,但字里行間彌漫著溫柔、善良、寬容、純潔、燦爛、堅強,罪惡之上,有愛、有信仰。摩羅超越了最初滋養自己的文化,也超越了自己。在超越中,不僅僅是批判、揚棄、否定、清算傳統,而是向傳統中注入新質。這種新質就是新的生長點。
杜紫微:《六道悲傷》中的男女主人公張鐘鳴和許紅蘭,是作者傾其全部創作熱情塑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我認為,這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畫廊里,都是新的成員。張鐘鳴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懷有一顆異常善良而柔弱的心,在他的世界觀里,一切生靈都應該受到應有的尊重。人,喜鵲,蛤蟆,雞,豬,狗,泥鰍,山,水,樹,石,這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著活潑潑的靈性。雖然這些人類之外的生命無法用人的語言與人的世界交流,但是,它們是人類不可忽視的同伴,同是自然的造化,享受著同一片陽光。人類與自身與周遭生靈的相處,應該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愛的,而不是互相殘害。《六道悲傷》里的愛與恨不局限在人類自身,它還展示了人與人之外的生靈的關系,展示了人之外的不可忽視的生命存在和力量,展示了人作為人應該具有的美好的精神境界,由“人倫之理”擴展到所有生命之理。張鐘鳴是一個弱書生,可他的弱卻讓他不能容忍任何生命受到不該遭受的傷害和欺侮。這種弱是一種高貴的品格,是基于對他類生命的認同與尊重之上的愛。同時,張鐘鳴也具有另一種弱,那就是在面對冷酷無情的現實生活時,不由自主地被外在強大勢力所左右的軟弱,這是讓人心疼的軟弱,為了自己的這個弱,張鐘鳴的內心充滿了無限痛苦。他直面自己的軟弱,與自己的靈魂進行斗爭,因而,他的痛苦是常人難以體會的。
楊傳珍:福樓拜有一句自白,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我認為,張鐘鳴是一個徹底的生命倫理主義者。這個人物,有作者自我審視的因素,從他身上,可以發現作者的影子。普通讀者心目中的摩羅,是一個血性十足的知識分子,他敢于面對黑暗,揭露丑惡。但是,那只是他內在精神的一個方面。如果你細細品味摩羅的隨筆,透過表層向深處看,他那些關于社會結構、政治道德、秩序倫理的追問與審思,其底色和根基是利他、尊嚴、敬畏、信仰,他沒有將自己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停留在對各種不合理社會現實的抨擊、批判上,甚至也沒把改善政治源頭作為自己的目的,他的思索和言說,是為了安置“更大的秩序”,即“造物主的記憶”,最終,通過建立生命倫理,實施對茫茫宇宙間一切生靈的保護、悲憫和拯救。而現實生活中的摩羅,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從他的隨筆中讀到的那個寫作主體形象,正是作者真實內心的流露。而張鐘鳴,則是隨筆摩羅的豐富和延伸。
整個文本充滿了宗教情懷,對所有苦難而又罪惡的生靈懷著深沉的愛和悲憫。
杜紫微:是的,這一點我也深有體會。在《六道悲傷》里,摩羅不止在張鐘鳴這個人物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另一個人物——許紅蘭,也是經過作者精心塑造,是世界文學人物的畫廊里第一次出現的形象。許紅蘭原先是上海灘的妓女,為了愛情,為了尋找一個歸宿,嫁給了紀文波,來到張家灣這個血汪汪的湖畔村莊。可是,沒過多久,恩愛的丈夫就被人暗算。作為一個世俗中的女人,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安全感,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全部。在這種情況下,她仍然是善良、美和愛的化身。因為有了這個光彩照人的女子,張家灣這個冷硬荒寒的村莊里才有了溫暖的色調。她承擔了作為女人應該和不應該承擔的全部苦難,卻用女人能夠付出的善良和仁厚呵護著別人。作者給他安排了一個鄉村醫生的角色,村里的人,誰有了小傷小病,馬上想到去找許紅蘭。有一次,許紅蘭自己的手碰破了,站在一旁的張鐘鳴竟脫口而出“去找許紅蘭!”我認為,讓許紅蘭擔當“醫治者”的角色,這是一種象征,她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不僅療治人們身體的傷痛,也療治人類心靈的傷痛。她的愛,就像她家旁邊的悲忻潭水一樣,清澈甘甜,滋潤著一顆顆受傷的心靈。只是,這種力量太微弱了。
楊傳珍:許紅蘭身上體現出來的這個光明與愛的生長點,并不微弱。正如美學家潘知常先生所說,“光明與黑暗并不對等,而是遠在后者之上;愛與恨也不對等,而是遠在后者之上。”作者明寫這種力量的微弱,實質上,是暗示這種力量的韌性與強大。
杜紫微:許紅蘭這個人物很值得認真分析。她身上有著豐富的人性,仁厚的母性,慈悲的佛性,普世的神性。在大隊書記章世松對她實施強暴時,沒有真正反抗的許紅蘭聞到一股強烈的狐臭味而嘔吐起來,表面上不可一世而內心深處極度自卑的章世松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地要拿別人出氣。許紅蘭預感到了這場惡作劇將會傷害無力反抗的無辜者,于是,她不顧尊嚴忍受委屈去安慰章世松。此時,她甚至在潛意識里為自己無意中對章世松造成的傷害而懺悔。由于章世松還沒能從挫敗中走出,怒氣未消,他用訓斥和輕蔑拒絕了許紅蘭的獻身。然后,以“專政”的名義,殺害了在石壁上畫圣像的知識分子何幸之。這個時候,小說呈現的是這樣一幅畫面:許紅蘭以虛弱之軀,背著死去的何幸之從圣母像前走過,傾其全力安撫一個不可能復活的生命。這個場景,實在撼人心魄!而當張鐘鳴實在不能容忍章世松的惡行,想去告發時,許紅蘭卻又勸戒張鐘鳴放棄這么做,她認為,冤冤相報,只有增加更多的傷害。許紅蘭的這種態度,發自她的生命本性,而這本性,天然地具有寬恕一切的宗教情懷。
楊傳珍:小說里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章世松。對章世松這個“壞人”的塑造,作者既寫了他借助權利作惡多端,又寫了“精英統治”的傳統社會給這個卑微者的心靈深處造成的傷害。他的惡行,是一個受盡屈辱的無知者在反抗、報復情緒處在高漲時突然被賦予神圣權利之后的所作所為。作者是用耶穌的心腸來對待這個人物的。這是一個被精英傳統、流氓政治、等級文化、勢利社會、謊言風潮、暴力統治扭曲出來的怪胎,他的人性深處,勤勞、堅韌、忠誠、責任的成分大于流氓、無賴、殘忍、偏執的成分,是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的急劇扭轉,把他推到一個讓他作惡的位置上。其結果,不僅害了一方鄉親,而且害了家人,葬送了自己。
杜紫微:《六道悲傷》的整個文本充滿了宗教情懷,對所有苦難而又罪惡的生靈都懷著濃郁的悲憫之情。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不能原諒和悲憫猶大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聽你對章世松這個人物如此一番的分析,是不是可以說:不能悲憫章世松的讀者,還不能理解摩羅。
楊傳珍:正是這樣。我覺得,作者通過張鐘鳴這個人物,將自己的當下承擔推到了前臺,而許紅蘭,則是作者的期待自我或理想自我,作者把她的忍讓理解成更高遠更形而上的承擔。在章世松這個人物身上,則集中了幾千年來的弱勢群體的血淚。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之后,章世松這種人并沒有獲得文化、道德、心理、名分意義上的翻身,自認為高貴者(其實與他并無根本區別)仍然視他為卑賤者,他自己也沒擺脫掉卑微者的心態,他承擔不了時代強加給他的歷史使命。作者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審視章世松,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同情。作為生命倫理主義者的摩羅,對章世松這個人物的悲憫,遠勝于對其他生命的悲憫。
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當中,存在一種強盜邏輯,小說真實揭示了這種強盜邏輯給無數小人物、小生靈帶來苦難的悲劇。
杜紫微:小說中還有一個小精靈一樣的女孩張若雨,那么善良,聰慧,心靈絲毫沒有受到功利社會的污染,憑著生命直覺,她經常說出一些常人想不到卻直逼天道核心的話語。這個小女孩,可以說是善良的化身,是天使降臨人間。可是,她卻死了,無辜地為有罪的人承擔了苦難。作者如此安排,實在令人心痛。
楊傳珍:你回憶一下《被踩死的屎殼郎》那一章,就會明白了。
杜紫微:那一章主要是一場討論,發生在張鐘鳴與常修文之間。常修文看到一只勤勞的屎殼郎費了好大力氣,團了一個糞球朝自己的窩里推,另一個不愿出力的屎殼郎卻闖過來打劫,勤勞本分者與強盜爭奪起來。常修文因為還要接著勞動,沒有耐心和時間等著看結果,可他又不愿留下懸念,就一腳踩死了那只勤勞本分的屎殼郎,讓強盜獲取了糞球。之后,常修文就此向張鐘鳴發表了一番宏論。這個細節,我認為是塑造常修文思想、性格的一段重要筆墨,也是張鐘鳴剖析人性的一個精彩段落。
楊傳珍: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作者是要通過這個細節告訴讀者,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當中,存在一種強盜邏輯,這種邏輯會侵入到社會無意識、政治無意識、歷史無意識之中,導致張若雨死亡悲劇的發生。
杜紫微:揭示了這些殘酷的無意識,是否就能喚醒人們去努力改變呢?
楊傳珍: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力量還重。”作家沒有能力消除罪惡,但有責任真實地揭示罪惡。因為,第一,罪惡能夠導致悲劇,掩飾罪惡或對罪惡視而不見,導致悲劇的概率就會增大。讓麻木者、偏盲者、概念化的慣性思維者正視罪惡,可以減少苦難,減少悲劇發生。作家的良知和社會責任,往往要通過揭示罪惡體現出來。第二,苦難本身固然是悲劇,世人對發生在身邊的苦難一無所知則是更大的悲劇。要使苦難為人所知,讓苦難有出聲的機會,就不能從表層揭露,而要從深層揭示。這必須借助于審美文體,用虛構表現真。在這個意義上,審美是通向真理的捷徑。第三,一個人早年受了苦,若后來成為強者,那么他的苦澀和苦難自然就轉化成了財富,甚至甘美。若當事人始終是個弱者,他就沒有訴說苦難和悲劇的勇氣和機會,許多苦難和悲劇就會被歷史的風煙塵埋。文學是為小人物立傳的(王鼎鈞語),揭示強盜邏輯給無數小人物帶來苦難的悲劇,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我想,摩羅就是出于以上考慮,才作出這種揭示的。
杜紫微:只是,這些真實的文字實在太殘酷,讀來讓人心酸。
楊傳珍:作家楊烽說過,“真實的東西常常是殘酷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真實;謊言往往是美麗的,但我們不能相信謊言。”作家的責任是寫實,包括殘酷的真實。
杜紫微:《六道悲傷》就準確地揭示了那場大動亂之前人們的心理狀態,讓我們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揪心。
《悲忻潭》一章的性愛描寫,是能夠進入藝術殿堂的經典,其氣氛、感受、激情、欲火,都用高密度的詩性文字表現了出來。
楊傳珍:摩羅是一位詩性思維的思想者。在出版了四五部隨筆集,成為文壇翹楚之后,安下心來,歷時五年打造一部長篇,表現他的生命倫理,其沉穩的精神品格讓人敬佩。這部作品,將漢語的審美寫作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杜紫微:你是指形式和語言嗎?
楊傳珍:在形式上,《六道悲傷》是真正的復調小說,而且是結構勻稱的渾厚復調。語言的詩化,讓我聯想到《當代英雄》和散文譯本的《神曲》。但它不是歐化的,而是純正的漢語氣韻。這些,還都不是最重要的。《六道悲傷》對漢語小說的貢獻,是它內在的精神,是彌漫在字里行間的那種逼人的美。整部作品簡直就是一團晶體,處處閃射著美與善的光輝。書中的任何一個細節,任何一處鋪墊,都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活生生的器官,都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鏈條,都是表達作者思想和信仰的火花,渾然一體,無一處游離。而每一個小的單元,都蘊涵著豐富的內容,讓人處處都能見到大的境界。《悲忻潭》一章中的性愛描寫,我現在就敢說是能夠進入藝術殿堂的經典。英國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有幾處美不勝收的性描寫,但那太單一,只能說是唯美主義的。還有幾位大師級的作家,寫性時,有的是為了表現罪惡,有的則暗示性即骯臟。而人類的性行為,既不是罪惡也不是骯臟,而是美,是感情和精神力量的飛升。因為前有勞倫斯,摩羅在呈現張鐘鳴和許紅蘭的那場驚天動地的性愛時,加進去苦澀與悲涼。那樣的社會大環境,那樣兩個對生命、對美有著形而上理解的苦命人,在那個月光如水的悲忻潭邊,體驗那樣的身體與靈魂的碰撞,其氣氛、感受、激情、欲火,都讓作者用高密度的詩性文字表現了出來。那種境界,那樣清澈的美,說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光輝的篇章,一點都不為過。
杜紫微:摩羅對人性的挖掘、把握、展示、表達,都具有直逼核心窮盡內蘊的力度與厚度。在《大嘔吐》一章里,寫章世松強暴許紅蘭未成的場面,其豐富性、合理性,不僅是對過去此類描寫簡單化、模式化的警告和超越,更是對人性的昭示。此時此刻的許紅蘭,被權勢者威逼的女人,被作者還原成了人,不再是作者拉來利用的符號。左拉說:“我把作家看作是上帝之后使一個世界誕生的創造者。”在這里,摩羅站在一個女性生命的心靈深處,伴著她的酸楚與期盼,生出對這樣一個孤苦女性的無限的同情,創造出一個苦命但完整而真實的女人。作為一名女性讀者,我認為,摩羅是真正讀得懂女性世界的作家,他賦予許紅蘭的尊重和同情,是來自男性寫作者的一種難能可貴的真情。如果作家本人缺乏這種真情,他是很難深入到人物內心的,又談何打動讀者呢?
楊傳珍:是的。摩羅小說的張力很大,當你讀到激烈場面,總是感到心酸,讀到苦澀的描寫,又讓你心中充滿希望。這是大手筆的標志,大境界的體現。當然,大手筆、大境界來自作家的大胸懷,即信仰者的胸懷。
杜紫微:我也能感受到作品里彌漫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情懷。
楊傳珍:以“五四”為發端的中國新文學,一個重要的源頭是俄羅斯文學。魯迅先生就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的小說受到果戈里的影響。之后,俄蘇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始終沒有間斷。但是,我不得不說一句讓很多人不舒服的話:《六道悲傷》是第一部俄羅斯文學內在精神在中國落地生根的作品。它吸取的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善的和惡的)的豐富營養,沐浴的是俄羅斯精神中最高貴的陽光,結出的是中國氣派的果實。
你無法分辨是寫實還是魔幻,這不是從外國文本中摹仿來的魔幻,而是直接來自生命體驗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式魔幻。
杜紫微:還有中國式的魔幻。
楊傳珍:你的感覺很對。這些年來,許多中國作家,今天學習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明天摹仿卡爾維諾和布爾加科夫,但誰也沒有成功,只披了一張外國作家的皮,不倫不類,還自以為得了人家的真經。摩羅的小說,是從作家的生命深出噴射出來的另一個生命,你無法分開是寫實還是魔幻,但那些場景、氣氛、形象、精神是那么和諧統一,又是那么撼人。正如你所說,這不是從外國文本中摹仿來的魔幻,而是直接來自生命體驗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式魔幻,是藝術家創造出來的“第二世界”,而不是用學來的技術組裝的冒牌貨。
杜紫微:血土,石頭精,孬孬與老虎,虎陣,哭聲,殺豬,葬禮,鄱湖長調,這些章節無不煥發著魔幻的神采;厚重的歷史傳說,傳奇的傻子的預言,神秘的儺舞與悲涼的唱腔,在張家灣這塊土地上織出了一幅五彩斑斕的生命錦緞。在這里,美統攝了一切,作家將具有普泛意義的內心苦痛轉化為令人銷魂的音樂,完成了劃時代的精神涅磐。
楊傳珍:我認為,《六道悲傷》中所呈現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創作主體內心痛苦的折射,作者所揭示的一切都源于自己那顆承載苦難的心靈。他通過這部作品,在恥辱中尋找尊嚴,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荒寒中尋找溫暖,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化解苦難中尋找做人的幸福,為靈魂尋找信仰。他的信仰,不是人間天國,不是哪一種具體宗教的神,而是對生命的敬畏,是從自身做起的善待一切生靈。這樣的作品,超然物外的文人寫不出來,勇于建造“憎的豐碑”的文化斗士寫不出來,它只能出自一個在精神上勇于承擔人類全部罪惡的生命倫理主義者,一個為全人類祈禱的普世宗教的圣徒,一個用詩性思維洞悉整個人類本性的藝術思想家的生命深處。在這個意義上,《六道悲傷》是摩羅的,也是人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