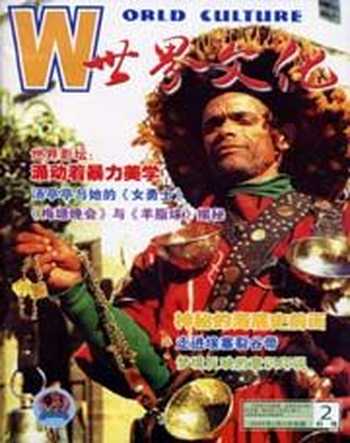鄂畢河畔的森林城市
孫加祺

四、蘭樹
新西伯利亞市盡管有百萬人口的規模,但由于地處偏遠,經貿不甚發達,與莫斯科華商扎大堆的情況相差甚遠,整個城市沒有幾個中國人,常住的中國人就更寥寥無幾了。但在市區中心,有一名曰“蘭樹”的中餐館,它是整個新市唯一一家由中國人開辦的中餐館,這讓我們多少感到欣喜與親切。
蘭樹是一幢上下二層面積約300平方米的小木樓,已有150多年的歷史。歲月留痕,小木樓外表看上去已經斑斑駁駁,尖尖的屋頂和木門、木窗、木柱、木墻與門前一排木柵欄,都掩映在高大的樹叢中,就像一幅風景油畫。主人告訴我們:這座小樓現在已是新西伯利亞市的文物保護對象。走進小樓,四處古色古香,有的房間呈原始結構、有的房間顯時尚風格,但總的格調沒有變。精致的雕飾和古樸的風貌,與我想象中的西伯利亞小木屋極為相象。因為是中餐館,所以,在長長的屋檐下吊著一排紅燈籠。
在古老的小木屋里,品著俄羅斯的“伏特加”,餐廳里輕漫著悠揚濃郁的俄羅斯小曲,臨窗下眺,街道上很安靜,不見行人,只有些小車不時匆匆駛過。小樓后面是幾幢老式住宅樓,在樓與樓之間都是高大的樹木,一派安靜甚至沉靜的氣氛。西伯利亞的秋天格外晴朗,高大的樹木在秋風中搖曳著它的枝葉,不時有一片片泛黃的葉子落下來,午后的陽光被樹葉打碎,落在餐桌前,給小屋增添了幾許暖意。
蘭樹,這座百年小屋,目睹了西伯利亞跨世紀的變遷,有多少主人在此生活,匆匆而去成為過客;有多少故事在此演繹,而成為歷史片斷;我們都不得而知了。只有小屋在無言中延展著過去的時光,讓人一看到它,不禁想起西伯利亞遙遠的過去……
五、西伯利亞大鐵路
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項震驚世界的偉大工程。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俄國和亞洲問題專家、佛羅里達大學教授倫森先生,曾這樣評價它:“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像西伯利亞鐵路那樣,象征著西伯利亞時代的到來”。這條曾驚人宏偉的鐵路,現在就靜靜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從中心旅館出來向東走大約20分鐘,就可以看到西伯利亞大鐵路高高地架在一座橫跨公路的鐵路橋上,它穿越城市,跨過寬闊的鄂畢河,與橫臥在鄂畢河上巨大的水電站一道,成為這個城市建設史上兩個永久性標志。總長9200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早已電氣化了,各種電纜、電線和高高矮矮的座桿像蜘蛛網一樣,罩在鐵路的上方,晨光中兩條發亮的鐵軌東西兩向伸展著,遠處有老式的車站和工房伴在鐵路旁。
大鐵路靜靜地臥在那里,像一條累了的巨龍在安歇。一個帶著鐮刀、斧頭圖案的火車頭,停放在一截斷頭的軌道上,實際上就是它的展臺。這是一輛老式的蒸汽機車,黑色的車身已經斑駁褪色,只有鐮刀、斧頭和紅旗像是剛被油漆過,紅光閃閃格外醒目,車身上所有的管路和粗大的鐵輪搖臂,由于無人清掃,已經掛滿了灰塵。
這大概是一輛功臣機車吧,也許是在開發遠東的三十年代建過功勛、也許是在二戰時期立下了戰功,不論過去怎樣輝煌過、轟鳴過,而今天它已經老了,靜靜臥在這里,看著一列列電動機車呼嘯而過……
六、年輕人的啤酒館
新西伯利亞的夜晚是安靜的。盡管街燈已亮,但整個城市仍沉浸在樹林的暗影中。沒有五光十色的廣告,不見閃爍的霓虹燈,一條條道路伸向城市的遠方,透著幾許神秘。路上不見人影,街心花園早已空無一人。萬里星空籠罩著這個遙遠的城市,人們都到哪里去了?西伯利亞的夜生活是怎樣的?當我們從旅館出來,準備上街逛逛夜景的時候,主人熱情地邀請我們:晚上找個地方再喝點酒,聊會兒天。真好,一個正中下懷的提議。在西伯利亞涼意沁人的夜風中,我們鉆進伏爾加車,在時而明亮,時而漆黑的寬街狹道里穿行,只見兩道車燈閃亮。三彎兩轉,小車在一家娛樂廳兼酒吧的門前停下來。主人告訴我們:“這是整個新西伯利亞市最具規模檔次的娛樂場所”。這是一間面積在四、五百平方米的兩層小樓。推門而入,在五彩燈下,掛在長長吧臺上方的酒具和各色酒瓶閃著晶瑩的光。拾階而上,二樓是個橢圓形的看臺,沙發茶幾和圓桌靠椅,依次擺開。往下望去,正是一樓的舞廳,三三兩兩或成雙結對的俄羅斯青年在燈光下飲酒、聊天或相偎耳語……舞池中則有十幾名男女青年在忘情舞之蹈之,舞臺上方大屏幕上播放著俄羅斯明星的歌曲,音量放得很大,有些讓人震耳欲聾……
啤酒上來了,純正的俄羅斯啤酒,但在這豪華舞廳中,小吃卻只有兩種:巧克力和咸味脆薯片。
舞池里的年輕人在勁舞,大屏幕上在勁歌,整個舞廳被震得轟隆隆,就像我們在國內看到的差不多。但細望去,卻又有區別,勁舞者很投入,但不狂野,透著自我愉悅的快活。舞場中的幾對中年人,也合著樂曲自顧自地邊說邊跳,整個舞廳的男男女女都像是來此放松的熟人。
在跳舞的過程中,穿插了兩次藝術表演,身材窈窕、面目姣好的俄羅斯姑娘在輕歌曼舞。燈光忽明忽暗,變動的色彩打在她們身上,輕紗飛揚,金發飄飄,一個個“魔鬼身材”,在舞臺上掀動著艷麗的氣氛,整個啤酒館都熱烈起來。我不禁有些擔心:在這秋夜深深的西伯利亞一間酒館里,這群像西伯利亞樺樹般粗壯的年輕人會不會隨之變得輕狂起來……但是,擔心多余了,一切如常。樓上樓下、酒中酒后的俄羅斯年輕人都中規中矩,始終沒有起哄聲、口哨聲或叫喊聲,他們都在靜靜欣賞。
七、十字街頭的擺攤兒老人
清晨,西伯利亞的太陽還沒起床,我已在晨曦中醒來,不是覺睡足了,而是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與新奇在催促。
晨風涼爽,當我們走出中心旅館的大門時,寬闊的大街靜悄悄,只有藍藍的天空和泛黃的樹林映在眼前。時間在緩緩地流失,看不見匆匆上班的人群、魚貫而行的自行車和一溜煙的小汽車。這是一個沒有急迫、沒有追趕的早晨,一個沒有壓力、不動聲色的早晨,一個與大森林氣息相融的自然的早晨。
就在這冷清的街頭,路口拐角處卻見到兩位俄羅斯“賣花大娘”,年齡大約有五、六十歲,看上去已經在路邊呆了一會兒了。地上擺著幾盆鮮花,叫不上名來,但水靈、鮮亮。幾只麻雀在花盆旁嘰嘰喳喳地叫著,仿佛也在賞花。兩個大娘一站一坐,一聲不吭地守在花旁。天涼了,站著的大娘已經穿上厚厚的冬裝,坐著小馬扎的大娘則將一個透明的塑料袋嚴嚴實實地套在身上,只露出個腦袋。見了我們只是笑一笑,依舊靜悄悄地坐著,不叫賣,不聲張,不招攬,悄然等著買花的人。馬路的對面,還有一對老夫婦在支攤兒賣菜,也是靜靜的沒有叫賣。我們好奇地走上前去,菜攤兒上只有黃瓜、白菜、西紅柿、土豆,數量不多,也就不到十斤的樣子,但價格貴得驚人。白菜和黃瓜論個賣,一棵白菜20盧布,兩位老人和藹耐心地回答著我們的提問。大概是第一次與好幾位中國人同時交談,老人顯得很開心。他告訴我們:西伯利亞蔬菜很少,土豆是這里常年用的“戰備”菜,其它品種的用量就少多了。城里人在城郊都有自己的“達卡”,一種木板制的別墅(準確地說就是小農舍),有一塊自己種植的自留地。他家也有。秋天了,一周去一次,周末休假并帶回土豆等自種菜。老倆口吃不了,就擺攤兒賣。“賣了更好,賣不了拉倒”老人微笑著無奈地說。
八、有趣的商店
與西伯利亞廣大地區的遙遠、封閉狀態相比,新西伯利亞市的商貿業相對發達。其大致分為三種業態:一種是“庫姆”,即百貨商場。大型百貨商場在新市僅兩家,分別座落在鄂畢河兩岸的城區。第二種是超市,大約有十來家,分成食品超市與百貨超市,或兩者兼而有之,形式上與我國超市差不多。第三種是專賣店,如手表、工藝品、服裝、運動用品專賣店等。這種店不僅隨處可見,而且十分有意思。它們多設在樓房的底層,一眼望去與一般的住宅一樣,既沒有中國商店的寬大門臉兒、漂亮櫥窗,也看不見出出入入的客流,只有一個三、四級臺階的穿梯和店鋪牌匾告訴你,這是商店。走進去一看,往往顧客就你一個人。不論哪個店,多大多小,都能看到身穿灰色保安服裝的“帶槍的人”。一幢高大的建筑有一扇小小的門,里面藏著一個幾十平米上百平米的商店,“小嘴大膛”,這就是新西伯利亞最普遍的商店形式。
更有趣的是,還有一種商店,就在居民樓內開設,形成“宅店共生”的獨特現象。在新市的列寧大街上,帶我們去考察商業的俄羅斯朋友把我們引入一幢高19層的居民樓中,我們莫名其妙:到居民樓干什么?上了四、五層后才發現,樓上有商店,里面還挺大,有食品機械。冰柜、冰箱、廚具、包裝機械,其它樓層還有服裝店與服裝加工廠。朋友告訴我們:這個樓中店在這一帶挺有名氣,買賣還不錯呢!到居民樓內去購物,大概是西伯利亞人的一大發明吧!漫漫冬季,這可真是一個避風躲雪的好辦法。
街頭小吃,這種我們最常見的方便食檔,在新市也很鮮見。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列寧廣場旁側小公園進口處的小吃亭,小亭里支著灶,三個俄羅斯小伙做著油煎包。亭外是一個涼棚,擺著幾張餐桌,茂密的樹冠把小亭掩在綠蔭中。活潑可愛的小麻雀在樹枝與餐桌上來回飛,有時還跳到你的近旁,啄食你掉下的飯渣。油煎包加飲料,這種最單調的小吃,照樣讓三三兩兩圍桌而坐的青年人吃得津津有味。除此,再沒看見其它小吃攤兒,更沒有看到什么小吃街、風味食廊。西伯利亞人的生活需求給我的感覺是:簡單。也許,是寒冷的氣候造就了簡單的生活吧!
九、流動的老車博覽會
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眼中,對蘇聯汽車都有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初期,蘇制汽車曾長期居主流地位。從吉爾貨車到客車,從吉姆、伏爾加、華沙、莫斯科人小轎車到“嘎斯69”吉普,各色蘇制車輛轟隆隆地在中國公路上駛過了三十多年。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它們才逐步退出市場。現在,在大街上看見一輛伏爾加、拉達已是稀罕的事情了。
但是在新西伯利亞,歷史場景又再現出來,讓我們回到蘇制老車滿街跑的時光。一下飛機,接我們的就是一輛伏爾加,寬大的車身配上高分貝的噪音,開起來更像一輛坦克。在進城的路上,一輛“嘎斯69”吉普車迎面駛過,那前輪上方兩個半圓形的擋泥板,活像兩塊鎧甲。走進城市,老式車輛越發多起來,伏爾加、拉達與莫斯科人仍是俄羅斯人的主流車型,我們真實地回到了上世紀中葉的汽車年代。
據俄羅斯朋友講,在新西伯利亞州沒有限期報廢汽車的規定,只要能開能跑,不管車多老,照樣在街道上疾行。由此,就形成了各個年代的車型都能在路上展示的景象。但多數小汽車已經老舊了,藏污納垢,灰頭土面,像一個個邋遢的老漢在街上亂竄,且發動機聲音奇大,不像小轎車更像拖拉機。但不論怎樣,在新州幾天,很少看見自行車和摩托車。不論款式新舊,俄羅斯人一律以小汽車為座騎。在城里,公共交通仍很發達,公共汽車、電車、包括有軌電車都各行其道。
在市郊公路上,我們還看見一道風景:一輛輛從“達卡”回城的小汽車車頂上,馱著大大小小的麻袋,里面都裝著同一樣東西———土豆。這是周末到鄉下休息,在自留地勞作后返城的人們,把一周的主食帶回家。這也是俄羅斯人創造的“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有趣方式吧。
仿佛為了與陳舊的汽車相配套,公路也陳舊了,坑坑洼洼的地段很多。俄羅斯朋友告訴我們:這些公路多是在衛國戰爭期間和戰后時期修建的,盡管破舊,仍四通八達。許多公路從城市里延伸出去不遠,便鉆進莽莽蒼蒼的大森林或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中。“我們還在吃老本呢!”俄國朋友自嘲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