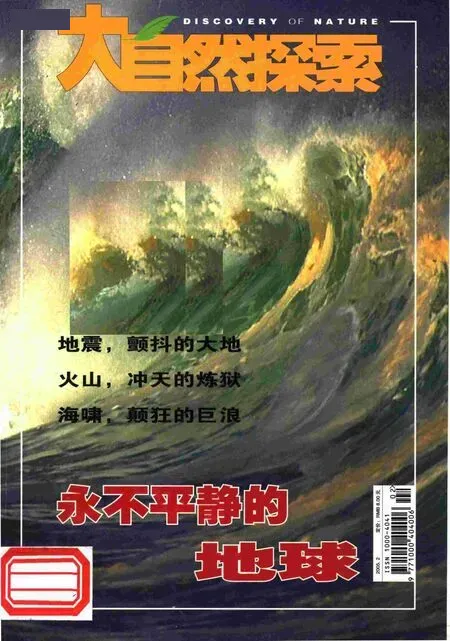秦嶺羚牛
雍嚴(yán)格
夏天的秦嶺山脊上,呈現(xiàn)一片花的海洋,高大的冷杉林下金背杜鵑花競相開放,高山灌叢中的繡線菊像盆景一樣擺得嚴(yán)嚴(yán)實實。而在山頂草甸上,許多不知名的小花,黃的、紅的、青的、紫的,都繡在綠色的地毯上。夏天的秦嶺簡直美得使人心醉。享受這一壯麗美景的不只是偶爾涉足此地的人類,更多的是長期生息在這里的珍禽異獸,秦嶺羚牛是它們中最主要的成員之一,是這里真正的主人。
不同的季節(jié),
遷移到不同的海拔高度
自然把一年的時光分為春夏秋冬四季,不同季節(jié)的氣候為各種植物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機(jī)遇。許多植物從春到冬經(jīng)歷著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實、枯萎的生命周期。而依靠植物為生的一些動物則利用植物不同季節(jié)生長的狀況,把依山體上下遷移選擇最富營養(yǎng)、最適合口味的食物作為自己的生存對策。
春天,當(dāng)秦嶺低山的積雪開始融化時,青草率先冒出了嫩芽,羚牛在度過饑寒交迫的嚴(yán)冬之后,舉家來到海拔高度1600米以下的低山河谷中,尋找青草改善生活。同時,一些經(jīng)過9個多月懷孕而將分娩的雌性羚牛,也在溫暖的陽光下選擇平緩的地形生下自己的小寶寶。羚牛選擇在春暖花開的季節(jié)產(chǎn)仔,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幼仔的成活率。
夏季,隨著氣溫的升高,低山植物開始老化,而高山眾多的可食性植物此時開始生長發(fā)芽,羚牛則從東南西北聚集到海拔2200米以上的針葉林中,取食適口性好、營養(yǎng)價值高的各種嫩草新葉。它們不僅利用這段時間來集積營養(yǎng),增加體質(zhì),為迎接食物短缺的冬季做好準(zhǔn)備,更主要的是許多族群將在這個時候聚集在一起,為談情說愛滿足生理上的需求創(chuàng)造良機(jī)。夏季不僅為羚牛提供了最豐盛的食物,也提供了廣泛交流、尋求愛情的機(jī)會,這是羚牛們最美好的時光。
秋季,高山氣溫急劇下降,草木開始凋謝,羚牛經(jīng)過一段愛的執(zhí)著追求后,它們以各自的族群為單位,再次下移到海拔2000米以下取食尚未干枯殘敗的落葉。
冬季是羚牛生活最艱苦的季節(jié),寒冷、饑餓、疾病、天敵向羚牛種群提出了挑戰(zhàn)。羚牛群由低海拔的闊葉林再次上移到海拔1800-2000米的針闊葉混交林中,以取食箭竹竹葉和一些含油脂的針葉樹皮及苔蘚,維持生存所需的基本能量。在整個冬季,羚牛的活動范圍和活動量較小,這可能是減少能量消耗來彌補(bǔ)食物短缺和能量低下所采取的對策。而此時那些年老體弱的個體因行動緩慢而常被天敵獵食,或因體質(zhì)衰弱不能抵抗嚴(yán)寒和疾病而倒斃。物競天擇,弱者被自然淘汰,留下健壯的個體以保持種群的興旺。
母系社會,
雌性羚牛統(tǒng)領(lǐng)家族
羚牛和大多數(shù)食草動物一樣營集群生活。它們在夏季由各個家族群匯集在一起,集成大群。每年的6-7月是羚牛的繁殖盛期,成年的雄性羚牛與進(jìn)入生育期的雌羚牛無憂無慮地追求“愛情”。越大的群體具有越大的安全感,可以避免天敵的侵犯,同時多個族群混聚在一起,有更多的機(jī)會選擇最佳的配偶,增加基因交流的機(jī)遇,減少近親繁殖。羚牛的愛情與大多數(shù)大型動物一樣,為了得到愛情,雄性羚牛都要經(jīng)過一場殊死的搏斗,只有勝者才能獲得與雌性羚牛交配的機(jī)會。因此,被打敗的雄性羚牛一旦在對峙中失去優(yōu)勢,便離開自己的群體獨(dú)自游蕩,以尋找其他羚牛群再去參加新的“愛情競爭”。我們在野外常常可以見到雄性獨(dú)牛孤獨(dú)地沿著山脊走來走去,四處漫游。這些獨(dú)牛穿行在各個群體之間,為遺傳基因多樣性的傳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xiàn)。
羚牛的群體大小不一,最少的為2-3只,多的可達(dá)近百只。集群以季節(jié)不同而有家族群、社群、聚集群三種形式。家族群是羚牛群的基本單位,一般在10只左右,由成年的雌性、年輕的雄性、未成年的亞成體和當(dāng)年出生的幼體組成。成年的雌性羚牛是家族群的頭牛,當(dāng)羚牛群遷移時,它總是走在群體的前面;當(dāng)群體取食時,它又總是站在高處不時向四周張望,負(fù)責(zé)警戒,一旦發(fā)現(xiàn)異常,即發(fā)出信號帶領(lǐng)群體轉(zhuǎn)移;當(dāng)夜暮降臨時,雌性羚牛們便圍成一圈,將幼體圍在中間以保護(hù)幼體的安全,由此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母系社會。而社群由3-5個家族群組成,在移動和休息時都在一起,但各個家族則相對集中。聚集群是在繁殖季節(jié)由幾個社群在同一片山坡,短時間中匯合而成,這種匯合最集中的時間不超過半個月。食物的豐富度和繁殖行為是決定羚牛集聚時間和規(guī)模的主要因素。
每天,
過著規(guī)律性的生活
早晨7—8時,當(dāng)東方升起一輪紅日,夜棲的羚牛群開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雌性羚牛忙著給自己的小寶寶哺乳,雄性羚牛則在牛群中走來走去,時而在周圍吃幾口草,時而向“家庭主婦”們張望,它們急躁的樣子顯然想趁太陽還未完全曬干草尖上的露珠之前,盡快享受一下大自然為它們提供的可口早點(diǎn)。當(dāng)雌性羚牛給小仔喂飽奶后,便率領(lǐng)牛群走向林中采食。羚牛采食時是用上下唇扯斷青草或樹葉,而不像牛那樣用舌卷食青草,其姿勢似羊而不似牛,并且它們還常以前肢搭至樹干,后肢站立的姿式采食樹上的樹葉。
上午11時左右,忙碌采食后的羚牛群為躲避牛虻的騷擾,常鉆進(jìn)茂密的竹林和灌木叢中休整,有的靠著樹干來回擦癢癢,消除一下毛下寄生蟲帶來的不適;有的用抵角撬開土坡上的草皮,躺在上邊盡情地享受著泥浴;還有的則靜靜地臥在地上反芻著上午吃下的食物。只有雌性羚牛最為辛苦,它們不僅要給幼仔哺乳,還要不時地到林緣或高處向四周觀望,為群體站崗放哨。
下午2—5時,太陽偏向西方,山風(fēng)趕走了討厭的蚊蠅,羚牛群陸續(xù)來到冰緣地貌形成的裸露礫石灘中,此時,亞成體和當(dāng)年出生的小羚牛如同離開父母管轄的小孩一樣歡呼跳躍,學(xué)著父輩們的行為用頭抵來頂去做著游戲。成年的雄性羚牛在這寬敞的環(huán)境中更不甘寂寞,或是雙雙決戰(zhàn),或是嗅聞雌性羚牛后臀以討得歡心,有的則不斷地進(jìn)行爬跨——交配,享受著愛情的甜蜜。
下午6—8時,這是羚牛一天中活動的第二個高峰,它們得抓緊夜幕降臨前的時間填飽肚子。
當(dāng)夕陽收起余輝躲進(jìn)大山的背后,羚牛群便集中到植被稀疏的石山或空曠的平臺上開始夜棲。羚牛總是選擇地勢高、視野開闊的地方作為夜棲地,這可能是為了安全而長期形成的習(xí)慣。因為山勢陡峻,無法在夜間接近,我們對羚牛夜間的詳細(xì)活動情況還知之甚少,但已觀察到羚牛群早晨活動之前的地點(diǎn)與前一天黃昏時集中的地方?jīng)]有變化,可以肯定羚牛在夜間除了反芻之外,沒有大的活動。
一片片孤島,
羚牛最后的庇護(hù)所
羚牛的天敵主要是虎、豹和豺。虎在秦嶺已瀕臨絕跡,豹和豺也因數(shù)量稀少對群體羚牛的威脅有限。那么,羚牛所面臨的嚴(yán)重威脅是什么呢?是那些與羚牛共同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類。
雖然,在秦嶺自然保護(hù)區(qū)生活的這種特有的國家一級重點(diǎn)保護(hù)動物秦嶺羚牛,目前其數(shù)量已由建立保護(hù)區(qū)前的100多只,增加到目前的600多只,然而,威脅還時刻存在,被分隔在一個個“孤島”上的羚牛,怎樣保持基因的多樣性以避免近親繁殖,仍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難題。
人類為了發(fā)展交通,幾條鐵路和數(shù)條公路干線將綿延千里的秦嶺斬為數(shù)段,公路的支線也延伸到溝溝岔岔,將秦嶺這片野生動物的完整棲息地分割成了支離破碎的片段,原可彼此交流的羚牛種群被限制在一片片“孤島”上,處境確實不妙。
人口數(shù)量不斷地增長,加劇了森林資源的消耗。在秦嶺地區(qū)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地大都被農(nóng)耕地侵占。而1500米以上的天然林多年來除被采伐之外,當(dāng)?shù)剞r(nóng)民還將成片的森林砍倒,鋸成木段,點(diǎn)種上香菇、木耳,以大量發(fā)展食用菌生產(chǎn)。目前可以說除現(xiàn)在的自然保護(hù)區(qū)之外,原始天然林已不復(fù)存在,而天然次生林大都已變?yōu)椴煞ホE地或灌木林。習(xí)慣生活在針葉林和針闊混交林中的羚牛正在失去原有的美好家園。
更有甚者,有些人受經(jīng)濟(jì)利益的驅(qū)使,不顧國法仍然潛入林內(nèi)安夾放套,獵殺羚牛。獵殺羚牛案件在保護(hù)區(qū)內(nèi)外屢屢發(fā)生,保護(hù)區(qū)雖然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開展巡護(hù)和清理夾套,但往往防不勝防。而在保護(hù)區(qū)外。情況就更為嚴(yán)重。因此,如何采取有力措施保護(hù)羚牛成了我們這代人的重要責(zé)任。目前,在秦嶺中段已先后建立起了16個自然保護(hù)區(qū),這些保護(hù)區(qū)大都是羚牛秦嶺亞種的主要分布區(qū),而且地域連成一片,構(gòu)成了自然保護(hù)區(qū)群。正在加強(qiáng)中的自然保護(hù)區(qū)管理,為羚牛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優(yōu)越條件。建立于1979年的佛坪自然保護(hù)區(qū),在建立之初調(diào)查羚牛數(shù)量為100多只,到1997年達(dá)400多只,到2001年已達(dá)600余只,總量增加了三倍以上,這標(biāo)志著一種希望——羚牛不會滅絕,自然保護(hù)區(qū)是它們最后的庇護(h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