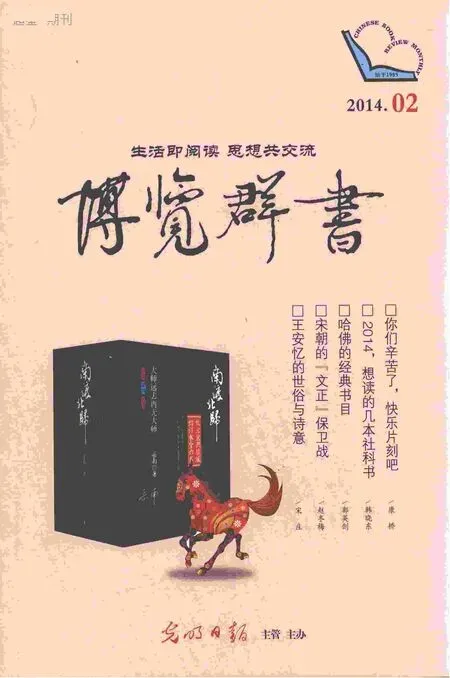費希特早期的憲法理論
沈 真
青年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的初期曾經仿效費希特的《自然法權基礎》(耶拿與萊比錫1796年與1797年),寫過一部長達300頁的法權哲學著作手稿。他在寫給他父親的信里說,他從費希特的理想主義中吸取了營養,但寫得比費希特更現代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15頁)現在這部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已經收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10輯問世,如果我們閱讀此書,將會從它所包含的憲法理論中體會到這種理想主義迄今仍然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
費希特早期的憲法理論有兩個邏輯演繹的前提。一個是人在社會中從道德領域到法權領域的過渡,一個是在法權領域中從公民社會到國家的過渡。在談到前一個前提時,他說明了道德領域屬于人們的內心活動,而法權領域屬于人們的外在行動;他論證了人們作為道德存在者在前一個領域固有的和不可轉讓的權利,諸如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從事勞動的權利和思想自由的權利,論證了人們作為社會公民在后一個領域發生的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的關系,而支配這種關系的法權規律的根本內容是:“你要這樣限制你的自由,那就是除了你以外,他人也會是自由的”。(該書第93頁)當人們從道德領域過渡到法權領域時,不僅依然應當服從道德規律,而且必須服從法權規律,但這兩種規律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質。道德規律雖然要求人們無條件地履行道德職責,但這只有規勸作用,而沒有強制作用;反之,法權規律則具有強制作用,不管人們是否具有善良意志,它都必須得到認可和加以執行。在法權領域里,人們是在自由意志的外在應用中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的,正是基于法權規律,他們才結合為一個作為公民社會的法權領域,如果沒有對于法權規律的共同認可和共同遵守,他們就又退回到了道德領域,即退回到了自由意志的內在應用中。而在自由意志的外在應用中,人們要維護公民社會這個初步形成的共同體,就必須在他們發揮自由意志的界限、擁有勞動成果的權利和相互支持的義務方面簽訂許多體現法權規律的、使簽約雙方都受惠的契約;但簽約者是否在內心世界里相互忠誠和信任,卻是外在的法律管不了的。簽約者一方往往由于自私自利或漫不經心而損害了另一方,從而使法權關系失去平衡。因此,這種體現法權規律的社會契約能否有效地履行,還帶有或然性,而缺乏確然性的保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推舉出一種能用強制手段實現簽約雙方的共同意志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就是政權。這樣,人們便從作為公民社會的法權領域過渡到了作為國家的法權領域,而費希特就是從這個地方演繹出他的憲法理論的。
在費希特看來,政府雖然是為了維護公民社會中人們的法權關系誕生的,因而在確立公民社會的各種契約中作為保障履行契約的第三者發揮著作用,但在人們最后結合成的這個作為國家的法權領域里,它的角色卻不再是這樣的第三者。在這里,這個法治共同體的全體成員把他們那部分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轉交給了他們選舉出來的政府,而政府必須對他們負責,它的職責不過是執行他們的共同意志,讓法律和正義統治國家。這就是說,這種權力的轉讓也必須簽訂一項契約,契約一方是法治共同體的全體國家公民,另一方是執行他們的共同意志的政府,而這項契約就是維護法權共同體的根本大法,即憲法。在這里,費希特堅持法國革命的理想,用人民主權的原則解決了國體問題。他論證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他把選舉政府最高官員的過程視為人民與官員簽署人民制定的這項契約的談判過程。當選的最高官員愿意按照這部憲法治理國家,接受了選舉結果,就變成了人民的公仆,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如果不愿意這么做,則重新回到人民中間。談判如此繼續進行,直至最后從人民中選出最有智慧的人擔任最高官職。費希特在此特別強調了兩點:第一,人民轉讓給當選官員的,僅僅是那部分管理法治共同體的權力,而決不是自己固有的不可轉讓的權利。因此,他批評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的極權主義傾向。盧梭主張,“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而且“這種轉讓是毫無保留的”(《社會契約論》,北京,1987年,第23~24頁);費希特則認為,“他們并耒完全獻出自己和自己的所有”,他們依然是“自由的、完全獨立自主的人,而且國家政權給個人保護的也正是這種自由,惟獨為了這種自由,個人才加入這個契約”。(該書第 206~207頁)第二,人民的權力必須超過最高政府當局掌握的權力,以防行政權力背叛人民。費希特認為,只有行政權力才可能成為反叛者,“人民則從來都不是反叛者,因為人民實際上是最高的權力,在它之上沒有任何權力,它就是一切其他權力的源泉”,而“只有反對更高的權力,才能說是反叛,但在地球上還有什么東西比人民更高的呢?所以,說人民能反叛自己,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該書第 185頁)
關于國家權力轉讓給誰的問題,費希特汲取法國革命的教訓,真正按照人民主權原則作出回答,確定了最佳的政體。在他看來,把國家權力轉讓給一個對管理公共權力不承擔任何責任的人,這就是專制政體;它雖然符合于愚昧落后的國情,但也只有暫時存在的可能性,而終究會被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摧毀;與此相反,把國家權力轉讓給一個對管理公共權力絕對負責的團體,這則是共和政體或狹義民主政體,它最能執行國家公民的共同意志,按照法權規律治理法治共同體。費希特把法治共同體全體成員不轉讓國家權力的政體稱為廣義民主政體,對它進行了批評。他首先指出,國家權力必須予以轉讓,而決不能保持在共同體全體成員的手中,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如果不能建立起一種執行共同意志、負責公共事務的政府,共同體全體成員就在執法方面既是法官,又是法律訴訟的一方,而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是很不安全的。其次,他從法國革命的進程中看出,盧梭事業的繼承者建立的那種廣義民主政體是不成功的嘗試,它本身具有兩個相反相成的弊端,即無政府主義和極權主義。針對前一個弊端,他質問道,如果共同體全體成員掌握了行政權,那么,哪種另外的權力能夠強迫他們在運用行政權時永遠遵守他們自己的法律呢?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糾正他們在執法中的錯誤的,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是自己的法官。其結果是,社會趨于不安,恐怖與日俱增,人們不僅像在沒有國家時那樣,經常害怕外來的暴力行為,而且特別害怕那些在法律的名義下從事非法行徑的群氓的盲目憤怒。因此,費希特認為,這種政體是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不可靠的政體;反之,在共和政體下,共同體全體成員則已經把行政權轉讓給了他們選舉出來的國家最高官員,這些官員專門負責管理公共權力,這時,他們已不能插手公共權力,而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無政府主義得以產生的可能。關于后一個弊端,費希特所指的是:那些以人民的名義把行政權力和監督這種權力的權力集于一身的群眾領袖,或者出于私心,在公共權力的管理中作出不公正的判決,或者自我膨脹,把他們個人的意志置于共同意志之上,使得共同體無法安定團結。針對這個弊端,費希特指出,“任何合理合法的政體的基本法都是:行政權與監督和判決如何管理行政權的權力是分開的”。(該書第164頁)而這種政體就是他主張建立的共和政體。
費希特效法古代斯巴達城邦的體制,把監督行政權力的權力稱為民選監察院。這個機構既不介入行政權力按照憲法制定各種法規的立法活動,也不介入它進行的行政事務,而是要對它是否貫徹了憲法作出判斷。這個機構是由人民選舉的一些年齡大和閱歷多、忠于人民和深孚眾望的人組成的,他們同樣是人民的仆人,而不屬于人民。他們的職責是在發現行政權力違憲時發布禁令,停止政府的一切職能。這時全體國家公民集合起來,在作為起訴人的民選監察院與作為被告人的政府之間,以法官的身份作出判決。如果前者起訴有充分的根據,政府的違憲行為就應作為反叛而受到懲辦;如果起訴沒有什么根據,這個民選監察院則須讓位于新的民選監察院。當然,事態的發展不會這么簡單。有可能,民選監察官在發現問題以后,勸說國家行政官員,收到了他們改邪歸正、重新取信于民的效果;也可能民選監察官接受賄賂,與他們聯合起來,踐踏憲法和法律。費希特就此寫道:“如果在一個民族中公認的優秀人物的思想竟然如此低下,這個如此腐敗的民族的命運就不會比它理應享有的命運更好些。”(該書第185頁)在這種情況下,總會有堅持真理、不怕犧牲的先知先覺者出來發難。其結果為:或者全體國家公民響應他們的號召,于是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舊民選監察官被廢黜,他們成為當然的民選監察官;或者全體國家公民尚未覺醒,沒有響應他們的號召,于是他們被當作所謂的反叛者,受到通緝,面臨著外在法律的懲罰,不過這種懲罰也并非絕對不可避免,因為“行政權力越卑鄙,那些向人民發出號召的人們率先逃避行政權力的懲罰的可能性就越多。”(該書第186頁)費希特最后說的是在制定憲法時如何形成和表達共同意志的問題。他認為,在這里既不能允許個人意志妨礙共同意志,也不能允許共同意志強制個人意志,而是應該求得兩者之間的合理合法的統一。一部合乎法權和理性的憲法既然是維護每個人的安全的,那就必須得到共同意志的保證,而共同意志就是共同體全體成員集合起來時形成的絕對一致的意見。在這里,每個人都必須以其個人的身份表明,他為了參加共同體,受到憲法給他的安全提供的保障,贊同大家達成的一致意見,如果有少數人不同意絕大多數人達成的共識,大多數人就應該尊重他們的權利,允許他們帶著自己創造的財富,離開這個國家的領土。雖然大家可以勸說他們,幫助他們提高判斷能力或克服偏頗見解,但任何人都無權強迫他們對一部憲法表示贊同。費希特認為,在修憲問題上,在選舉和罷免國家最高官員和民選監察官的問題上,也應達到意見絕對一致,而且他認為這條原則很容易實施。顯然,這是一條把憲法視為社會契約的原則,它體現了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尊重,而否定了多數人要求少數人服從自己的強制手段。
概括起來說,費希特制定的憲法原則是人民主權、共和政體、行政權與監察權的分立和絕對一致的意見。他以這些原則構成的憲法理論是他的整個法權哲學的最大成就。所以,《自然法權基礎》出版以后,無論在學者們的言談中,還是在報刊上,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學者與書評都對它表示了贊揚,但在對它提出的若干誤解與微詞中,卻有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費德爾在《哥廷根學術通報》(1796年12月3日)上發表的一篇對費希特充滿敵意的書評,這位評論者一口咬定,費希特說“人民永遠不會是反叛者”,旨在煽動人民鬧事。費希特針對這種卑鄙手段,著文嚴正聲明:“人民從來都不是反叛者。”“正是人民,才是一切政治權力最初的源泉,才是真正的、原初的最高權力擁有者。”“人民,只要確實是人民,怎么會成為反叛者呢?但君主會成為反叛者嗎?你們會同意我說,他會不公正,他會成為一個暴君,一個沾滿血腥的人;但如果我說,他作為君主也會成為反叛者,你們就會嘲笑我。”然而,“君主之所以不可能是反叛者,是因為他代表人民的權力;當人民起來直接管理自己的權力時,代表就被廢除了,君主就不復存在了。”(《費希特著作選集》第2卷,北京,1994年,第792頁)這就是一位真誠的德國古典哲學家經過研究得出而堅持到底的結論,就是他不怕公開說出而恥于隱瞞的觀點。
費希特這些法權原則一直在德國哲學史和法學史的研究中不斷得到好評。過眼的烏云怎么也遮蔽不了永恒的陽光。十九世紀中葉,曾經給馬克思提供過資料的慕尼黑大學教授胡貝爾,肯定了費希特的自然法權論著完全符合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無產者》,慕尼黑1865年,第8頁)十九世紀末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梅林在談到費希特的自然法權學說時指出,這一學說的實質是要建立一個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的真正的法治國家,在這個國家里公民自由不是使大多數人淪為奴隸而實現的,而是建立在凡具有人類面貌者一律平等的基礎上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1卷,北京,1963年,第72~73頁)尤其是,自從二十世紀中葉費希特哲學復興以來,他的自然法權學說,特別是其憲法理論,又進一步得到了新的研討與評價。俄國著名法學家馬穆特在莫季切夫主編的《政治學說史》 (莫斯科,1971與1972年)中寫道:“費希特關于國家和法權的學說具有獨特性”;“他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依據自然法權學說,堅決主張個人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力圖以此遏制專制主義的警察政權對待自己臣民的獨斷專行”;“他正確地認為,管理者須對社會負責,這應當成為任何一個合理的和符合法權要求的國家的特征,如果事實上沒有這種負責制,國家制度就會蛻化成專制制度”;“他深信人民的權威是不容爭辯的”,因此,“人民擁有對不合自己意愿的國家制度作任何變更的絕對權利,全體人民有權進行革命。”(中譯本,北京,1979年,上卷第308頁)美國費希特研究家希羅維爾認為,費希特最早認識到實行民主憲政是根本需要的學者之一。“從新的唯心論觀點出發,發展近代民主社會理論,是他第一個嘗試做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提出的問題是將盧梭和康德闡述的一般原則轉變為富有意義的實踐課題,用以建立各個新的、即將形成的民族國家;是他給予它們以幫助,向它們提供了真正民主的意識形態。”(《自然法權基礎》,倫敦,1970年,英譯本序言)進行這樣的研討的專著和相關著作相繼在各國涌現出來,諸如:德國布爾的《費希特早期哲學與法國革命》(柏林,1965年);紹特基的《近代契約論歷史研究》(慕尼黑,1963年);弗爾魏恩的《費希特論法權與道德》(慕尼黑, 1975年)和卡洛等編的《費希特法權學說》(萊茵河畔法蘭克福,1992年);法國費洛年科的《費希特哲學中的人的解放》(巴黎,1966年)和雷納特的《費希特思想中的哲學與法權》(巴黎,1986年);意大利杜索的《代議制——政治哲學的問題》(米蘭,1988年);俄國蓋登科的《費希特哲學中的自由悖論》(莫斯科,1990年)。
最后還應該說明費希特早期的憲法理論在德國古典法權哲學中的地位問題。
首先是費希特在繼承康德時超越了他的《法學的形而上學基礎》(1796年)。關于這種超越,法國著名費希特研究家費洛年科說:“康德區分了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費希特則肯定了人的價值最高,認為人人都有做國家公民或不做國家公民的權利;康德讓人居于一種被理解為以自身為目的的國家里,費希特則把國家,而且主要是國家公民組成的共同體視為達到目的的單純手段,而只有人才應當是目的;康德區分了法律上的平等與事實上的平等,費希特則認為人高于一切規定國家的關系,要求人人平等;康德譴責任何革命,因而像普芬道夫一樣,使任何壓迫都合法化,費希特把革命視為合法的;康德把戰爭狀態作為他所依據的自然狀態,從而指向建立秩序的必然性,費希特則不相信自然狀態本身是腐敗的;康德以那種自然狀態演繹出國家存在的必然性,費希特則從這種自然狀態演繹出人們在國家之外生存的可能性。”(《康德與早期費希特道德思想與政治思想中的理論與實踐》,巴黎,1968年,第156頁)這個概括盲簡意賅,確實兆明了費希特的創見。
其次是費希特與黑格爾的根本不同。黑格爾在他的《法權哲學原理》(1821年)中,把孟德斯鳩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立法、司法與行政的三權鼎立改為他的君主權(單一)、行政權(特殊)和立法權(普遍)的三位一體,認為在這個政體里立法權只有在“法律需要進一步規定”時才起陪襯作用,行政權雖然發揮著較大作用,但也不過是咨議而已;惟獨君主權作為上帝的代表是“作出最后決斷”的環節,“它把各種區分開的權力集中于統一的個人,因而就是整體,即君主立憲制的頂峰和起點。”(該書中譯本,北京,1961年,第281頁以下)這種神秘主義的和保守主義的憲法思想顯然是一種倒退,馬克思在其《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1843年)里已經作過正確的、尖銳的批評。所以我們也許可以說,費希特早期的憲法理論是德國古典法權哲學的最高成就。但很遺憾,在我們中國的法學史和哲學史教科書里,總是大談康德和黑格爾,而看不到費希特在法權哲學中作出的這一卓越貢獻。現在,謝地坤和程志民提供的這個在信達兩方面做得十分出色的《自然法權基礎》中譯本,將有助于糾正這類紕漏,而這就是筆者要介紹和評說這本古典作品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