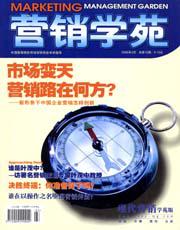找準你的位置感
楊 禹
近一段時間來,奇瑞、吉利、長安等國內汽車企業,頻頻見諸報端、屏幕。它們多年來在自主創新道路上的探索,確實有不少可取之處,也與自主創新的戰略取向相符。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媒體在相關報道中夸大這些企業在自主創新上的成效,而對這些企業及其產品存在著的某些缺陷,卻有意無意地有所回避;同時還試圖以這類企業的成功作為論據,來否定此前已實行多年的“市場換技術”戰略。而此前,在媒體報道中我們聽到更多的是來自另一個極端的聲音,即汽車制造是一項投入巨大、研發難度高、歷史傳承性強的產業,國外巨頭領先得太多、實力超強,我國沒有必要再另起爐灶、從頭干起,而是要通過開放與合作,“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汽車業內人士發出的偏向于兩個極端的信號,被媒體簡單地放大之后,使得一場不同發展模式間的爭鳴,演變成了兩條道路之間試圖相互取代的較量。
事實上,“自主”與“開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為什么這樣一場偏頗與偏頗的較量,謬誤與謬誤的較量,會出現在我們媒體的報道中?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自位置感的模糊。具體體現在:
首先,缺少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一些記者同行雖然到汽車生產和研發一線做了實地采訪,但苛刻地講,仍欠缺兩條:一是調查采訪中的冷靜心態,二是對報道對象的持續關注。
不妨拿奇瑞來舉個例子。前一個時期,支持“市場換技術”戰略的業內外人士常常抨擊奇瑞是“關起門來另搞一套”,是想回到閉關鎖國的時代。很多媒體報道了這些聲音。而事實上,“奇瑞模式”從誕生之初,就不是在“閉門造車”。其不同于合資模式的開放思路,在全球汽車產業的發展史上也并非無先例可循。不少批評奇瑞的人,實際上并不真正了解奇瑞的實情。另一方面,近一個時期里,有些媒體在把奇瑞作為自主創新典型加以報道時,又似乎對奇瑞作為汽車行業的一個后來者所難以超越的局限性不予關注。這顯然也與事實不符。客觀地看,汽車制造確實是一項很“高級”的產業,奇瑞產品的稚嫩,在消費市場上是顯而易見的。而我國的汽車消費者群體,同時也作為新聞報道的受眾群體,他們對汽車產品的了解程度在不斷提高。這決定了新聞同行們必須靠足夠的客觀和全面,來構建報道的說服力與媒體的公信力。部分媒體片面強調奇瑞在自主創新上的探索成果,避而不談任何一個企業或一種產品都可能存在的局限和缺陷,反而使整個報道的可信度下降,影響了對自主創新政策的正確解讀。
其次,對政策的理解不透。國家的自主創新戰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之舉。其相關的政策體系、制度建設要求,有著相當多的整體考慮和具體設計。部分新聞媒體在報道汽車領域的自主創新時所表現出來的極端或搖擺,體現出對政策的理解不精、不透。有一些新聞媒體在報道汽車界的爭論時,失去了媒體自身的冷靜,而是運用多種報道語言,片面夸大其中的某一種聲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要有選擇地支持一些汽車企業的發展,并非如某些西方理論闡述的那樣完全回避這種行為,但也并非如有些人期望的那樣,做出過于具體的、只讓個別企業受益的支持。媒體如不能對國家政策做出透徹的理解,并冷靜引導輿論,就無形中助長了前文所述的“謬誤與謬誤的較量”。
第三,不能正確處理與采訪對象的關系。國內媒體多年來培養了一批專注于汽車報道的專家型的優秀記者。業緣關系的積累,對記者本人和其所在媒體來說,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但是,這也容易成為一個陷阱。
多年來,與汽車企業積累了豐富業緣關系的汽車記者,采寫報道的時候,漸漸多了一些“額外的”考慮。有些記者是通過對個別跨國汽車企業的采訪,才跨入了汽車報道的門檻的。從此,在判斷事關汽車業發展的重大問題時,難免習慣于從自己比較熟悉的企業的視角出發。有的跑口記者,考慮到與跨國公司及其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之間保持長期工作關系的需要,在對行業重大問題做出判斷時,也下意識地瞻前顧后,失去了新聞媒體應有的超脫與冷靜。還有的記者,生活中成了某個品牌汽車的駕駛者、愛好者,于是在報道中,也夾雜進了一些個人的好惡和選擇。
這些情況,雖然發生在少數記者身上,但不能不引起新聞界同仁的嚴肅思考。這不僅使部分記者失去了基本的職業判斷力,也使很多新聞報道失去了基本的立場,而在復雜的社會音符間隨波逐流。
第四,屈從于媒體炒作的需要。媒體是社會公器,但也時刻處在競爭之中。這是市場經濟的常態。新聞媒體應積極地參與競爭,但也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迷失掉這個行業自身的準則。
一些報道者為了批駁某種偏頗的觀點,并使自己的報道引起更多受眾的關注,便試圖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路子,以矯枉過正的姿態,把自己的立論擺放到了相對立的另一個極端上去。這場“謬誤與謬誤的較量”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從這個角度看,確實包含著個別媒體在炒作分歧、夸大分歧,乃至無視事實真相和忽略全面觀察、放棄客觀判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