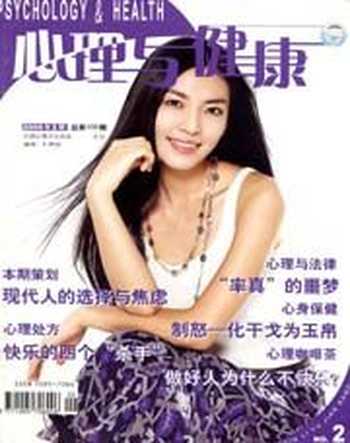不僅僅是愛情
劉小麗
1990年版的《大學生管理條例》還明確禁止大學生結婚。那時大學生談戀愛也是不允許的,有限的幾對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十幾年過去了,時代風氣一變再變,一轉再轉。如今,昔日的“地下黨”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地談婚論嫁。在新《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人為本”思想的鼓舞下,各大高校中,被學生們私下稱為“夫妻部落”的群體正在逐漸形成。所謂大學生“夫妻部落”,其實并不限于登記結婚的大學生,而是包括所有戀愛者,特別是那些戀愛同居者。
在當今社會,同居,早已不再是新鮮的話題。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人權思想的深入人心,社會輿論對同居的態度也愈加寬容。但是,當“同居”與“大學生”這一特定群體聯系起來時,這個話題便又有了討論的意義。一方面,大學校園的人文環境越來越寬松,學子們抒發愛情的興致持續高漲;但另一方面,家長和教師嚴峻的目光和批評的聲音卻從來沒有消失過,大家批判同居影響校園學習風氣、影響學習,指責多數大學生的經濟來源是家長的血汗錢、婚前同居不受法律保護等等。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大學生同居目前在道德層面上還不能算一個絕對的中性詞,它依然和不求上進、不務正業、不良影響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的關鍵問題就是“性”。
雖有了結婚的權利,但大部分同學大學期間仍只接受戀愛,對需要更大責任能力和更多義務擔當的婚姻,尚不愿輕易涉及。于是,很多人選擇做“邊緣人群”,組成“夫妻部落”。這群生理發育成熟、心理卻尚稚嫩的孩子能承擔得起同居帶來的后果嗎?身為學生,未婚同居是對人性的尊重還是對倫理道德的忤逆?未婚同居對他們今后健康的婚姻生活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又有什么方式能取代同居來滿足他們生理和情感上的需求?盡管懸疑種種,但年輕的學子們已經等不及結論的得出,越來越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打開了“同居”這個潘多拉之盒。理由之多,來聽聽他們的聲音:
以愛之名
“在兩個人的感情達到一定深度,兩個人都希望和愿意愛與性相結合的時候,性就變得自然而然了。性的選擇很簡單,兩人相愛就夠了。愛,就是性最可靠、最權威的許可證”。作這樣選擇的學生們,唯“愛情”是尊,認為有愛情就應該有想要得到的一切,隨著日益接近和親昵,性,成了他們戀愛之后理所當然的發展,初嘗禁果的好奇令其對愛情多了甜蜜而盲目的依賴,在愛情的名義之下,他們對同居樂此不疲。
慰藉孤獨
“來自南方的我們對這座北方城市很不適應,不適應這里的食物、語言、還有宿舍的嘈雜……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認識了,共同的感受讓我們惺惺相惜,長時間的孤獨讓我們說什么也不愿意錯過對方,所以我們在兩人的學校之間租了一間房”。很多身在異鄉的同學都有著類似的經歷:剛剛離開父母的懷抱,面對周圍一群陌生的面孔,沒有熟悉的聲音和環境,孤獨隨時襲來,思鄉的淚水更是層層涌動。別人不理解他們的不適應,只有同鄉之間才有共同語言。于是,同齡的兩個人互相傾訴、互相照顧直至互相愛戀,相依為命的幸福感和“家”的溫馨感促使他們以同居來排解孤獨。
以示成熟
“我們宿舍4個男生,其中3個都有‘老婆了,我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會被他們小看的,而且我也是成年人了,看到他們‘那樣了,發現自己其實也有那種需要”。不少男生有些委屈又有點兒調侃地說道。戀愛中的雙方尤其是男生,希望以某種方式來肯定自己的戀情,肯定自己的成人化而不是一般人幼稚懵懂的校園之戀。于是以成人的方式面對愛情,于是想到“同樣是成人,憑什么校園外的成人能興高采烈地抒發愛情的美妙,而我們只能在墻內看?為什么我們不能坦然接受現實”?性行為便有了合理的理由。
婚前練習
“我覺得現在的同居也是在為以后的婚姻作準備,我不覺得這是對婚姻的不負責任,恰恰相反,這才是對婚姻負責任的態度,而且經歷了選擇的過程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人”。有人如是說。然而卻有統計表明,在這些同居的大學生中,婚姻的成功率不到5%,一般都是畢業之后各奔東西分道揚鑣了。對他們而言,“婚姻”這個詞還很陌生,即便以未來婚姻的名義,同居仍不能給他們中的任何人帶來婚姻的必然保障。也就是說,社會競爭如此激烈,面對未來的多種不確定因素,在現代大學生的世界里,前途比什么都重要,如若婚姻和前途有了矛盾,那么他們是不會因為曾經同居就一定選擇婚姻而放棄前途的。
對于大學生同居現象,我們已無法從純粹的愛情或婚姻的角度去理解它,我們顯然不能把這種游牧式的短暫的大學生同居理解為純粹的生理和感官上的需求。其實,多少學生有過性行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少學生對自己的性行為的安全程度以及結果有清醒的認識,重要的是他們是否能對自己的行為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對待“性”和“責任”上,大學生的情形有別于其他社會群體。大學階段所處的環境十分特殊:大學生涯是從學生群體過渡到社會人的最后一個階段,生理發育基本成熟,在年齡上已經屬于成人;經濟上基本(或者按常理說)沒有壓力,大部分不用自己養活自己,衣食無憂,可以不用考慮重大的生存問題。也就是說,大學生擁有成人的生理條件卻沒有一個成人的社會條件,這是客觀事實。然而人畢竟是社會的人,所有的行為都有其社會影響。在大學生同居問題上,責任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能力上而不是思想上。客觀方面能力的缺失使得大學生在面對同居行為可能造成的后果面前顯得比有收入的人更加無奈,也就是對后果進行補救的可能性更小。在此時,為了愛情可以情愿奉獻自己并為愛生死相許,但隨著時間流逝和年齡漸長,生活的重心必然轉向學業和事業,特別是對那些迫于現實原因沒有走到一起的學生們,對往事無奈的回味或者曾經的傷感都縈繞于心,處理不當就會對以后正常的婚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常常發現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障礙都與青春期成長的陣痛有關,尤其對女大學生而言,因為性知識缺乏或者其他原因,同居造成的早孕、流產更會對其身心留下永久的創傷。
中國第一本大學生性心理自傳體小說——《非常日記》的作者、西北師范大學的徐兆壽教授從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提出了看法:“18歲以上的青年,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基本上已成熟,在這個時候發生性行為即同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始終強調一點,那就是以愛為基礎,失去了愛的同居,是不道德的。”
浙江大學心理與行為科學系主任沈模衛教授就此發表了他對同居問題的看法:大學生這個年齡段是一個生理和心理日漸成熟的過程,處于這個年齡段的人,對性會有比較大的好奇心,但是由于心理的不成熟,往往容易產生一些偏差。對于解決途徑,我覺得更多的不應該是堵而應該是引導。
大學校園是一個男女生集體“群居”的地方,是一方容易滋生愛情的水土。但是在這方特殊的土地上,我們必須遵守一些“規矩”,適應“群居”的生活。19—22歲這一年齡段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期,人的一生當中,是很難再有大學四年這樣一個集中的時間來進行學習、與同學朋友共同生活的。大學生們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家庭的責任、正確的婚姻觀念和性觀念,這需要社會及學校的理性引導,也需要個體的進步。只有這樣,當愛情來臨的時候,才能在享受愛情美好的同時,也能對愛情有著積極的清醒認識;在大學時代學習愛與承擔責任,以及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走上一條后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