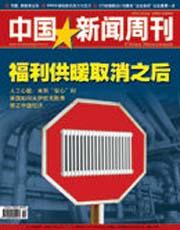鄰居:重新崛起的社會資本
孫 冉 曹紅蓓 張 炫
鄰里關系的淡漠曾被視為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代價,然而,在素有“遠親不如近鄰”傳統的中國,鄰居,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正在重新崛起。
翻開《現代漢語詞典》(修訂版)第798頁,對“鄰居”一詞的解釋是:住家接近的人或人家。如何與人為鄰,曾是中國古老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命題,“孟母三遷”的故事、“遠親不如近鄰”等俗諺,使最平凡的百姓都知道鄰居的重要性。
鄰里淡漠是城市化的代價?
新中國的鄰里關系存在于三種不同的社區類型中。第一種是平房街道社區中的傳統鄰里關系。以北京為例,解放初期,四合院是家庭的再生產空間,獨門獨戶,在空間地理結構上與鄰居的房間靠得非常近,鄰里之間家庭氛圍濃厚。直到1956年,大量外來人員進京,政府安排其入住四合院,才逐漸打破原有格局,向大雜院過渡;尤其是1976年大地震后,大雜院公共空間更是被大量占用,從此鄰里關系開始變得復雜化。
第二種是單位社區的鄰里關系,這是1958年后政府為高效推近工業化進程而實行職宿一體的形式;七八十年代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現了新公寓改造,這些新公寓,即現在所說的“老單元房”,只考慮改善居民居住面積和居住設備,但沒有考慮到在居住環境中仍然有原來的交往空間和設施。在此后的10~15年的時間內,這個問題都未被慎重考慮。單位社區的鄰里關系實際上是業緣關系和鄰里關系的疊加,即除了工作關系外同時也是鄰里關系。家長之間是同事,孩子們是同學、是伙伴,彼此見面打招呼,平時有空常串門,逢年過節禮尚往來的氣氛依然很強烈。鄰居之間互相信任,我家鑰匙放你家,你有事我幫你照看孩子的事情比比皆是。至今,這時的鄰居關系仍被很多人所懷念。然而,由于這種鄰里關系完全是被動的,且存在工作關系在里面,鄰里關系也很微妙,自由度相對較少。
第三種是商品樓社區的鄰里關系。這種形式興起于1990年代。隨著住房補貼的出現,及福利分房的結束,人們開始慢慢嘗試著買房了。住房類型的多樣化,提升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需求,也帶來了陌生的鄰居。早期的商品房居民擇鄰而居的余地很小,鄰居之間彼此互不相識,相識的愿望也很淡薄,雖然近在咫尺,卻遠隔千里。此時,鄰居間的糾紛逐漸減少,轉為冷漠的情緒。住上三五載都不知對門是誰的情況隨處可見。
更寬敞更獨立的空間改善了居住環境,卻難以滿足群居的人們社會性心理上的歸屬訴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把城市樓群中鄰里關系的淡漠解釋為城市化的代價。
他對本刊表示:總的來說,由于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全球性的鄰里關系正在從一種首屬性的關系向次屬性的關系轉變,鄰里人際關系日趨疏遠,鄰里社會資本流失嚴重。這種變化的意義完全是消極的,只能用“退化”來定義它。
你的鄰居,你的資本
在社會學中,社會資本被定義為通過社會關系獲得的資本,是期望在市場中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它既包括社會關系本身,也包括由此所帶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作為一種唾手可得的社會資本,千百年來在中國曾經備受重視的鄰里關系曾一度被人們遺忘。
1990年代后期,在商品房社區的規劃和購買都日漸成熟之后,居住已經成為人們依據自己的經濟地位對于城市空間的重新布局。當人文地產的概念在房地產界大行其道,而懷有濃郁睦鄰情結的飽受教育者終于在城市的經濟生活中拼搏上位,成為一介新晉的準中產時,人們重新發現了鄰居。
遠水解不了近渴,不論是意外時刻還是緊急情況,向鄰居求救總是最快捷的方式。鄰里交往不但減低了娛樂活動群體性的支出,亦是友情投資最容易獲得回饋的方式。在一些以前以陌生居住為標志的商品樓小區里,鄰居間還重新出現了業緣的粘連跡象。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與鄰居的關系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怎么樣的影響。
雖然準中產業主和社區是新睦鄰暖流的策源地,但這股暖流的影響沒有理由不波及其上下的經濟階層。種種跡象表明,鄰居,作為社會資本正在重新崛起。
對社會資本的重視,是儒家文化的特點之一。長期浸淫其中的國人對此從來不陌生。
復旦大學傳統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胡守鈞認為,和諧社會將落實到兩個基本地方,一個是各種企業和機關,另一個就是社區。社會資本對于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社區的建設來說,胡守鈞認為應當多建立公共平臺,如社區網絡、會所等,同時發展小區里的草根社團組織。社區發展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個和諧共生的家園,以互動的方式合理地共享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