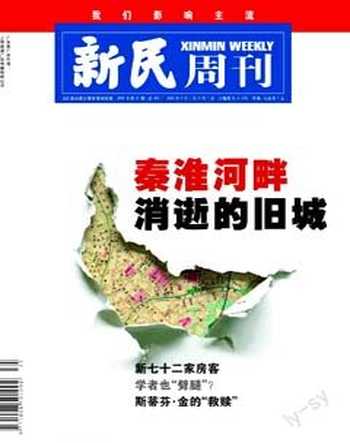如果汽車論斤賣
曾文祺
如果汽車論斤賣,則中國制造永遠提升不到中國創造,體力活永遠提升不到知識活,大家永遠都在產業鏈的最底層掙扎,而不能到產業鏈的高層享受。這不會是我們理想中的21世紀,不會是理想中的中國。
制造業是個體力活,跟農業一樣,一份耕耘一份收獲,只不過是把農田變成工廠,把鋤頭變成螺絲起子。
全世界的制造業有個行情價,跟農業一樣,生產一斤稻米與制造一噸鋼鐵的成本計算方式一樣,售價在扣除人為的關稅壁壘之后也一樣。
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農業社會逐漸跨入工業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農夫變成世界工廠的工人,人均收入從300美元提升到1000美元。300美元與1000美元的差距,是稻米與鋼鐵價格的差距。
當中國開始學會把鋼鐵變成汽車,把擰螺絲的工人變成品質管理工程師,一些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均GDP也從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傳統的農夫不需要念什么書,當個工人至少要念到中專,做個好工程師,就得要大學畢業。人們努力念書,好讓自己的薪水增加;國家投資在教育的經費增加,希望人民的素質提升,最終反映到GDP的提升。
日本與美國的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是“農業中國”的100倍,是“工業中國”的30倍,即使對應到經濟最發達的“工程師中國”,也有10倍的差距。在經濟活動的過程當中,附加多少價值,取回多少報酬。農民取回稻米的報酬,工人取回鋼鐵的報酬,而工程師取回汽車的報酬。但是,同樣都是做汽車,為什么日本工程師的報酬是中國工程師的10倍呢?差別在于汽車的附加價值。日本人制造并銷售汽車的利潤,是中國人的10倍以上,反映在報酬上也是10倍以上。
國內一位著名摩托車企業的老總,當被問到為什么要進入競爭如此激烈的汽車行業時表示,相對摩托車一公斤賣28元,汽車現在一公斤還可以賣100元,競爭不算太激烈,空間還很大。這種汽車一公斤賣多少錢的思考方式,與稻米一公斤賣多少錢一樣,重點在于計算勞動力的成本,只不過是把農民的勞動力,換算成工人與工程師的勞動力。與其他國家競爭的基礎,在于中國廣大與廉價的勞動力。只要中國工人薪水夠低,工程師薪水夠低,做出來的汽車,一公斤的價格夠低,就可以跟外國競爭。
商人做買賣,論斤稱兩,從短期利益出發雖然說目光短淺,卻也無可厚非。當今中國,商人們確實是靠著眾多廉價的勞動力,把全世界打得鼻青臉腫。如果從長期的眼光來看,隨著GDP的成長,勞動力的成本也會不斷攀升,如果勞動力的價值無法跟著提升,GDP成長的動力必然消失,從長遠來說,一定要提高人的附加價值。
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個人,勞動力的提高,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把靠雙手勞動所得,提升成靠腦力知識所得。知識所能創造出來的價值,遠高于體力勞動所能制造出來的價值。
雙手的勞動力,提升到大腦的智力,有兩種途徑。在初始階段,大家靠左邊走,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運用左腦的理性能力,成為建設新中國的工程師。在下一階段,開始有人朝右走,研讀文史哲,走進自己的興趣,運用右腦的感性能力,感動自己,感動中國。工程師的中國,經濟建設的步伐很快,物質生活提升也很快。人文的中國,文化的多元發展,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滋潤人們的精神生活。兩種途徑,理性與感性,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價值都很高,報酬都很豐富。
如果汽車論斤賣,則中國制造永遠提升不到中國創造,體力活永遠提升不到知識活,大家永遠都在產業鏈的最底層掙扎,而不能到產業鏈的高層享受。這不會是我們理想中的21世紀,不會是理想中的中國。
13億中國人,不是吃苦耐勞就是聰明伶俐。能做世界上最優秀的農夫,最熟練的技工,最能干的工程師,也能做有創意的文學家。無論是做哪一行,都不能讓自己論斤賣,都得善用知識,創造新的附加值。只有中國制造提升到中國創造,全民才能有機會奔小康,才能創造出和諧社會。21世紀,也才會是中國人的世紀。